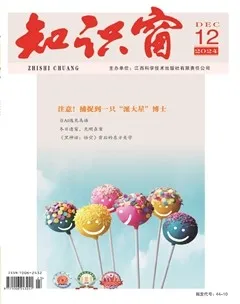淋湿青春的眺望
谁的青春里没有一次足以淋湿岁月的眺望呢?
我和子涵在读小学时就认识了。她住在隔壁的巷道里,和我的小区只隔了一面墙。墙边有棵槐树,我每次找她时,只需要从树干爬到墙头,再翻过去。秋冬季节,树叶落光后,从我家厨房可以看见她家的后窗;春夏季节,枝叶繁茂,挡住了视线,但到了晚上,我仍能看见她家亮起的灯。
也因此,我习惯了在厨房刷牙洗脸,时不时地抬头眺望,“她还没有睡觉!”可惜,我只能看到一方暖黄色的灯光,看不见灯下的人。子涵在做什么呢?无人知道,就像无人知道窗外深深的夜色里藏起了多少悦耳的虫鸣一样。
有些秘密不适合独守,它需要一个人去分享,但只能有一个人,否则它就不是秘密了。我和子涵在槐树下谈天说地,班级里的、家里的或是电视里的故事。它们是挂在槐树上的风铃,在当时清脆地响着,可如今早已摇晃不动了,生锈后,纷纷掉落在泥土中。我再也记不起来童年的呢喃絮语,它们和夜色中的虫鸣一样,只在那个夜晚才有意义。
我只记得我和子涵一起去过的地方——地点是没法被风刮走的。巷子旁有一座废弃的老屋,屋内屋外长满了比人还高的草。在青苔横生的瓦片上,藏着雨的小情绪,由风种上些草籽,用一层层绿意将它们掩盖住。这里是被人遗忘的角落,却成了昆虫的乐园。蜜蜂和蝴蝶喜欢捉迷藏,一个藏在花蕊中,一个把自己打扮成花瓣,风一吹,就呼啦啦地飞了出来。我们坐在墙头上,闻着槐花的清香,听着蝉的卖力演唱,任由影子在草叶间和蚂蚱一起寻找童话。两个人脸上的笑意被熏得暖暖的,阳光稍稍一倾斜,彼此的弧度便完美地连在了一起。
后来,我和子涵约定好,我做完作业后,推开窗子,朝她那儿大喊一声“严子涵”。她若是也想出来玩,就把窗户打开,否则就拉上窗帘。那时,我们没有手机,这一声声呼喊便成了我对童年深切的怀恋。
很长时间,我都不知道子涵家窗帘的颜色。
不过,升入中学后,我和子涵在不同的学校读书,就很少聚在一起玩了。在一些晚上,我到厨房刷牙,看见远方的小楼亮着明黄色的灯光,总会有一种莫名的感情涌上心头。正如微风划过夜色的眉头,一些褶皱也出现在我的目光中。她偶尔会趴在窗台上,一动不动。是在眺望槐树,还是想听一听虫鸣?我想喊她的名字,可那声“严子涵”却始终拽不出喉咙。
当然,我和子涵的关系还是很好的,在路上遇见,依旧会相伴而行,只是都默契地由以前的肆无忌惮变得含蓄,影子之间留出足够的距离。当高考时,听说她有一门科目发挥失常,到我母校的复读班里复读。大一寒假,我回到母校,路过她所在的教学楼时,不禁抬头眺望——她此时又坐在哪儿,还是在窗户旁吗?我突然感到有些遗憾,若是晚上来,教室里的灯光照在窗户上,应该会让我的目光也分到一些暖黄色。
大二后,我很少回家了,一些回忆也渐渐褪色。直到毕业那年暑假,我无意间抬头往窗外望去,湿漉漉的黑色笼罩了一切。那扇窗呢,那盏明亮的灯去了哪里?那一夜,虫鸣不断,扰得我辗转难眠。
第二天,父亲告诉我,对面的人家搬走了,巷子已经荒废。我爬上墙头,果然,老屋还在,对面的房子也还在,但已经空了。她家土黄色的外墙壁上,细细的野草钻出了头,轻轻摇晃着,像是在告诉我,这里也将成为一座荒屋。
我坐在温柔的槐花香里,久久不动。我知道,在这个人潮汹涌的城市,在这个广袤而空荡的世界,我们可能再也不会遇见彼此了。那曾经的眺望,都将像是屋檐上的大雨,淋湿我的一段青春,然后蒸发,杳无踪迹。
但我还是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在这个城市的某一个地方,我心有所感的一次仰望,会看见一扇窗户里似曾相识的身影,与我对视后,再把目光错过。于是,我微微笑着,对这人世间的无常聚散,交出一声悠长的叹息。
如今,风又吹起了槐花香。
(作者系河海大学水文学与水资源专业2020级工程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