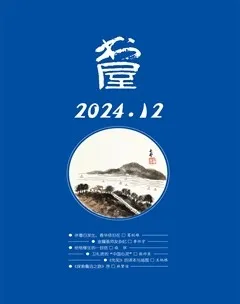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徐泓《燕东园左邻右舍》(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版)一书是一部有关燕东园建筑、故人和往事的回忆录。徐泓是燕东园40号老住户徐献瑜先生的长女,她生于1946年,她在序言中说,她一直住在燕东园,对燕东园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因而在字里行间都表现出对燕东园的无限深情:“必须提起笔来,为燕东园这些小楼,为曾经住在楼里那些不应被遗忘的老一辈学者,为发生在楼里那些不应被湮没的往事,留下一份追索与记录了。”
对现在的一般读者而言,燕东园是不及燕南园被熟知的。而事实上,燕东园和燕南园都是燕京大学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修建的教师住宅区。燕东园于1926年动工,燕南园则稍晚。燕东园占地七十七亩,在校园外;燕南园占地四十八亩,在校园内。燕东园大而阔朗,燕南园小而幽深。
《燕东园左邻右舍》是徐泓对居住在燕东园的燕京大学和其后转入北京大学的教授学者们的往事回忆、轶事钩沉。徐泓以“燕二代”的后辈视角来仰望这些大先生们,回忆那一代学人为人处世、教书育人的点点滴滴,平凡中蕴藏伟大,琐事里饱含景仰。“出自我们燕东园二代独特的视角、私人的记忆。以此缅怀我们长辈们波澜起伏的学术人生,悲欣交集的精神求索。还有我们也曾经受益的,那一代读书人的家风,教养与品格的魅力。”
《燕东园左邻右舍》总共十章,图文并茂、可读性强。每一章标题下配有一幅手绘图。第一章标题下配的是燕东园(东大地)的平面图,可以让读者俯瞰全貌、了解布局;从第二章开始至第十章标题下配的是钢笔速写画,画作勾勒该章涉及建筑的一般性特征。每章正文之中还配有相关建筑的照片或者相关住户的若干照片,弥足珍贵。以每一栋小楼(小院)的住户为记叙对象,以居住时间先后为顺序,讲述那些鲜为人知的往事。因为当时大学教授工作的变动频繁,同一栋楼可能先后有不少人住过。徐泓就依照时间先后顺序制作了同一栋楼不同时期住户的姓名、职位“档案”,这一“档案”附在某号同一栋楼人物故事的后面。这样的设计组合,使全书叙事显得清晰、准确、完整。以燕东园桥东22号楼为例,徐泓在这栋楼的故事正文之后附录的住户名单为:
住户名单 1926年—1966年6月
东大地时期
徐淑希 燕京大学政治系主任
刘文庄
胡经甫 燕京大学生物系教授
龙承云(继室) 协和医院护士长
贺麟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后调入社科院哲学所
刘自芳 1956年去世
黄人道(继室) 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
燕东园时期
冯至 北京大学西语系主任
姚可崑 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教授
严宝瑜 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
吴琼瑂 北京大学西语系副教授
可以看出,燕东园桥东22号楼曾经有五位教授的家庭先后居住。但徐泓在行文时,并没有全部介绍,而集中笔墨写了徐淑希、刘文庄一家和冯至、姚可崑一家。这样的谋篇布局,既做到了资料翔实,又做到了详略得当,书中在写其他各栋楼的故事时,也大致如此。
正如徐泓父亲徐献瑜去世后的一篇纪念文章说的那样,书中记录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主要指的是出生于清末民国初年,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留学欧美,立志以科学救国、科学报国的这个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几乎有着共同的经历:国难的时候回来了,国运转折的时候留下了,历次政治运动经受了,改革开放以后再尽力了。”
燕东园桥西42号楼的谢玉铭教授和他的女儿谢希德的故事让人唏嘘。在新中国成立时,原来任教于燕京大学物理系的谢玉铭教授已在菲律宾马尼拉东方大学任教,当时他的女儿谢希德在美国读博士,他希望女儿博士毕业后继续在欧美从事科学研究,而谢希德和新婚丈夫曹天钦博士没有听从谢玉铭的意见,在1951年经过一番周折后毅然回国。这一事情造成了父女之间的误会,以致父女断绝关系。谢希德回国后在复旦大学任教,笃志研究,潜心教学,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才,被誉为“中国半导体之母”,1980年夫妻二人同时当选院士。
读燕东园桥西38号楼的张景钺、崔之兰夫妇一家的故事,我感受到当时学人教书育人的热忱。文中写到生物学家崔之兰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大学一丝不苟的教学态度:“每个星期日上午,她都会到系里的工作室准备下周的课,写好讲课大纲,设计好配合讲课所用挂图悬挂的位置和顺序……崔先生为培养青年教师倾注了满腔心血,她的指导细致又严格,从讲授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用词、板书乃至衣着都要过问。”
我感动于当时学人追求学术的执着。燕东园桥东22号楼的冯至、姚可崑夫妇被称为“模范夫妇”,他们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卓有成就、影响深远。读他们的故事,最感到震撼的是他们两人年轻时代在德国求学的执着和互不干扰:
1932年10月,姚可崑从(北平)女高师毕业,攒够了去德国的旅费……一对恋人分别两年之后终于相会了。冯至把未婚妻接回柏林,却做了一个不寻常的决定。他们一起住到城市的西郊,但是住在了不同的街道,冯至住的那条街叫“鸣蝉路”,他为姚可崑租了另一条街的房屋,那条街名叫“落叶松路”。
为什么做这样的分居安排?他在给杨晦兄的信中写道:“可崑已经到柏林一个月了,她住在我的附近,我们的生活很好。但我常常有不知所以的不安,生怕自己失掉了自己。因为两个人常在一起,是容易任意把自己抛掷的。这中间各人保持着个人的境界,要有一番修养。”
冯至、姚可崑两位先生青年时代追求学问、为了各自的事业不迷失自我的做法,至今仍值得当下青年人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