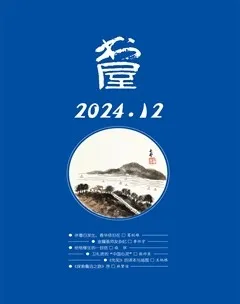冷湖是许多人心头永远的痛
1982年2月9日(正月十六)夜,在哗哗作响的大雨声中,我随父母乘火车离开家乡湖南衡阳,三天后到达甘肃柳园,15日夜宿冷湖。次日早饭后,我迎着清冷的阳光和凛冽的寒风,向长街东头迤逦而行,没想到遇上了外国人。他们见人都很友好,我们互相挥一挥手,“哈罗”“哈罗”。过后才知道,1979年开始的甘青藏石油大会战(主战场在柴达木盆地,也是柴达木石油第二次大会战),当时的石油工业部与美国地球物理勘探服务公司(GSI)签订中美合作地震勘探合同,美方派来专家及雇员四十四人,中方配合工作人员有五百四十人。所以,冷湖上空出现了小型直升机,路上有了中国最早的日本丰田和美国福特越野车。
冷湖以石油名世,曾是中国第四大石油基地。1958年9月13日,冷湖五号地中四井钻至六百五十米时发生强烈井喷,日喷油量达八百吨。远在玉门油田的著名诗人李季,闻讯赋诗《一听说冷湖喷了油》。翌年春夏,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及副部长孙敬文、康世恩等先后来探区视察,柴达木盆地开始第一次石油大会战。冷湖当年原油产量达到二十四点六万吨,约占全国原油总产量百分之十二。
地处柴达木盆地西北端的冷湖,是沟通青海西部与新疆、甘肃两省区的结合点,北距敦煌二百五十七公里,东距德令哈四百六十四公里,西距花土沟二百九十八公里,南距格尔木四百二十公里。它是全国日照时数最长、光能辐射最强的地区之一,也是多风和风力较大的地区,民谚有“一年两场风,从春刮到冬”。气候寒冷干燥,无霜期短,昼夜温差大,四季不分明。按照地名学原理,冷湖,冷湖,必定有一个湖泊。冷湖勘探开发比花土沟晚一年。1955年初夏,地质部西北地质局青海石油普查大队(代号632)一分队,首先深入祁连山脉尾翼赛什腾山下,最初落脚点就是日后的老基地。离老基地西北几公里,有一个半咸水湖,可以提供生产和生活用水。湖水很凉,蒙古族牧民叫它“奎屯诺尔”,翻译成汉语就是“冷湖”。曾有人把昆特依湖(蒙古语意为“谷地”)当作冷湖,坊间甚至有“昆特依市”的说法,其实二者相距几十公里。
1986年6月,我从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系毕业,志愿来到青海石油管理局机关所在地冷湖4号工作,曾经无数次来往于冷湖与敦煌之间,无数次路过苏干湖,写有题为《苏干湖岸听涛》的诗歌和散文。但你能想象得到吗?青海历史上第一首诗歌竟然出自苏干湖。苏干湖旧称墨离海,有一大一小、一咸一淡两个湖泊。《敦煌唐人陷蕃诗集残卷》中有佚名氏诗五十九首,其中三首与苏干湖有关,如《至墨离海奉怀敦煌知己》云:“朝行傍海涯,暮宿幕为家。千山空皓雪,万里尽黄沙。戎俗途将近,知音道已赊。回瞻云岭外,挥涕独咨嗟。”经两岸敦煌学专家严谨考证,佚名氏是曾为敦煌小吏的中唐时期落蕃人毛押牙。
石油被称作“工业的血液”,有了石油,才掀开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帷幕。而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要走上工业化进程,就必须有石油,必须甩掉“贫油”的帽子。1956年9月8日,徐迟与同行的苏联专家在冷湖度过一个难忘的中秋之夜,他在《共和国最初的岁月里》写道:“冷湖,新城市一座,已经定出规划来,东西街道规划了五条,南北的街道三条,都是五十来公尺宽的。冷湖市将有八平方公里面积。什么都要有,一应俱全。”三年后的1959年9月17日,国务院批准设立冷湖县级市,有心人可从当年中国地图上找到“冷湖市”这一称谓。
谈及柴达木文学及冷湖、茫崖、花土沟文化苦旅,首先不能不提到李若冰先生。这位“柴达木文学之父”有一个明确而坚定的创作方向,就是“我热爱这块土地,我钟情柴达木人。我爱柴达木大自然严酷的美,更爱柴达木人心灵的美”。他一生五进柴达木盆地采风,除了第一次1954年9月在花土沟停留,1957年、1980年、1987年、1993年均抵达冷湖。2002年10月,为了拍摄三集电视专题片《沙驼铃》,他随摄制组来到敦煌,由于身体健康原因未能跨过当金山,成为其终生的遗憾。
1956年冬天,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了李若冰,并寄予了殷切的希望。李若冰翌年二进柴达木,9月26日创作散文《冷湖的星塔》:“朋友,冷湖之夜,确实美极了。当你走出帐房,在探区走着的时候,天上布满了星座,大地上布满了星塔。天上地上,星星相互辉映,连成一片,组成一幅奇异绚丽的夜景。你听,沙丘林里有多少钻机吼动着;你看,又有多少钻探工在星海里劳动着。”
与李若冰前后来柴达木采访的,有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的记者姚宗仪、赵淮青、顾雷、卢云等人。他们对生活观察入微,文笔细腻生动,随笔和文艺通讯颇堪一读。其中姚、赵《在柴达木盆地上勘探》是海西州历史上第一本摄影画册,顾雷《祖国的聚宝盆》是第一本以“聚宝盆”揄扬柴达木的插图本读物,卢云《柴达木盆地访问记》则是海西州历史上第一本散文集。我没有见过顾、卢两位前辈,但在西安见过姚公,在北京见过赵公。我所写的柴达木文事数千则笔记,其中多得赵公的热情相助,他的脾气非常温和,说话不疾不徐,记忆力超乎常人。
1978年的中国,政治气候乍暖还寒,但作家、诗人们最先感觉到了春天。李季从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回到中国作协,担任党组副书记、《诗刊》主编。李季提议组织作家、诗人到各油田采风,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的赞同和支持。是年9月10日,在北京和平饭店,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与石油工业部部长宋振明商定,派出东、西两路采风团,奔赴大庆、辽河和柴达木、玉门四大油田。青海石油管理局办公室10月12日油印编发《油海新歌》四开小报的前言记载:“13名作家、诗人于中秋之夜,到我局访问、学习、创作。其中有《河北文艺》主编、《老坚决外传》作者张庆田,有河南文联作家、《检验工叶英》作者何南丁,有长篇小说《平原烈火》、中篇小说《小兵张嘎》作者徐光耀,有出过十余本诗集的诗人梁上泉,有长篇小说《海河春浓》作者王昌定,有短篇小说《心声》《希望》工人作者萧育轩,有湖南苗族诗人石太瑞,有江西散文作家吕云松,有安徽小说家刘克,有电影《万木春》、长篇小说《苍山如海》女作者潘青,有黑龙江省散文家林青,有外文杂志《人民中国》诗人韩瀚,有长篇小说《高山春水》作者侯述怀。”但据我所知,漏记了《人民文学》杂志编辑涂光群、冼宁,还有一个随团工作人员刘宗洛。
冷湖是许多人心头永远的痛。曾有无数志士奔赴冷湖开拓奋斗,无数儿女生长于斯,也有无数好汉永远留在了异乡。冷湖热浪,热爱冷湖,多少人梦萦魂牵,多少人含泪诉说,多少人千里迢迢前去凭吊。
《冷湖的星塔》是冷湖有史以来第一个散文选本,从六七十年间公开发表的数百篇作品中遴选而来,三四代与冷湖情感相系的人们,各自抒发对那块遥远而偏僻地方的相思之苦,读来让人潸然泪下,更让人怀念那个英雄年代。其中一些文章曾被历史的风尘遮蔽,人们之前可能闻所未闻。可以说,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散文选本,而是视野宏阔、角度各异、选点全面、文采飞扬,具有高质量和高品位的冷湖人文地图。
(本文系中国文化地理散文选本《冷湖的星塔》跋,黄海数字出版社202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