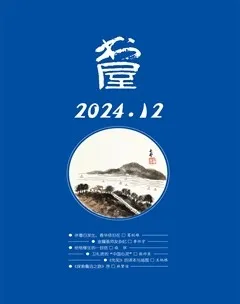印顺法师与太虚大师的因缘
一
1994年农历7月30日,一向寡薄病弱、八十九岁高龄的台湾著名高僧印顺法师在离开大陆四十多年之后,回到大陆,巡走当年出家、学习、教学等驻锡之地。此番意外之旅,乃是因为法师不能忘却曾经求法修学的因缘。
8月3日下午,法师到达宁波,先去了当年受戒所在的天童寺,又去了阿育王寺,再到奉化的雪窦寺。去雪窦寺,法师特意准备了一束鲜花,敬供太虚大师的舍利塔。法师在自传《平凡的一生》中说:“雪窦寺是虚大师舍利塔所在,也是我主编《太虚大师全书》(以下简称《全书》)的地方。可惜虚大师的舍利塔,已被毁灭了!只得将鲜花遥敬。”
法师性格平实,害怕礼数,自言不懂艺术,没有艺术气质,出了家,便将身心安顿在三宝中,不觉得有什么感情需要安放。法师自述:“离了家,就忘了家;离了普陀,就忘了普陀;离了讲堂,就忘了讲堂。如不是有意的回忆,是不会念上心来的;我所记得的,只是当前。”那么,这一束突兀的鲜花,定是法师念上心来的凭证了。约半个世纪前,抗战胜利后,1947年3月6日晚,法师从重庆辗转来到上海,礼谒太虚大师于上海玉佛寺的直指轩。“大师为教的心境,当时非常不顺适。”10日早上,因要到西湖一游,法师向太虚大师告别。太虚大师说:“就回这里来吧,带几枝梅花来!”哪知这是最后的礼别,不几天,大师匆遽示寂,舍报往生。法师得到电讯,特地折了几枝灵峰的梅花,带回大师灵前供养。
太虚大师喜欢鲜花,这大概印入了性格平静的印顺法师的脑海。1994年的大陆之行,最后一程,8月21日抵达香港,法师又带了鲜花,往芙蓉山礼拜太虚大师纪念塔。两次奉花供养,这在法师一生中颇为少见,或是仅有。
二
太虚大师与印顺法师同是出生并成长于钱塘江北岸的浙江海宁,大师年长法师十七岁,出家因缘各别。大师爱惜僧才,对法师慈悲关切,但二人在故乡却无缘相遇。法师第一次礼见大师是在奉化雪窦寺,时为1934年新年,法师二十九岁。法师回忆:“第一次礼谒大师,请求开示。大师只是劝我多多礼佛,发愿,修普贤十愿。我没有理解大师的用意,也就不曾忠实履行。现在想来,大师的慧眼,是何等犀利!他见我福薄障重,非多修易行道,增长善根,销除宿业,将来是‘孤慧不足以弘法’,弘法而必招障难的。”
法师在自传《平凡的一生》中时常感叹不可思议的因缘。日寇全面侵华前夕,一种不自觉的因缘力使法师东离普陀——从武昌到四川,远离了苦难,不至于遭受沦陷区生活的煎熬,而能进入一新的领域——新的人事,新的法义,深深地影响了随后几十年的一切。这种不可思议的因缘力,乃是来自太虚大师的一份坚持的指引。
法师自1931年2月进入闽南佛学院修学。太虚大师时任闽南佛学院院长,以培养现代僧才为佛教改革之重心,特别希望法师去武昌佛学院从事教学工作,而法师的心愿却是在普陀佛顶山通读佛法全藏的经典。且法师深感病弱的身体难以承受武汉夏天的酷热。他们第二次见面仍在大师驻锡的雪窦山。法师回忆:“在二十四年(1935)二月,回到了上海,又同到雪窦下院去再见大师。大师剃去髭须不久,显得年轻些了,劝我去武昌。我决心回普陀,完成读通大藏的目的。”紧接着,1936年初冬,二人又在杭州灵隐寺见面,大师仍希望法师去武昌世苑研究部任般若三论系的指导。法师没有答应,到镇江、南通巡游去了,大师派人到六和塔找法师,扑了个空。法师不愿去武昌,因此似乎有意避见大师,然而两个星期后,法师游历了镇江、南通等地后,准备回普陀,因设在上海三昧庵内的中国佛学会上海分会有常惺法师的演讲,法师心想横竖无事,也就和僧友一起去了,不料又在此地遇见大师。大师重提前议,要法师去武院。法师仍觉得去武院非心愿所在,但这一次因为在师友包围下,不善辞令的法师觉得实在应付不了,无可奈何,只好决定去一趟再说。然而就是这样一段不可思议的因缘,让法师避开了铁蹄与硝烟。法师回忆:“在我的回忆中,觉得有一种(复杂而错综的)力量,在引诱我,驱策我,强迫我,在不自觉、不自主的情形下,使我远离了苦难,不至于拘守普陀,而受尽抗战期间的生活煎熬。”法师深深体会到,这种复杂而错综的力量,便来自太虚大师要他去武院任教的坚持。他说:“我从因缘不可思议的经验中,时时想起了大师。”
三
太虚大师是中国近现代佛教改革运动中伟大的理论家和实践家,是近代“人间佛教”理论与实践的发轫者。印顺法师赞其“开一代风气”,是“惊天动地的思想革新者”“不世出的思想家”。太虚大师一生处于新旧交替、东西冲撞交汇的现代化时期,面对佛教衰败,发振兴佛教悲愿,创立人生佛教思想,著述宏富。但大师一生奔波于佛教改革运动,无暇整理自己的思想,其著述言论亦亟待归集。
1947年3月17日,大师匆遽示寂,出家、在家的佛教同人和弟子,深感《太虚大师全书》编纂之事不容再缓,而急需一位佛法造诣高深的法师领导,此时大家公推印顺法师担负领导责任。法师深感“大师慧命所寄,不忍浚拒,遂允加考虑”。
人员既已确定,但编纂《全书》的工作地尚待落实,负责此事的“佛教文化社”社长李子宽意欲在南京觅地,但一时找不到理想的地方,幸而时任雪窦寺住持的大醒法师向印顺法师发出邀请。一起参与编纂工作的续明法师回忆:“四月十五日,在鄞参加恭送大师灵骨赴溪口雪窦寺的行列,在山小憩数日,寺主大醒法师因坚邀印公来山编纂全书,印公和我,也以能在幽静地方作此项工作为最理想,但以子宽居士既有在京觅地编纂之计,故一时不便应允……京地既难获安静之地,印公乃将雪窦醒公邀往编纂之事相告李居士,因决议迁往雪窦山工作……于二十日下午一时,安抵编纂全书工作地——奉化溪口四明山雪窦寺。”
编纂组抵寺后,大醒法师妥为安置,将寺内之圆觉轩作为编纂工作场所,而一切饮食茶水等,均由雪窦寺常住供给。续明法师记述:“醒公法师对大师遗志之热忱与护助,深深地引起关心大师事业者的敬佩!回忆雪窦寺,自太虚大师于民二十一年膺任住持以来,直到胜利复员后,乃举大醒法师入主法席,故大师与雪窦寺的关系,甚为深远。大师圆寂荼毗后,众弟子议决:大师灵骨在雪窦山建塔供养,而大师法身舍利之全书,今亦在此编纂完成,大师与雪窦寺的因缘,真可谓不浅!”
印顺法师也记述此事:“大师去世了,弟子们云集上海。但是各有法务。留下的全书编纂,茫无着落。大家要我来勉为其难,总算在大师弟子中,有大醒法师供给膳宿,这才在大局如火的动乱中,草草地完成。”
1948年5月30日,由印顺法师领导,历时一年零十天,总计七百余万言的《全书》在雪窦寺安静的环境中大功告成。
四
1994年,八十九岁高龄的印顺法师手捧鲜花来雪窦山,因太虚大师舍利塔已毁,只得遥敬。但时经事纬,因缘成法,1995年担任雪窦寺方丈的怡藏方丈作《重建太虚大师塔院碑记》记述,怡藏方丈因仰慕大师悲愿弘深,矢志佛法精神,1999年用方丈升座所得香金及多年积蓄购置山林立地八十余亩,用于恢复大师塔院,并兴建纪念堂和教学楼。2000年5月4日请大师法嗣茗山老法师为纪念堂奠基。不可思议的因缘就这样来临,怡藏方丈在《重建太虚大师塔院碑记》中记述:“2001年闻香港菩提学会永惺长老珍藏竺摩法师转赠的太虚大师之舍利。我带领常住智理、明悟等师前往祈请,蒙能祥法师于中接洽,长老之慈悲,请得精莹剔透舍利两粒,在返寺一夜之间,于周围长出四粒,令我感动万分,说明大师护佑道场,更坚定我建塔院之信念……并在纪念堂落成舍利塔将建时,市旅游集团维修隐潭水库发现大师之墓碑,更让人匪夷所思此中因缘,深埋水中之物历数十年之久恰于此时又见天日,使我泪流满面,悲喜交加。墓碑虽被人为破坏,然乃历史之鉴证,决定将此墓碑镌于塔内,并将舍利一分为二,一份奉供入塔,一份留于培院供人瞻仰,以此告慰大师之灵,昭示后学。”
这真是:“墓碑虽坏是原物,主人识得自家门。晶莹剔透舍利子,直入如来真佛地。”
印顺法师的这一捧鲜花,跨越两岸,招引了不可思议的顺世因缘。法师说:“我怀念大师,我寻求着大师的精神,我期待着大师的乘愿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