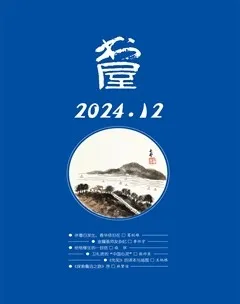翦伯赞:“爱国心之源泉”
翦伯赞1940年2月26日到达重庆,不久即发表了《中国历史科学与实验主义》一文,点名批判了胡适博士。文章一开头就单刀直入地指出“实验主义是以极粗浅的形式逻辑为基础的玄学”,是胡适从美国的杜威那里贩卖来的。他进一步指出,实验主义者左右开弓,以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全盘否定祖国几千年的文化成就,又对“真正在兴起中的社会主义思潮拼命的打击”。他对胡适的一些关于历史的说法,诸如历史是“百依百顺的女孩”,历史“一点一滴的进步”,“个人吐一口痰在地上,也许可以毁灭一村一族。他起一个念头,也许可以起几十年的血战。他也许‘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等,逐一进行了批驳,并指出这“完全是观念论中的主观主义”,是“陈旧的进化论”,是“极端强调‘个人’的作用,而否认‘大众’之历史的创造作用”的“神秘主义”英雄史论。
胡适曾傲慢地对青年们说:“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的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翦伯赞一针见血地指出:“很显然地,当胡适说这段话时,他自己已经被杜威牵着鼻子走了。”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重庆顿时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翦伯赞留在重庆,埋头研究中国古代史,还积极参加学术活动,并在文化界、学术界和政界的上层人物中做统战工作。他于1942年夏开始撰写《中国史纲》第一卷。这年7月22日,郭沫若写信给他说:“小弟需要《宋史·忠义传》及《元史·宪宗本纪》,听说老兄处有之,望能假我一阅。希望在炎热之中写一部火烈的剧本也。”这个剧本写的是南宋名将余玠、张珏于钓鱼城抗击蒙古军的悲壮故事。此剧未成,郭沫若另写了一个剧本《孔雀胆》,函请翦伯赞写剧评。12月31日,翦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关于〈孔雀胆〉》一文说:“在今年夏天,当寒暑表升到九十度以上的时候,我接到沫若先生的来信。他告诉我,他‘将在这火热的天气中,写一部火热的剧本’,而我在当时,却正在研究冰河时代的中国史。”
翦伯赞写作《中国史纲》第一卷(原始社会到战国时期),共三十万字,半年脱稿。第二卷(秦汉史)共四十六万字,又过一年脱稿。两卷付梓,第三卷(魏晋南北朝史)的写作又在筹划中。
全书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明确肯定中国的古代历史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原始社会。这个社会分为两大阶段,一为“前氏族社会”,即旧石器时代;二为氏族社会,即新石器时代。这个社会后期,经历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形成的阶段,接着进入商朝奴隶社会。西周、春秋、战国为初期封建社会,秦汉以后为“专制主义的封建制”社会。在论述每个历史阶段或朝代时,作者对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重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上下关联、相互关系,及其在整个中国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都作了比较深入、细致的剖析或评述,对于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亦有评价。
旧史学家包括胡适等人在内,对于先秦两汉史的研究,其资料只限于文献。信古者,以为中国的历史始于“冠冕堂皇的三皇五帝的文物衣冠的盛世”。疑古者则以文献不足征,只从周代讲起。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劈空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孔子替他揭幕”。有些人至多把中国古代史追溯到商代,而对原始社会史则不敢问津。他们的编纂方法,基本上是文献资料摘抄、汇编,再缀以个人的标题或说明。这样的著作,内容贫乏,资料单薄,千篇一律,根本看不出历史发展的真正过程,而只是朝代的兴亡和历史的简单循环。《中国史纲》冲破了这种旧的编纂方法,在文献之外,大量地使用了考古资料,其中包括古人类化石、石器、陶器、甲骨文、金文、汉简、石刻画像、碑刻、封泥、遗址和墓葬资料等,把考古资料从旧的金石学的狭小天地中解放出来,用以说明社会历史问题。
翦伯赞认为,历史是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历史著作不应“周诰殷盘,佶屈聱牙”,而应在不影响科学性的原则下,尽量生动一些。他在分析一些历史原理、讲述一些制度条令时,都力求文笔生动,引人入胜。他在书中还插入了三十多幅地图、九十多幅文物图片和八幅表格。大部分图片选自考古报告或临摹于古器物、画像石等,时代的、生活的气息浓厚。图文并茂,进一步加强了全书内容的直观性和说服力。这在当时的史学著作中并不多见。
1942年11月,在《中国史纲》第一卷即将脱稿时,翦伯赞将此情况函告郭沫若。郭很高兴,复信说:“这断然是一九四二年的一大事件。”该书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人们往往多方购求,以先读为快。而国民党领导的《中央日报》却一再发表文章,对此书及翦伯赞本人进行人身攻击和辱骂,翦伯赞则泰然处之,正如他在第二卷《序》中所说:“不管时代如何苦难,我总是走自己的路。”
在重庆的六年中,翦伯赞发表了六十多篇论文,如《略论中国史研究》《桃花扇底看南朝》《南明史上的弘光时代》《南明史上的永历时代》《我的姓氏,我的故乡》等。这些文章,资料丰富,观点新颖,现实性很强,不仅学术价值很高,而且强烈谴责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野蛮侵略,揭露和批判了国民党政府的黑暗腐朽及其妥协、投降政策。
翦伯赞还在文化教育界做了许多工作。他参加发起组建重庆大学教授联谊会,在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复旦大学、朝阳大学、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曹孟君创办的暑期学习班等单位作学术讲演。
1942年2月7日,郭沫若写信给翦伯赞,称赞他在文工会的讲演:“旧前莅城讲学,穷搜博览,析缕规宏,听者无不佩赞,诚为我辈壮气不小也。”7月14日,郭再次写信请翦到赖家桥文工会作学术讲演:“惠札奉悉,天气实在太热,老兄的讲演改到秋凉,听者的小弟也极端欢迎。不过此间的同志们依然希望您早来,其诚比太阳还要热烈。”
1944年夏,日寇疯狂进攻湖南衡阳,国民党军全线大溃退。翦伯赞愤慨地写下了《日寇犯衡阳有感》一首:“喋血常桃血未干,又传胡马渡衡山。焚书到处纵秦火,杀敌何人出汉关。南渡君臣怜晋宋,北征豪杰遍幽燕。莫倚巫巴能阻险,从来王业不偏安。”这首情感激昂、寓意深刻的诗歌并未见报,可是诗写成不久,即在进步的文化界人士中争相传抄吟诵,后来还传到延安。
次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