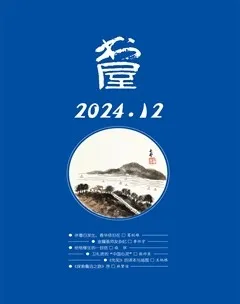2024年第12期书屋絮语
我初来《书屋》,洵兄最先为我引见的,便是湖南图书馆的崔述伟老先生。崔老头发花白,身朗体健,笑容可掬,在阅览室里向我们展示他的珍藏,有他的手稿书信、欲理还乱的剪报书影,还有保存了半个多世纪的发黄照片,岁月积尘,细处闪光。自打相识,崔老常亲来送稿,有时把稿件袋放传达室,每每附手书一封,缄好,题款,充满仪式感。我编发他的一篇文章,是关于他与翻译家杨静远的交谊。7月初,突然收到崔老逝世的噩耗,莫名悲痛,感慨万千。
诗人痖弦与家乡南阳的作家杨稼生相交三十年,往来三百封信,2014年结集付梓,一时传为佳话。关于书名,痖弦说:“鲁迅有《两地书》,咱哥俩的书就叫《两岸书》吧。海峡两岸音尘相隔,我们就像两只互报春讯的燕子。”他们真正见面的时间,不过“四天零十分钟”,但两颗滚烫的赤子之心,跨越浩渺时空,紧密相连。年岁愈长,眼发花手发抖了,收到信时,总是“一边看一边哭”,如是种种,终至于鳞鸿杳绝。稼生先生病重,将自己最后的手书,连同痖弦先生给他的最后一封信,都给了《书屋》。信末言“丝尽矣”,不想这一年之内,两位先生竟先后离世,虽高寿,却令人神伤不已。
信息时代,一笔一画的手写信可谓十足珍贵。犹记得初中时,同学间流行“笔友”的游戏。小小的信笺,课桌下悄悄地传,有时还多了一个苹果,或一只梨,余温未尽,轻咬一口,“流年暗中偷换”。信多数还在,老木箱子锁着,多年未开启。十几岁的信,写时青春一路燃烧奔涌,三十岁看了要笑,六十岁看了要哭。书信总要寄往远方。第一次面对邮筒,它沉默如绿兽,蹲守街角,一口将信件吞下,毫无声息,仿佛空荡荡的邮筒直通地心,或到达思念的彼端,或从此不见天日。可叹的是,写信人本已少,邮递员也变懒。信丢得多了,也就不再写信。西班牙作家安赫莱斯·多尼亚特的《高山上的小邮局》编织了一个幻梦般的故事:偏僻山村里的人们,用书信接力的方式,挽救了将被裁撤的小邮局,也串起了生命旅途中滚落各处的珍珠。
书信体小说原是一种特别的文学体裁,能予人以沉浸式的阅读体验,感染颇深。歌德年轻时写下《少年维特之烦恼》,书中的维特因爱恋无果,饮弹自尽。此书风靡全球,也一度被禁,概因青年人识见尚浅,定力不足,多有效仿,即所谓的“维特效应”。
少时,曾得语文老师转赠一本《香草山》。从匆匆一过的不屑,到掩卷无言的触动,只消一个黄昏。宁萱与廷生互传书信,谈论文学,议论世事,分享生活,在交流中不断磨合贴近,灵与肉渐渐合而为一。“良人属于我,我也属于他。他在百合花中牧群羊。百合花长在香草山上,羊群长在香草山上。”香草山一如陶潜的桃花源、阮刘的天台山,是真善美之所在。如露如电,梦幻泡影;心若向往,行则必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