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语言学家方光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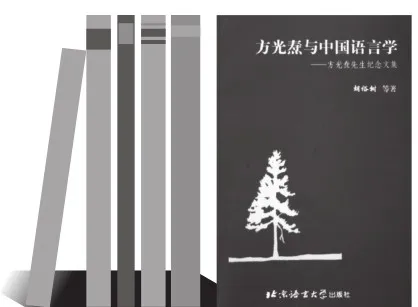
方光焘先生去世前曾对学生如是评价自己:
我可不是栖霞山高大的枫树。我反复想过了,我不过是一丛红花草,就是书上叫紫云英的,它长出小小的绿叶,开出小小的红花,就为了让农民在它最茂盛的时候,把它翻到泥土里充当绿肥,好种出粮食来。
方光焘,字曙先,浙江衢县人,是中国现代著名语言学家、文艺学家、教育家及社会活动家。他被称为中国全面系统介绍现代语言学说的第一人。方先生于1964年7月27日逝世,距今已整整60年。他的语言学思想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宝贵遗产,今天重读他的论著,依然能从中发现许多启人深思的真知灼见。
方先生的学术贡献,过去多集中在他所阐述的影响深远的语言学理论。先生如何关注、学习并应用西方理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语言学体系,也是其学术思想的重要部分,值得进一步研究。
深怕“闭门造车”
方光焘先生熟习英语、法语、俄语、日语等多种语言。1928年,他读了新刊行的日文版索绪尔《一般语言学教程》,对语言体系产生了浓厚兴趣,决定终身研究语言科学。1929年,他前往法国留学,跟随索绪尔的学生梅耶、房德里耶斯等系统学习现代语言学理论。1931年归国后,他在国内高校开设了语言学理论课程。据考证,方光焘先生是国内最早开设该课程的学者之一。方光焘先生认为,要学好语言学理论,必须密切关注现代语言学的发展,深怕“闭门造车”。1961年,朱德熙先生在《中国语文》杂志上,运用美国描写语言学方法发表了《说“的”》一文。方先生立即组织南京大学师生讨论,积极探索结构主义新方法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运用。他对朱先生的文章进行了全面总结,并提出了订正方案。
1963年,方先生关注到哥本哈根学派叶尔姆斯列夫的语言学说,他认为叶氏真正继承并发展了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并组织师生学习介绍。同时,方先生建议汉语学者应当接受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并尝试将其应用于汉语研究。但他同时指出,转换并非万能钥匙,不能无限制地使用。乔氏的理论可能还存在忽视语言与人类其他活动关系的问题。这些评价,至今仍具指导意义。方先生一贯重视语言形式研究,辩证地看待形式与意义的关系,其观点似乎比乔氏更为科学。如果方先生晚年有更多体力和精力投入现代语言学理论研究,或许会诞生中国特色的形式语言学理论。
在网络时代,中国与世界的距离缩短了,关注现代语言学理论发展的方式和途径变多了,有时候反而不那么珍惜了。方先生始终强调,在重视汉语研究的同时,也应重视外国现代语言学理论的介绍工作。作为青年学者,我们应持续关注外国语言学理论,并有选择、有目的地进行追踪研究。学界也应该加强对新的有影响力的外国语言学理论的引介。
一名之立 旬日踟蹰
几十年过去了,方光焘先生学习外国理论的方法和态度,即使到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学习。方先生在学习外国语言学著作时,格外重视翻译问题。他强调翻译不是无足轻重的小事,需要有“一名之立,旬日踟蹰”的态度。例如,他坚持将索绪尔的名著General Linguistics翻译为《一般语言学教程》,并倡导设立一般语言学学科。这一译名区别于岑麒祥、王力和高名凯等人使用的“普通语言学”,体现了他对索绪尔学说的独到理解。他认为“一般”是对个别、特殊而言的。一般语言学的核心任务在于寻求能把语言学史上的一切特殊现象都归结在里面的一般规律。吕叔湘先生赞同方先生关于“一般语言学”的坚持。“一般语言学”更能准确反映语言学的性质,体现了方先生探索一般语言规律的理论追求。
再比如翻译叶尔姆斯列夫的《语言理论导引》时,方先生的研究生、研究室的教师,懂英语的用英文版翻译,懂俄语的用俄文版翻译。集体研讨时,逐词逐句的讨论译文的准确性,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参与讨论的人甚至笑称“只有把叶尔姆斯列夫请来,让他自己说,到底是什么意思?”
翻译一直是学习外国理论的关键环节。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语言隔阂会变得越来越小,翻译变简单了,但是能否准确把握原著真意并没有变简单。我们依然需要学习方先生对原著求真务实的态度,取其真经,求其真法。
此外,方先生指出,在引进西方语言学理论时,仅凭原著中的只言片语发表议论,容易犯断章取义的错误。他主张,应当综合、联系地学习和引进现代语言学理论,方能更好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比如方先生专门研究了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分析了涂尔干的社会事实与社会意识理论对索绪尔语言观的影响。他还梳理了叶尔姆斯列夫唯心主义思想的来源,指出丹麦逻辑学传统及胡塞尔现象学对其有深刻影响。这也提醒我们,必须关注语言学理论背后的哲学、逻辑学和社会学基础,才能更好地理解应用。
研究汉语,丰富世界语言学
方光焘先生认为学习现代语言学理论,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汉语事实,阐释中国语言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为了研究中国的语言事实,丰富世界语言学,生发中国的影响世界的现代语言学理论。方先生也很好地践行了这一主张,他发起并参与了多次语言学界的争鸣讨论,很好地应用了现代语言学理论,为现代语言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20世纪30年代,陈望道、方光焘等在上海开展了中国文法革新讨论。在讨论中,方先生应用索绪尔学说,强调语法研究要区分语言和言语。他还提出要严格区分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主张建立“以同时代的、民众的共同意识做基础”的文法体系。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方光焘先生首次明确提出要区分共时和历时研究,推动了汉语研究的科学化、现代化。方先生还一再强调要重视语法体系研究,并且提出了建立语法体系的具体步骤,即“凭形态而建立范畴,集范畴而构成体系”。

在汉语词类大讨论中,方先生认为厘清基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理论研究的重中之重,要把握理论的真精神,重视基础概念研究。他还提醒学者在应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时,切不可引用理论的片言只句来回护或掩盖自己的错误。上世纪50年代末,方先生发起语言与言语学术讨论,他认为索绪尔从混质的言语活动中认清语言,这是正确且必要的,但是将语言和言语对立起来是错误的。在此次讨论中,方先生进一步明确了现代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推动了语言科学的现代化。
方先生尤其重视在正确语言观指导下的方法论原则。他指出,语言研究者要重视一般原理,不因具体语言的特殊性而排斥语言学的一般原理,也不排除个别的具体语言表现。他还认为语言研究要重视口头语言,口语是野生的,茁壮的,生动活泼的,是丰富的园地,是最能表意的,是研究语言最2699bc69f9cd72caaed30e900d6075bd重要的材料。他延续联系的观点,重视语言的体系,提出研究语法不以个别的词、孤立的词为对象,而是以词与词、词素与词素、词与词素、词与词组、词组与词组的结合关系为对象。
方先生还被称为“被语言学遮蔽的新文学作家”。1921年,他在日本留学期间,与郁达夫、郭沫若等人在宿舍创立了新文学团体——创造社。回国后,他创作了《疟疾》《曼蓝之死》等多部文学作品。方先生在高校同时开设文艺学理论与语言学理论两门课程,在今天的中文系,这已难以想象。身为语言学家、文学家、文艺评论家的方光焘先生,曾从促进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的角度评论作家与语言的关系。方先生认为初学写作者应该从认清语言的性质和明白语言的规律做起,应把注意语言、深刻地认识语言、正确的使用语言视为作家的主要任务。方先生的多重身份拓宽了他对语言的认识。
抗战时期,生活困顿的方光焘,时常看着自己从法国背回来的一箱箱语言学书籍,感叹自己何时能有现代语言学的传人。即便在身体疲弱病重时,他仍鼓励学生多提问题,“多利用我”。方先生确如紫云英一样,做了中国现代语言学发展的“肥料”,他的学生胡裕树、徐思益、吴为章、龚千炎、王希杰、于根元等,沿着他的研究思路一直在前进。世界现代语言学大师索绪尔的经典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是由他的学生根据讲稿整理而成。或许是历史的巧合,中国现代语言学宗师方光焘的主要著作,如《语法论稿》和《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等,也是由他的学生根据课堂笔记整理出版,呈现给学术界的。
方光焘先生对生活和学术都十分认真,王希杰曾形容他的学术风格为“求真、较真”。对于现代语言学,方先生求真引进,认真应用,创造性地吸收改进,为我们学习和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树立了典范。
国家社科基金倡导研究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的学术思想、中国语言学思想史。以方光焘先生为代表的语言学家,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传承与发展呕心沥血,回顾前辈们引进西方理论建构中国现代语言学理论体系的历史,阐释他们的学术思想,书写中国语言学思想史,是当下语言学界的重要课题。
(作者简介:王文豪,广州大学国家语言服务与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研究中心研究员;郭熙,广州大学特聘客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