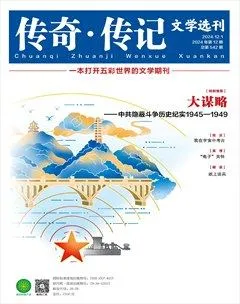鉴玉师
这世上的事,要说奇怪,有时真是怪得离谱。比如说临州,本不产玉,也没玉雕师,却出鉴玉师。有些大玉商拿到货,心里没底,就带着货来到临州,请鉴玉师掌眼,定好价,才敢放开了去吆喝叫卖,否则心虚。
临州四大鉴玉家族,滕、谷、刘、辛,谷家排第二。谷家这辈的掌事人名叫谷维查,其鉴玉的本事已出神入化。他开了一家铺子,虽然不大,但生意红火,收入可观,小日子过得也不错。随着儿子们逐渐长大,他有了新想法。
谷维查共有三个儿子:长子谷俊明,次子谷俊朗,三子谷俊丰。谷俊明和谷俊朗都跟着他做生意,也跟着他学了鉴玉的本事,谷俊丰一直在念书,想要考取功名。后来,谷俊明成了家,又学了些本事,就有了分家的心思。谷维查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到异地开一个分号,交给谷俊朗打理。两个铺子各赚各的,赚多少看各自的本事,真来了贵客,两边的货物还能互通,两全其美。
谷维查想把新铺子开在保定。保定的达官贵人多,有钱的人也多,好玉才能卖到好价钱。但销路到底如何,还得先去保定看看。谷维查把店铺交给谷俊明打理,自己带着谷俊朗上路了。两个人各骑一头毛驴,赶往保定。
七八天后,他们来到正阳,谷俊朗却病倒了。此时正是六月,艳阳高照,谷俊朗却冷得打摆子,浑身起鸡皮疙瘩,盖了两层被子还说冷。谷维查赶紧请了当地最有名的苏郎中来给儿子看病。苏郎中一番望闻问切,诊断谷俊朗患了寒症,即刻开了方子。谷维查按方抓药,熬好给谷俊朗服下。七天后,谷俊朗的寒症治好了,却又得了一种怪病:白天一切如常,到了晚上头疼得直用脑袋撞墙。苏郎中又给他开了几服药,却不见丝毫好转。苏郎中眉头紧蹙,说此症太怪,他治不了,附近几县的郎中也治不了,唯有一人或能治,那就是河间府的名医关满堂。不过,关满堂诊费很高,请他来治,得花费不少银子。谷维查哪还在乎银子呀,他托苏郎中照看儿子,自己骑着毛驴赶往河间府。
关满堂听说要去正阳问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说自己身体虚弱,眼下又热,只怕还没赶到正阳,自己就先病了。再就是他的这个医馆求诊者众多,不能耽误那么多人的病情。谷维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我儿的病,只有先生能治,恳请先生救他!路上我一定尽心照顾,不让先生受一点儿委屈。”说着,他又掏出一锭银子。关满堂不能说不喜欢银子,又因病情特殊,他很想一试身手,就点头应了。谷维查忙去雇了骡轿,又置办了一应干粮饮品,恭请关满堂上路。
这一路关满堂只在早晚凉快时走一段,夜不走午不走,五六天后才到正阳。手一搭上谷俊朗的脉,关满堂倒吸了一口凉气。他忙挽起谷俊朗的裤脚,看见小腿上有一个红色的包,点点头道:“就是它了。”谷维查忙问:“先生,这是啥病?”关满堂说,时下有一种蜱虫,十分活跃,毒性很大,若被它咬了,轻则头疼欲裂,重则命丧黄泉。这个包便是蜱虫所咬导致。谷俊朗白天没症状夜晚却严重,想必跟自身体质有关。如今,这蜱虫之毒已入骨髓,治起来很难,而且花费巨大。关满堂开下三张方子,嘱咐谷维查头半个月用第一张,下半月用第二张,之后再用第三张。诊治完毕,关满堂就坐上骡轿走了。
谷维查赶紧到药铺抓药。小伙计看完方子,没去抓药,而是说道:“请你先把药钱交了。”谷维查说:“你还没给我抓药,我凭啥给你药钱?天下的药铺都没这规矩吧!”小伙计无奈地笑了笑,说道:“大叔,你这药太贵了,我怕你没带那么多银子。”谷维查暗暗一惊,问:“这几服药能要多少银子?”小伙计说:“一服药是一两五钱。”谷维查脱口而出:“你们这是抢钱!”小伙计讪讪地笑笑说:“我也觉得贵。要不,你到别的药铺去问问?”谷维查暗想,小伙计敢这么说,说明这药真是这个价。他掏出两锭银子,说道:“抓吧。”
抓完药,谷维查绕道去了脚夫行,雇人给家里送信儿,说明情况,让他们送二百两银子过来。谷俊朗这病不知道要花多少银子,更何况他们还得住店吃喝,谷维查带的银两根本不够。
过了七八天,脚夫回来,说信已送到,但没捎回银子。谷维查暗想,大儿子做事还是谨慎,怕脚夫贪占银子,故而不用外人,日后会派靠得住的伙计送。可他望穿双眼,也没见到伙计来送银子,而他兜里的银子已见了底。此时第一张方子用完,谷俊朗病症见轻,夜里只疼两个多时辰了,便出主意说:“咱往家走吧。”谷维查却摇了摇头。谷俊朗身体虚弱,不宜赶路。
谷维查又来到脚夫行,请脚夫再给家里送信。他转身来到金兴典当行,小心翼翼地从怀里掏出一个锦盒,里面是一只水润碧绿的玉貔貅。他说:“我这宝贝只当两个月。你们精心收好,两个月后我必定来取,可不能有丝毫差池。”
掌柜的瞥了一眼玉貔貅,摆摆手说:“这位兄弟,你这宝贝我们不收。”谷维查愣住了,以为自己听错了,反问道:“你说啥?”掌柜的重复了一遍。谷维查难以置信,两眼发红:“你可知我这宝贝值多少银子?”掌柜的说道:“兄弟啊,值多少银子,那得分人。在你眼里,你这宝贝可能值一座金山,可对我来说,它没用,那就不值啥银子了。要我说,你还是把你的宝贝收好了,或者到别的地方去问问吧。”谷维查把玉貔貅举起来:“你睁大眼睛看看,这玉的水头足不足,这颜色掺没掺一点儿瑕疵?不瞒你说,要不是缺钱了,我这宝贝,看都不会让你看一眼。”掌柜的仍是一副波澜不惊的表情。谷维查问:“你知道我是谁不?”掌柜的摇了摇头,淡淡地说道:“你是谁不重要。我再说一遍,你这宝贝,我不收。”
谷维查险些被气死。他把玉貔貅收好,又在县城里寻到一家典当行。这家典当行跟金兴的做派如出一辙。县城里就这两家典当行,宝贝出不了手,筹不到银子,下一步可咋办呢?谷维查垂头丧气地回到客栈,却不见谷俊朗的影子,他出去找了一圈儿也没找到。
天黑了,谷俊朗才乐颠颠地回来,一进门,就掏出一百文钱放到谷维查面前,笑呵呵地说:“爹,我挣着钱了!”谷维查问:“咋挣的?”谷俊朗说,他闲来无事,骑着毛驴外出闲逛,到城东的五里店时,觉得口渴,就到村口一家碾坊去讨水喝。那家碾坊的人在推磨,看到他的毛驴,两眼放光,愿用一百文钱租一天,他当即同意了。碾坊的人跟他说好,明日就还毛驴。一百文钱虽然不多,但供住店和吃喝还能有余。他身上已有了些力气,再帮着干干活儿,还能多挣一些。
谷维查忙说:“你伸出手来给我看看。”
谷俊朗伸出手,谷维查一看,当即勃然大怒:“你这个浑球儿,不知道你的手该干什么吗?帮人家推磨赶驴,把手弄糙了,还怎么鉴玉?你这是自毁前程!”鉴玉师鉴玉,不光凭眼睛看,还得靠手摸。谷维查的本事就是手一摸就知道玉的质地,玉有几分杂质,哪里隐藏着瑕疵,是否作假。鉴玉师的手温润细腻才能保持触感敏锐。干了粗活,手糙了,就不能鉴玉了。
谷俊朗小声说道:“我得先挣到钱,看好了病,保住了命,才能说别的。再说,我也不想当鉴玉师了。”谷维查愕然地睁大了眼睛,问:“你说什么?”谷俊朗说:“我不想当鉴玉师了。天天看石头,烦都烦死了。”谷维查再也忍不住了,大声吼道:“这是手艺,是本事,是让你吃饱饭过好日子的技能。别人要花钱才能学,我白教你,你还不学了?你想明白了再跟我说话!”
谷俊朗上炕躺下了。
半夜,谷维查爬起来给儿子喂药,却发现身边空空如也,儿子早已不知去向。他跑到院里,值更的伙计说谷俊朗早就走了。谷维查赶紧骑上毛驴去追,可哪里还有儿子的影子?寻了几日,也不见儿子,更何况兜里早已空了,他只好回家。
夫人没见到儿子,吓了一大跳,还以为儿子不治而亡了,谷维查把儿子半夜溜走的事讲了。夫人抹着眼泪絮叨:“他还生着病呢,这一走,谁能管他呢?”谷维查气急败坏地说:“他自己不想活,谁救得了他?等他想活的时候,自然就回来了!”他想起一件事,忙问谷俊明:“我两次雇脚夫给你捎信儿,说俊朗看病得花银子,你怎么不给送去?”
谷俊明哭丧着脸说,就在谷维查带着谷俊朗走后不久,铺子里来了两个枣强富商,说老母亲要过生日,特意挑选了几件贵重首饰当贺礼。但他们还要外出采买,问谷俊明能否送货上门,他们先把货款和路费付了。谷俊明很想赚这笔钱,就爽快地答应了。他怕途中出岔子,就带着一个伙计亲自送去。一路上他小心翼翼,不敢有丝毫懈怠。可到了枣强,那几件首饰居然都碎裂了。因为耽误了给老母亲送生日寿礼,富商很生气,要把谷俊明送官,谷俊明好说歹说,答应双倍赔付货款,人家才作罢。谷俊明回家后东挪西借,凑齐了银子,才把富商打发走。他接到脚夫传来的信儿,很是焦急,可家里没银子,也借不来,想把玉器贱卖,一时也卖不出去,送银子的事就耽搁下来了。
谷维查很是吃惊:“全碎了?怎么会全碎了?”
谷俊明说:“我也不知道啊。”
谷维查又让谷俊明把那两个富商挑玉的经过原原本本地讲给他听。谷俊明就一五一十地讲了。谷维查蹙着眉头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个所以然。要说那两个富商在挑玉的时候神不知鬼不觉地做了手脚,让玉器在收货时才碎裂,这种手段他闻所未闻。玉倒是有三禁四怕,但只会影响光泽和成色,并不会碎裂。谷俊明忽然又想起一事,那两个富商走后,他触摸了一下桌子,觉得桌子特别凉,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谷维查惊问:“他们挑玉件的时候,手中还拿着东西?”谷俊明说他们手上各拿着一个厚重的锦包,时刻不离手,应该是非常贵重的东西,就是在挑玉件的时候,也将包放在桌上,玉件也是放到锦包上挑的。谷俊明长了个心眼儿,怕他们偷藏,还特意每次只拿两件让他们挑,挑中的放在一旁,没挑中的收起来,一件都没丢,也没被换过。谷维查思忖片刻,说道:“问题应该就出在那两个锦包上。包里应该放着极寒之物,只有这样,你在他们走后很久再触碰桌子还会觉得凉。以后咱们还是坚持店内交易,绝不送货上门,免得再被人算计。”谷俊明连忙点头。
谷维查一直以为,谷俊朗在外面混不下去了,就会乖乖回来,跟着他继续学鉴玉。谷俊朗聪明伶俐,一学就会,要真塌心学,肯定比谷俊明学得好。学好了手艺,还怕没饭吃?可谷俊朗一直没有回来。谷维查心里非常惦记他,托人到正阳去打听,有从正阳过来的人他也细加询问,却没有一点儿消息。
接下来的几年,临州连年遭遇风灾,田里的收成锐减,百姓生活困苦,有的人甚至拿起打狗棒,外出讨饭了。谷家家境还算殷实,但也架不住粮价飞涨,店铺又没啥生意,坐吃山空,这么下去,也扛不了多久了。谷维查每天坐在铺子里看着那些玉件犯愁。他和大儿子谷俊明都是鉴玉师,除了鉴玉,啥都不会。三儿子谷俊丰在私塾教书,挣的那两葫芦醋钱,养活自己都不容易。但一大家子人张口等着吃饭,这可怎么办呢?
有一天,门外忽然响起蹄声。谷维查以为来了大主顾,赶紧出门看,却见几辆毛驴车在铺子前停住了,谷俊朗从车上跳下来,见到谷维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连磕了三个响头,这才抬起头来,说道:“爹,我来接你们了。”谷维查大步奔过去,一把抓住了谷俊朗的胳膊,细细打量他。几年没见,谷俊朗身体变结实了,人也更成熟了。谷维查颤着声儿问道:“你那病,好了?”谷俊朗说:“好啦!你看我这身子骨,结实着呢!”谷维查拉着儿子进门。谷俊朗冲那几个车把式招手:“都进来吧!”
一家人相见,不觉喜出望外。尤其是谷俊朗他娘,更是哭得稀里哗啦。谷维查拦住了她,对儿子说道:“快说说,这几年你是怎么过的!”
谷俊朗讲开了。那天他跟谷维查吵了一架,半夜逃走,其实是想让老爹丢下他走人,两个人不能都困死在正阳啊。老爹走后,他得活着,还得吃药,怎么挣钱呢?他想起了那头毛驴。于是,他又去了碾坊,帮人家推磨,不仅挣了一百五十文钱,晚上还能在那家住宿。
后来他才得知,在正阳,牲口奇缺,他这头毛驴简直成了宝贝。因为河间府那边兴起了驴肉火烧,正阳的驴就跟着倒了霉,先是被窃贼偷了高价卖到河间,后来养驴的人家怕驴被偷,干脆自己去卖。时间一长,正阳就没有毛驴了。谷俊朗暗想,要是能赶批毛驴来,肯定能狠赚一笔。
谷俊朗吃完一个月的药后,再拿着第三张方子去抓药时,药价便宜了不少。关满堂果然是神医,谷俊朗吃完最后一服药,病彻底好了,就带着毛驴四处给人家帮工,很快就赚到了一笔钱。他又说动一位富人,借到一笔钱,而后到口外买了一百头毛驴赶回去,白天出租,晚上收回来统一看管。如此,他很快就富裕起来,又组建了一个毛驴车队,专门给人家运送货物,有做不完的生意,钱当然没少赚,如今已买了地,也盖了房子。
谷俊朗抬起手来,手上满是老茧,很是粗糙。他不觉赧然:“爹,我这手天天搬货推车的,都快磨成石头了,再也没办法鉴玉了。”谷维查大声说道:“我儿子靠自己的本事吃饭,我心里美得很呢!”
简单收拾了些家当,装上了车,谷维查又把那些玉件收拢,藏进了夹壁墙里。谷俊朗问:“爹,那些名贵的玉件,你不带走啊?别让人偷了。”谷维查摇了摇头,说:“不带了。路上颠簸,伤了碎了,我心疼。这年月,大家都去找食儿吃了,谁还会惦记这不当吃不当喝的东西?走吧!”
锁好门上了车,谷维查扭头看着渐远的家,无声地叹了口气,却说不清是为了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