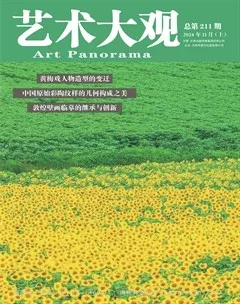论中国画与书法的关系
摘要:中国画与书法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代表了中华民族的艺术追求,二者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受科技、西画等因素的影响,当代艺术逐渐趋向材质化,本文重点探讨中国画与书法的关系,主要从书画同源、笔墨相通、意境相通、书画同心、审美统一等方面展开分析,为现代艺术创作提供有效参考,一方面用书法为中国画注入灵魂,避免淡化、消解其哲学性;另一方面用中国画为书法提供艺术指导,增强其表现力。
关键词:中国画;书法;关联性
中国画强调意境和气韵生动,追求超越形似的精神境界,主要以线条为造型手段,通过线条的粗细、浓淡、干湿、快慢等变化,表现物体的轮廓、形态和质感。同时,注重笔墨的表现力,以墨色的浓淡、干湿、虚实,以及笔触的轻重、快慢、顿挫,突出画面的节奏感和韵律感;书法是强调笔墨纸砚的运用和笔法的精妙,运笔应如行云流水般自如,同时字形变化多端,风格各异。二者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在技法、艺术追求、文化传承等方面都存在联系,应合理把握二者的关系,以便更好地掌握其艺术精髓,做到灵活应用。
一、中国画与书法兼容并蓄的发展情况
(一)传统笔墨、笔法的促进作用
传统的笔墨、笔法是推进中国画与书法发展的重要基础,《画论》中将书画笔迹称为骨,认为作画最忌描、抹、涂,即入笔后“一波三折”,横拖直拉,光有墨迹没有用笔技法。南朝画家陆探微,是以书法入画的第一人,运用了东汉张芝草书的笔法,做到了“六法尽该”,即因“穷理尽性”而使画面收到“气韵生动”的效果。总的来说,中国画与书法同源而不同构,中国画需要完成画面上的题诗、出处、落款用笔,书法需要用中国画来融合自身的艺术风格,蕴含着中华民族传统审美观。
(二)当代笔墨、笔法的促进作用
所谓“善书者必善画”,中国画与书法互相影响、相互作用。在当代文化中,笔墨的传统精神让中国画与书法焕发出新的活力,笔性理论是其中的代表,指笔本身的物质性与科学性所决定的特性。“翰不虚动,下必有由”,了解并顺应笔性,是掌握书法和绘画技艺的基础。比如,毛笔由兽毫制成,具有软性,使用时需顺其性、合其理;毛笔的笔头呈圆锥体,需避免扭折以保持笔力的均匀;毛笔的笔毫有主、副之分,书写时主毫立骨抱筋,副毫得肌肤之丽;毛笔蘸墨书写时,如笔毫相对齐顺,墨就容易从笔跟流向笔尖,行笔也易饱满厚实[1]。
(三)线条使作品造型趋向成熟
中国画与书法以线条为主要表现手段,是创作的基本语言,一方面通过线条的粗细、曲折、枯湿、浓淡等变化,塑造出丰富多样的物象形态,使中国画充满生机和韵律感;另一方面通过运笔的技巧和力度的掌握,使线条呈现出质感、力感、立体感、动感、节奏感等多种美感特征,形成各具特色的书法风格。线条的艺术成就在一定程度上也强调了中国画与书法的同质性。
二、中国画与书法的内在联系
(一)书画同源
中国画与书法的书画同源理论可上溯到唐代,张彦远所著的《历代名画记》强调了三点,一是绘画与书法的起源相同,都是源于象形。最早的甲骨文是简单的象形,而彩陶、岩画等最早的图画也是简单的象形。但之后文字逐渐发展成了抽象的符号,绘画则从简单的象形转为更为复杂的象形,二者分道扬镳。二是绘画与书法的功能都是教化,让人们深入理解圣人的思想。三是绘画与书法的用笔技法相同,张彦远认为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吴道子的作画笔法与优秀书法的笔法完全一致,本质上是强调在抽象理法上的相通,即“顿挫转折,气脉相连”。
到了元代,书画同源又发展出了新的内涵。赵孟頫的题画诗强调,绘画用笔在理法和具体技法上都与书法相同,但限于枯木竹石、简率山水等题材,如采用飞白法突出石头,采用籀书突出枯木,采用八法突出竹子的竿、节、枝、叶等;到了晚明,书画同源出现质变,虚通转为实同,董其昌、徐渭等人强调“书法即画法”,无论是正统派还是野逸派,都采用书法性绘画模式,即以笔墨为中心,形象化服务于笔墨的抒写,从根本上颠覆了绘画的规范。
(二)笔墨相通
1.用笔
中国画与书法都需要使用毛笔,“用笔千古不易”,二者在运笔规律、法度等方面具有一致性,讲究力度美、气韵美。笔法包括下笔、行笔和收笔,需充分利用笔毫柔软、有弹性的特点,使运锋铺毫首尾完善,气势流畅,笔力丰盈,使笔毫在顺逆相交、疾涩相顾、轻重相间的情况下运行。其中,书法的用笔可归纳为中锋、偏锋、藏锋、露锋、逆锋、顺锋、方笔、圆笔等,而中国画的笔法可归纳为平笔、留笔、圆笔、重笔、变笔五种。二者相互联系、相互重叠,如书法的圆笔是指无棱角者,在点画线条的起止转折上,运用“提笔圆转”的方法形成圆润之势,使之不露筋骨,内含浑厚遒劲,即“转以成圆”;中国画则从书法中提炼出圆笔笔法,指线条圆浑沉厚,富有弹性,树无寸直,石也多圆笔画法。宾翁认为,应做到如“折钗股”“莼菜条”,连绵盘旋,纯任自然,笔法线条婀娜中保持刚劲,圆浑润丽而不能流于柔媚[2]。
2.用墨
(1)浓墨,即墨中掺水较少,色度较深。书法创作强调浓墨最见精神,特别是篆书、隶书、楷书等正体书,如苏轼对墨的要求是“光清不浮,湛湛然如小儿一睛”,认为墨不但要黑,而且要有光泽,其大多书法作品都有一种浓墨淋漓的艺术效果。在中国画中则可以用来表现物象的阴暗面、凹陷处和近的景物。
(2)淡墨,即墨中掺水较多,色度较浅。在书法创作中淡墨适合表现清淡幽远的意境,如明代董其昌、近人林散先生都擅长用淡墨,具有“干裂秋风,润含春雨”这种深远朦胧的效果。在中国画中则用于表现物体的向光面、凸出处和远景,强调“明净无渣、淡不浮薄”,一般用于描绘峰峦出没、云雾显晦、岚色郁苍等。
(3)焦墨,指墨水浓重,极少水分,用笔枯干滞涩凝重,但要达到焦中蕴含滋润的效果。在书法创作中有画龙点睛之妙,像干皴之笔,明代徐谓、清人虚谷擅等书法家较为擅长此法;在中国画中,主要起到点苔、点睛,以及调整画面轻重的作用,要做到“枯而不润,刚而不柔,即入野狐”。
(4)宿墨,即使用隔一日或数日的墨汁。在书法创作中,清人王铎擅用的涨墨是宿墨中的一种,可呈现出空灵、简淡的美感。在中国画中,宿墨作画易枯润、苍茫,常用于最后一道墨,使墨中更黑,黑中见亮,加强黑白对比,使画面更加神采焕发[3]。
3.书法结体与绘画物象
书法结体与绘画物象的联系在于二者都是将固定结构、固定形态进行再创造的艺术形式,属于借物表意的半抽象艺术,不仅赋予了艺术作品更大的表现力和灵活性,也为观者提供了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和审美体验。书法注重在掌握汉字基本结构规律的基础上,进行个性化的再塑造。为了达意,书法家会对笔画进行夸大或缩小处理,体现在笔画的大小、粗细、形态、方向和力度上,如在清代朱耷的《河上花图卷题诗》中,采用移位夸张手法形成奇险的构图,具有强烈的对比美,但整体仍注重整体性和和谐性,各个笔画之间相互呼应、协调一致;中国画的物象绘画不完全受局限,也不追求形似,为写心中之意,会对物象进行抽象再塑造,如在陈洪绶的《荷花鸳鸯图》中,采用再塑造手法抽象出了石头、荷花的轮廓。
4.章法
中国画的书法章法主要体现在疏和密、虚和实两方面。
(1)书法中的疏密主要是指笔画、字与字之间空间分布的松紧程度。在王羲之的《兰亭序》中,大量使用省略、合并等手法,使得字与字、笔画与笔画之间形成了鲜明的疏密对比。比如,某些字中故意将某些笔画拉长或缩短,使得字内部的空间分布变得疏密有致,增强了字的动态感和表现力。中国画中的疏密主要是指形式排布的聚与散,如卢辅圣强调在画树时,要注意丛树的形式美通过密与疏的对比,树与树之间的高下映衬和前后穿插,体现丛树的深度感[4]。
(2)书法的虚实主要体现在笔画与墨色的对比上,苏东坡擅长大面积用墨,形成墨块效果,同时通过笔画的轻重缓急、墨色的干湿变化来营造虚实效果,使得作品在整体上既有厚重的质感,又有轻盈的灵动之感。黄宾虹曾强调古人的画诀是“实处易,虚处难”,画黑其实是为了彰显白,画密其实是为了彰显疏,其山水画中山用墨很重,云雾、道路和溪流的空白处和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像是在山上开了一扇扇“透气窗”,整个画面因此变得生动。
5.气韵
书法作品中的势指连续书写的节奏变化,如轻重快慢、离合断续等。形则表现为一点如高山坠石,一横如千里阵云,形势合一后是生命的律动,进而展现了书法的气韵。中国画也是如此,南朝谢赫《古画品录》强调的“六法”首先就是“气韵生动”,是形势合一的表现。以山石画为例,清代王原祁将山头的折塔转换称为龙脉,即山石的造型及其组合关系必须表现出“过接映带”的龙脉。画面形象的笔墨形态要“得势之引发,顺其势而得其气”。
(三)意境相通
中国画与书法的意境之美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中,融合了儒家、佛家、道家等哲学思想,形成了独具魅力的意境追求。中式审美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在艺术创作中,即为形与神、虚与实、动与静、有与无的统一。蔡小石在《拜石房词》序中将意境分为三个层次,包括“象内之境”“境中之意”“境内之道”。
1.象内之境具有鲜明的感官性、再现性,书法所呈现的音乐般节奏感和线条本身的力度神采,中国画运用墨色的浓淡干湿、线条的疏密曲直,都具有形式上的美感,是意境美生成的基石[5]。
2.境中之意是指主体与客体的融合,即书写与绘画艺术所表现的思想感情与创作内容相互应和。书法家对天地万物形体美、动态美有不同的心理感受,并将其展现在作品中,王羲之的《兰亭序》洋溢着清新、恬淡、自然的气息,整片序言疏朗简净,而《丧乱帖》则充满了沉痛与悲愤。清“四僧”都擅长山水画,但艺术风格存在较大差异性,石涛奇肆超逸,八大山人简略精练,髡残苍左淳雅,弘仁高简幽疏,虽然都在描绘自然元素,但情思不同,审美追求也随之发生变化。
3.境内之道强调了中国人朴素、传统的宇宙意识,“于空寂处见流行,于流行处见空寂”。作为意境的最高层次,蕴含着“无”的哲学。优秀的书法家会摒弃刻意求工的匠气,忘掉线条,归于“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如草书摆脱了书法实用性,在线条游动中暗藏着无限生机和精神意向,“奔蛇走虺势入座,骤雨旋风声满堂”。宋代马远的《寒江独钓图》运用古朴的笔法,在画面中留存了大片空白,通过小舟与大江的对照、虚与实的衬托,凸显“清空寥旷,烟波浩渺”的意境。
(四)书画同心
中国画与书法不仅仅是记录工具,更是人们抒发感情、表达思想的媒介。这种同心关系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抒发情感。书法家通过不同的创作技巧表达自身情感与心境,如唐代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文稿笔法奔放不羁,墨色浓淡干湿变化丰富,充分表达了颜真卿对侄子的深切怀念和对战乱的愤慨之情。明代徐渭以大写意的手法创作了《墨葡萄图》,笔墨酣畅淋漓,墨色浓淡干湿相间,表现出一种不羁与狂放的个性,同时也传达了画家对人生苦难的感慨与抗争。二是借物喻人。在山水画中,山象征坚韧不拔、稳重厚实的君子形象,水则被比喻为智慧清明、包容万物的仁者形象。花鸟画中的梅花象征着坚韧不拔、高洁自守的品格;竹子则代表着坚韧不拔、虚怀若谷的精神,与书法中借景物抒内心之情感的手法相同。
(五)审美统一
中国画与书法在审美方面具有统一性,主要体现在表现内容、表现形式、表现方法三方面。
1.表现内容。中国画强调“外事造化,中得心源”,如郑板桥曾提出“绘竹论”,先观察“眼中之竹”,将其作为激发创作欲望的感性素材,然后在情感观照下,将“眼中之竹”取舍和处理为另一种意象,随机生发,因势利导,最后画出“胸中之竹”。书法则强调“书肇于自然”,且“书者心画也”,认为书法本质上也是经过观察、理解、取舍和变形之后得到的一种心象。
2.表现形式。书法艺术要依靠阴阳来表现意象,“禀阴阳而动静,体万物以成形”,具体体现在各种相反相成的对比关系上,如用笔的轻和重、墨色的浓和淡、结体的大和小等,都具备阴阳特征。中国画中的山水树木、亭台楼阁、舟楫车马,其构图、造型、用墨都可以用来营造阴阳对比、处理阴阳关系。
3.表现方法。书法创作强调作品是有生命的,应当根据作品的生成逻辑来自然展开,具体方法是按照以他平他的原则不断生发,点画生结体,结体生章法,最后成为相对独立的整体。绘画创作也强调“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需将创作意象落到纸上,以激发作品的生命力。
三、结束语
书法和中国画都是独立的艺术,但具有内在的联系性。要做到以书入画、以画入书,应依照“要知书画本来同”“画法关通书法律”等理念,深入挖掘二者的相通点,以便将对方的内容、形式和方法落实到艺术创作中,做到形势兼备,气韵生动,真正突破造型的束缚。
参考文献:
[1]金泽阳.墨韵笔意:中国画与书法的同源性探析[J].天工,2024,(29):58-60.
[2]杨旸.浅析中国画线条与书法线条的关系——以人物画为例[J].参花,2024,(13):89-91.
[3]陈龙国.书法对中国画的影响及二者的融合发展途径探索[J].艺术评鉴,2024,(07):27-32.
[4]张海江.从书法看中国画笔墨形式及色彩的审美意蕴[J].色彩,2024,(03):74-76.
[5]吴修杰.写意中国画与书法线条的融合与碰撞[J].艺术大观,2023,(23):63-65.
作者简介:毛子欣(2002-),男,黑龙江绥化人,硕士在读,从事美术与书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