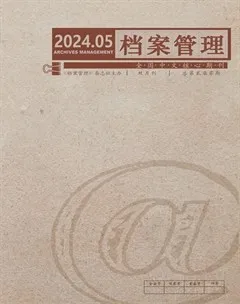关于买卖契约文书专有名词“质剂”起源的历史语言学研究

摘 要:在买卖契约文书溯源研究中,学术界多已认识到在买卖契约文书发展演变史上居于源头位置的是“质剂”,与其有关的记载最早见于《周礼》。但《周礼》本身并非全为可靠信史,其中混杂有作者的理想设计等非现实内容,既有研究较普遍存在“未加考证或辨析便将《周礼》等同于西周史实”等谬误。针对“质剂”一词的起源及其嬗变为买卖契约文书专有名词的过程等问题,以二重证据法为贯穿,遵循历史语言学研究法的逻辑进路,阐明单音节名词“质”和“剂”的起源与内涵,辨析“质要”“质律”等更早出现的契券泛称类双音节名词与“质剂”的异同,指出“质剂”一词不是被记载于《周礼》而是起源于《周礼》,是我国古代用以指代买卖契约文书的第一个专有名词。该研究既有助于解决学界关于“质剂”存在的误读误用和似是而非的问题,也对现代合同制度尤其是电子合同制度之构建与完善以及文书档案管理制度改革具有显著的借鉴与促进效用。
关键词:买卖契约文书;质剂;《周礼》;文档名词;历史语言学;文书档案史
1 引言
名称,是认识和研究事物的基础。按照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历史语言学的一般理论,凡是起源较早且存续较久的事物,虽其本质和核心特征未有更易,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能存在不同的名称,如中国有“华夏”“神州”“九州”等多个代称。[1]之于买卖契约文书,研究发现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质剂”“下手书”“画指券”“红契”等多种不同称谓。其中,“质剂”是我国历史上目前有文献可征、有史料可考的用以指代买卖契约文书的第一个专有名词。因此,厘清“质剂”一词的起源,准确界定“质剂”的概念,是买卖契约文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当前,与买卖契约文书相关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种维度:一是宏观的发展演变历程研究,如张传玺著作《契约史买地券研究》之“中国古代契约发展的四个阶段”[2]、乜小红专著《中国古代契约发展简史》之“买卖券契的分类与演化”[3]和白小平《中国古代买卖契约研究》[4]等;二是中观的断代史视角下的买卖契约文书研究,如宋代[5]、清代[6]等某一历史时期的买卖契约研究;三是微观的对买卖契约文书的形式[7]、类型和构成要件[8]等具体问题的研究。概括而言,在对买卖契约文书研究的过程中,既有成果大都已经认识到“质剂”在买卖契约文书发展演变史上居于源头位置,且在“质剂”的形式、作用和保管等具体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目前所见,从历史语言学角度对“质剂”作出针对性研究的,主要是笔者的研究团队。笔者在以往的研究中将“质剂”的性质界定为合同类法律文书,[9]指出“质剂”是《周礼》专有且被后世延续使用的文档名词之一,[10]并对《周礼》在内容上混杂先秦史实和作者设计的双重性以及《周礼》对文书档案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史料学价值做出了有效论证,[11,12]但“质剂”一词是如何起源的、它的产生对买卖契约文书有何重要意义、在《周礼》之前是否存在与“质剂”近似的文档名词,以及《周礼》对“质剂”的记载是否有同时期典籍或考古实物的证明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彼时未及深入考证。同时,笔者检索发现迄今仍未有针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成果出现。学术界对“质剂”一词起源问题的研究长期停滞不前,且存在将《周礼》记载全部视为信史而不加考证或辨析等错误现象。据此,笔者拟以此文对上述问题展开系统考证和论述。
2 肇始:单音节名词“质”和“剂”的产生
研究“质剂”一词的起源与内涵,首先需从了解“质”“剂”这两个组词词素的起源与含义开始。原因有二:
第一,从历史语言学角度分析,“质剂”一词是由“质”和“剂”这两个并列的单音节名词组合在一起所形成的联合式双音节名词。因此,了解“质”和“剂”这两个词素的含义与关系,以及它们组合的背景、原因,是研究“质剂”一词起源问题的关键与前提。
第二,在先秦时期的买卖活动中,“质剂”也是分为“质”和“剂”两种形式而分别使用的。《周礼·地官·质人》有谓:“凡卖儥者质剂焉,大市以质,小市以剂。”[13]大市,即“人民”(指奴婢)、牛马等大额买卖,用“质”;小市,即兵器、珍异等小额买卖,用“剂”。郑玄注《周礼·天官·小宰》“七曰听卖买以质剂”[14]曰:“质剂,谓两书一札,同而别之,长曰质,短曰剂。”[15]即先秦时期的买卖契约统称为“质剂”,因交易物品不同而有长短券之别,长券称质,短券称剂。与上述大小额买卖结合而论,便是“人民”、牛马等大额买卖用长券之质,兵器、珍异等小额买卖用短券之剂,即郑玄所云:“大市,人民、马牛之属,用长券;小市,兵器、珍异之物,用短券”,[16]也正是孙诒让所释“人畜等物重贾贵,则用长券之质;器用等物轻贾贱,则用短券之剂”。[17]由此,考证并阐明“质”“剂”这两个元词汇之起源与含义,是为厘清“质剂”起源问题的关键与前提。
2.1 “质”字考源
2.1.1 “质”字的起源与本义。“质”字,目前可考的最早的出处是在西周晚期的金文所见之“ ”“井人 鐘”(集成编号109.1,[18]111.1[19])、“ 其钟”(集成编号187,[20]189,[21]192[22])等西周晚期的青铜器上所刻金文,均有见“ ”字 ,例如“井人 鐘”刻有“克 厥德”[23]之文。其后,在春秋、战国的金文,以及战国晚期和秦代的竹简等目前已出土文献中均有发现“质”字,如睡虎地秦简所见“ ”,[24]表明“质”字在这几个历史时期被持续沿用。
我国辞书之祖《尔雅》将“质”与“功、绩、登、平、明、考、就”七个字并列,同释为“成也”。[25]郭璞注“质”时,引用《诗经》“质尔民人”之文以证“质”在先秦确有“成”的含义。[26]考《诗经》,郭璞“质尔民人”之语出自《诗经·大雅·抑》篇,原文为“质尔人民,谨尔侯度,用戒不虞。”[27]其意是指谨慎地使人民安居乐业,谨遵王和诸侯的礼仪法度,警惕和防备意外发生。由此可知,“质”的本义是“成”,即成功、有功绩之义。
2.1.2 “质”字质押含义的出现与普遍应用。《说文解字》释“质”为“以物相赘。”[28]所谓“赘”,《说文解字》释为“以物质钱。从敖贝。敖者犹放,谓贝当复取之也。”[29]即以物品作为抵押换取金钱,物品只是暂时存放,抵押人在约定期限内可用金钱赎回抵押物。故段玉裁注曰“若今人之抵押也。”[30]《汉书卷六十四·严助传》有云:“间者,数年岁比不登,民待卖爵赘子以接衣食,赖陛下德泽振救之,得毋转死沟壑。”[31]如淳注曰:“淮南俗卖子与人作奴婢,名为赘子,三年不能赎,遂为奴婢。”[32]如淳此注所述淮南俗例,正是“赘”字之含义在我国古代社会较为精当的表现,其核心要义是有物品作为抵押,约定有回赎期限,允许抵押人在约定期限内用金钱赎回抵押物,超过约定期限后,抵押物则归债权人所有。由此推断,所谓“质”者,《说文解字》释为“以物相赘”,也是以物品作抵押之意。段玉裁于此注曰:“以物相赘,如《春秋》交质子是也。”[33]“质子”,即在古代(以战国居多)被派往别国作为人质的人,其目的是建立信任和担保盟约的履行,因此质子多是由王子或诸侯之子充任。如《史记卷三十九·晋世家第九》记云:“(晋惠公)八年,使太子圉质秦。”[34]同篇又载曰:“(晋景公)九年,……晋伐齐,齐使太子彊为质于晋,晋兵罢。”[35]可见,战国以降,用“质”表示抵押的含义已较为普遍。
在现今法律中,与抵押相对,质押也是一个较为常用的法律术语。质押是建立在质押物占管形态转移的基础之上,由质押权人对质押物进行占管,并由质押权人承担质押物的毁损或价值减少等法律责任,而抵押这一法律关系建立时,抵押物的占管形态不发生转移,仍由抵押人对抵押物进行占管,并由抵押人承担抵押物的毁损或价值减少等法律责任。所以,如果按照现今法律术语和法律概念对“质”进行界定,那么其更为准确的释义应为质押。质押的含义也与上文所举淮南赘子和战国质子之实例更为契合,因为赘子和质子等人的占管形态事实上已经发生了转移,所以其占管责任也一并转移给了质押权人一方。“质”字质押含义的出现与普遍应用,为其日后衍生出文书契券等凭据类含义奠定了基础。
2.2 “剂”字考源
据目前史料而论,“剂”字在西周时期已经出现,其最初的本义是指“整齐地截断”,并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出“文书契券”“剂量”等含义。
2.2.1 “剂”字的起源与本义。“剂”字,目前所见,其最早的出处是在西周早期的“麦方尊”(集成编号6015)铭文之中,其铭文字形为“ ”。[36]“麦方尊”记云:“之日,王以侯内(入)于寝,侯赐玄周(琱)戈,雩王在 (斥),己夕,侯賜者(赭) 臣二百家,劑(齎)用王乘車馬、金勒、冂(䄙)衣、芾、舄,唯歸, (揚)天子休,告亡尤,用龏(恭)義(儀)寧侯, (景)考于井(邢)侯,……”[37]此处引文为《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的释文和断句方式。郭沫若对“麦方尊”铭文亦有专门研究,他认为“剂”处前后的句读应为“臣二百家,剂。”[38]郭氏认为,“剂”字在此处的意思是契券,作用是证明奴隶的身份和来源的合法性,即奴券。此句的大意是周天子赏赐井候二百个男性奴隶,并将载明这些奴隶身份和来源的契券一并赏赐给井候。据此,郭氏提出:“此语可证古有奴券。”[39]其后,在战国早中晚期的青铜器铭文之中,亦有见“剂”字。
《尔雅卷第三·释言第二》有曰:“剂、翦,齐也。”[40]邢昺疏谓:“皆为齐截也。”[41]即“剂”和“翦”都有截断以使整齐的含义。郭璞注云:“南方人呼翦刀为剂刀。”[42]由郭氏之语可知,因为“翦”和“剂”意思相同,所以可互相通用。在郭璞生活的两晋时期,同为剪刀,北方人称“翦刀”,南方人叫“剂刀”。此一民间称谓的异同,是“剂”和“翦”同义互用的实例之一。《说文解字》对“剂”字的阐释与《尔雅·释言》基本相同,其将“剂”字释为“齐也。从刀。”[43]从刀,意为截断之后像用刀砍切一样地整齐。概而言之,“剂”字最初的本义是“整齐地截断”。
2.2.2 “剂”字契券类含义的形成。“剂”字产生之后,逐渐在“整齐地截断”之本义的基础上引申出其他的含义和用法。其一,断绝。如扬雄所撰《太玄·永》有云:“永不轨,其命剂也。”[44]此处“剂”字即是由其本义“整齐地截断”引申FuN8t46Y0OjrdPE2qZ9Fdpc6ojidjzFPmn4Uk+4JFvU=为“断绝”之意。其二,契券。如《周礼·秋官·大司寇》所载“以两剂禁民狱……”[45]其三,剂量。如《三国志卷二十九·魏书二十九·方技传第二十九》记曰:“华佗……又精方药,其疗疾,合汤不过数种,心解分剂,不复称量,煮熟便饮,语其节度,舍去辄愈。”[46]其四,具有物理、化学或生物效用的制剂。如氧化剂、杀虫剂等。
在“剂”字以上诸种含义之中,其契券类含义与“质剂”直接相关,是“质剂”一词形成买卖契约文书这一概念的主要来源之一。字词内涵的拓展和演化,虽大都呈现出纷繁和复杂的多种现象,但也有着潜在的线索和脉络可循。就“剂”字而言,其在先秦时期是如何从“整齐地截断”之本义衍生出“契券”这一含义,也是有线索和规律可循的。然而,目前尚未有研究成果对这一嬗变过程作出较为有效的阐释。《尔雅》和《说文解字》仅对“剂”字之本义做出了准确的说明,并未涉及“剂”字之其他含义。段玉裁在注《说文解字》时,也只是在进一步诠释“剂”字之本义的基础上,列举了“剂”字之“券书”和“剂量”两种新含义,[47]但段氏并未对“剂”字这两种新含义是如何嬗变而来作出诠释。
笔者研究发现,“剂”字之“契券”概念的由来,与“剂”字之“整齐地截断”这一最原始的含义密切相关。先秦时期,契券多书于木札或竹简之上,在书写完毕之后,有一个关键的步骤是将木札或竹简从中间一分为二,由当事双方分别保存。性质和用途不同的契券,尽管在具体的书写形式上有所差别,但是在书写完成之后都会有一个从中间位置用刀整齐地截断这一分割步骤。如“傅别”(借贷契约)的形制是“大书中央,中破别之”,即将契约内容用大号字体书写于木札或竹简的正中间位置,待书写完毕后,用刀从中间一剖为二,最终的结果是双方当事人各自持有的契券在形状和内容上均只有一半;“质剂”(买卖契约)的形制是“两书一札,同而别之”,即在同一幅木札或竹简的右边和左边这两个位置,先后分别书写同样的契约内容,在书写完成之后,用刀从中缝线位置将木札或竹简一分为二,最后的结果是买卖双方各自持有木札或竹简的一半,但在这半片木札或竹简上却记载着关于此次买卖所订立契约的完整内容。后世乃至现今的契券(即今惯用之合同),虽是以纸张作为主要的记录载体,在书写完毕之后从中间一分为二的做法已较为少见,但一式两份、正副两联、上下两联、前后多联等形式设计,仍属“中截为二”这一制度在形式上的变换。由此可见,凡是一份有效的契券,在准确详细地载明契约的内容之后,都要经过从木札或竹简的中线位置整齐地截断这一制作过程。这一整齐截断的过程与“剂”字之本义“整齐地截断”正相符合,较为有效地证明了“剂”字之“契券”这一衍生含义与其本义之间的原始联系,厘清了其内涵的嬗变过程。
此一研究结论的得出,不仅是建立在“剂”字“整齐地截断”之本义和衍生含义“契券”具有较为密切的关联这一客观基础之上,而且在契券类名词之中,与其相类似的内涵嬗变过程并非孤例。譬如“契”字,其与“剂”字内涵相近,都用来表示契券,但契券都不是它们最原始的本义,而是在后来的发展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契”字本身的含义是用刀具等较硬的锐器在陶器、甲骨、铜铁等金属器、玉版、木札、简牍、石料等物体表面刻画出形状和文字。我国目前已知的最早的记录方式是结绳刻契,所谓刻契就是在物体表面刻画符号用于表意和记事。《诗经卷第十六·大雅·緜》有云:“爰始爰谋,爰契我龟。”[48]此处“契”字即为用刀在用于占卜的龟甲上刻字。古代与“契”字互为通用的“栔”“锲”等字,也都表示用刀刻画的意思。如《说文解字》释“栔”为“刻也”[49];段玉裁注云“古经多作契”,[50]同时指出类似的假借字或俗字还有“锲”“挈”“楔”“㓶”等。在“契”字“用刀刻画”之本义的基础上,其先是衍生出了“断绝”之意,如《尔雅卷第二·释诂》载云:“契、灭、殄,绝也。”[51]邢昺疏“绝”曰“皆谓断绝”。[52]“契”字由本义“用刀刻画”嬗变出“断绝”之意,与“剂”字从本义“整齐地截断”引申出“断绝”之意的早期演进过程十分相似。随后,“契”字演变出“契券”之义,并逐渐成为其主要的含义。如《说文解字》将“契”字释为“大约也。……《易》曰:‘后代圣人易之以书契。’”[53]所谓“大约”,即正式的契约文件。《周易卷第八·系辞下第八》记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54]上文已述,结绳刻契是我国最早的记录方式,《周易》此文是为“契”字由本义“用刀刻画”演变为“文书契券”含义的又一佐证。同时,这一记载表明其时的人们已经认识到文书契券在司法和行政上具有重要的凭证作用,并将这种作用概括为“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55]王弼注云:“书契所以决断万事也。”[56]由此可见,先秦时期,“契”字已经完成了从其“用刀刻画”的本义到“文书契券”这一概念的演变,后者逐渐成为其主要的含义并沿用至今。“契”字内涵的演变过程,为我们理解和验证“剂”字从其“整齐地截断”之本义嬗变为“文书契券”之新含义提供了较为有效和翔实的例证。
综上所述,“剂”字最原始的本义为“整齐地截断”。因为先秦时期的文书契券,多以木札或竹简为记录载体,且在书写完成之后都要经过“中破别之、一分为二”的截断步骤。因应先秦文书契券“中破别之”的制作过程,“剂”字逐渐从最原始的本义“整齐地截断”衍生出“文书契券”之意。
3 过渡:泛称类双音节名词“质要”和“质律”的出现
一般而言,名称的出现和渐趋定型要稍滞后于事物的起源和发展。在用于表示买卖契约文书这一事物的专有名词产生以前,买卖行为就已经发生或形成了。据流传至今的先秦典籍和已出土的金文简牍等考古史料而论,在“质剂”这一专有名称出现以前,尚没有指代买卖契约文书的专有名词。在“质剂”一词生成之前,当表达买卖契约文书这一事物时,除了“契”“券”“书契”“契券”等较为常见和易于理解的契约文书总称类名词,与“质剂”较为相近且包含有买卖契约含义的名词有“质要”和“质律”。需要注意的是,“质要”“质律”是泛称包括买卖契约、借贷契约、商业票据等在内的多种文书契券,而非专指买卖契约。
3.1 “质要”。在《春秋左传·文公六年》所传[57]之中,有谓“质要”之语,魏晋时期杜预在注《春秋左传》时认为“质要”就是券契。
《春秋左传·文公六年》有云:“宣子[58]于是乎始为国政。……由质要,治旧洿,……出滞淹。”[59]杜预注“质要”为“券契”,[60]唐代孔颖达正义曰:“‘由质要’者,谓断争财之狱,用券契正定之也。”[61]孔颖达自陈“知‘质要’是契券也,如《周礼·天官·小宰》文。”[62]即孔颖达根据《周礼·天官·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经邦治:……四曰听称责以傅别,……六曰听取予以书契,七曰听卖买以质剂,……”[63]的记载,还有郑众所述“傅别”谓“券书”并称“听讼责者,以券书决之”[64]的注释,以及郑玄“傅别质剂,皆今之券书也,事异,异其名耳”[65]的注解,认为《春秋左传·文公六年》传所云之“质要”,是和《周礼·天官·小宰》所载之“质剂”“傅别”“书契”类似的契券。其意是指,赵盾在执掌晋国政权之后,修订法律和刑罚章程,规定凡是审理和裁定与争夺财物有关的狱讼,在确定诉讼双方权益和责任的过程中,应当以“质要”(即契券)作为主要的凭证和依据。由此可见,至晚在春秋时期的鲁文公六年(公元前621年),人们已经开始使用“质要”等契券,而且这类契券是与财物相关的一种所有权凭证。既与财物相关,还涉及争财之狱讼,彼时作为契券泛称的“质要”所适用的场景无疑也包括商品交易等买卖活动。
3 . 2 “质律”。《荀子·王霸篇》记曰:“关市几而不征,质律禁止而不偏,如是,则商贾莫不敦愨而无诈矣。”[66]唐代杨倞注“质律”云:“质剂也,可以为法,故言质律也。”[67]其认为《荀子·王霸篇》所云“质律”的含义与“质剂”较为接近,因为“质剂”作为法律文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法律意义上的约束作用,所以将其称为“质律”。同时,杨倞认为,“质律”的作用在于禁止而不偏。所谓“禁止”者,即预防和禁止奸人;所谓“不偏”者,即避免负责市场争讼的官员在审理案件时偏听偏信。为了诠释“质律”,杨倞还引用《周礼·天官·小宰》“听卖买以质剂”[68]作为旁证,并引郑众注“质剂”为“市中平贾,今时月平是也”[69]和郑玄注“质剂”为“两书一札,同而别之,长曰质,短曰剂,皆今之券书也”,[70]列举了二郑对“质剂”不同的解释。此外,杨倞也引述《春秋左传·文公六年》传文所见“赵盾为政,董逋逃,由质要”[71]之语,并称“质”意为“正”,即匡正、不偏以及合于法则之意,与《荀子·王霸篇》所云“质律禁止而不偏”之说相合。对《春秋左传·文公六年》传文“由质要”的援用,表明杨倞认为“质律”和“质要”有含义相通之处。
笔者研究发现,《荀子·王霸》篇中此语是专门针对商业贸易而言的,其意是指如果关卡和集市勤加检查而不收税,使用契券预防和禁止奸人弄虚作假,并以契券作为审理争讼的依据避免偏听偏信,那么商人们就会诚信经营,从而杜绝欺诈等不实行为。据此可知,《荀子·王霸》篇所云“质律”,亦是契券的泛称。
综上所述,《春秋左传·文公六年》传云“质要”和《荀子·王霸》篇所见“质律”都是对契券的泛称,此类泛称虽然也包括买卖契约的涵义,但同时也包括借贷契约、取予契约及商业票据等文书契券。即在“质剂”出现之前,“质要”“质律”等名词在作为文书契券这类事物的泛称时,包含有买卖契约的含义,但尚未有名词专门指代买卖契约。
4 定型:专有名词“质剂”起源于《周礼》
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分析,“质剂”一词是由“质”和“剂”组合而成的联合式双音词。它们的组合是历史语言学“同义相吸”原则的典型代表,即“质”和“剂”的内涵各自嬗变并形成“文书契券”这一主要含义之后,因二者义项相同,联合组成“质剂”一词,其含义可借由同义词素互证的方式得到进一步强化。因此,在先后阐明“质”和“剂”两个更早出现的单音节名词之历史起源与内涵嬗变过程,以及辨析“质要”“质律”等与“质剂”相近且较早出现的契券泛称类名词之后,探究并厘清“质剂”一词的起源就成为一个迎刃待解的问题。
4.1 单音节名词“质”和“剂”于《周礼》多以文书契券类含义出现。据笔者统计,“质”和“剂”在《周礼》中分别出现十八次和十六次,出现频次相差无几。细研原文,发现它们在《周礼》中虽有两或三种含义,但最主要且最常用的概念均与文书契券直接相关。
4.1.1 《周礼》所见“质”字及其具体含义。在《周礼》之中,“质”字共有统计簿书、评估价值、文书契券三种含义。其中,文书契券类含义最为常见。
其一,统计簿书。孙诒让于《周礼·天官·小宰》对“七曰听卖买以质剂”正义有曰:“旬计曰月成,月计曰月要,岁计曰岁会,皆名为质。”[72]意即每旬、每月和每年的统计簿书,分别称之为月成、月要和岁会,它们的总名称是质。所谓“簿书”者,是登记在簿籍上的会计之书,其作用是将一定的统计对象汇总到一起,以便于清点和核查它们的类别和数量。先秦时期,簿书的应用范围颇为广泛,如行军打仗前清点士卒和军用物资时,使用簿书登记士卒的姓名和隶属关系、兵器的类别和数量等信息;再如天府、泉府等掌管重要物资的部门,以及典丝、典枲等掌管专门物品的职官,凡是物品的进出均须登记其品名、类别和数量等信息,并于次年初形成上一年度的统计簿书。在我国古代,统治阶级已经较为充分地认识到簿书的重要作用和价值,不仅规定有专门的时间督促各地定期上报统计簿书,而且将未能按时报送簿书视为重大失职,如《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第十八述曰:“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73]之所以如此重视簿书,不单是因为簿书利于清点、汇总和统计,还因为簿书有核验和凭证功能。郑玄注《周礼·天官·小宰》“六曰听取予以书契”有曰:“凡簿书之最目,狱讼之要辞,皆曰‘契’。”[74]所谓“契”,是按照相互之间的约定达成并对双方有约束作用的凭证类法律文书。
严格意义上而言,统计簿书并不一定都是法律文书。但簿书在登记时,其所涉及的统计对象以及相关数据,往往经过负责登记的官吏和所有权人等两方或多方的确定与核对,乃至签字确认,所以最终形成的簿书对各方都具有一定的约束效力。先秦时期,统治阶级已经认识到簿书的证验作用,并按照特定的用途对簿书进行分类以发挥更有针对性的凭证效用,如《周礼·天官·小宰》有谓:“以官府之八成经邦治:一曰听政役以比居,二曰听师田以简稽,三曰听闾里以版图,四曰听称责以傅别,五曰听禄位以礼命,六曰听取予以书契,七曰听卖买以质剂,八曰听出入以要会。”[75]所谓“八成”,即“成事品式著于簿书文券可以案验者,其目有八也”。[76]此“官府之八成”之中,比居(登载可任劳役人员的簿册)、简稽(登载士卒姓名和隶属关系、兵器类别和数量的簿书)、版(户籍簿册)、要会(会计簿书)等都是簿书,是治理朝政不可或缺的凭证类文书之一。
其二,评估价值。《周礼》之中,“质”还有“平”的含义。所谓“平”,即评估价值并达成交易,是买卖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周礼·夏官·马质》记曰:“马质掌质马。马量三物,一曰戎马,二曰田马,三曰驽马,皆有物贾。”[77]意即马质这一职官负责对马的价值进行评估,按照马的品种、毛色和年齿等特征确定其价格,并负责购买戎马、田马和驽马等种类的马匹。此处的“质”字,贾公彦疏为“平也,主平马力及毛色与贾直之等”。[78]在古代,“平”字与“评”相通,表评价、评议、评定、评估之意。贾氏认为,“质”表示评估,“质马”即评估马的力量、毛色和价格等。郑玄于《周礼·夏官·叙官·马质》注“质”曰“平也”,并述云:“主买马,平其大小之贾直。”[79]郑玄认为马质所负责评估的主要是马匹价格的高低。明代王应电于此亦有注,其语曰:“质者,平成之义,谓平其马价而成其交易。”[80]即王应电认为“质”除有评估之意外,还有促成交易的含义,而马质的职责之一是评估马的价格并促成交易,含有讨价还价等买卖过程中常见的协商之意。
结合上述注疏,可知“质”字在《周礼》之中还有评估商品价值的含义。这一评估过程有赖于对商品具体特征的充分了解和把握,如马质必须首先对马的品种、力量、毛色、年齿等基本特征作出衡量,才能较为准确地评定马的价值,而对商品价值的评估,主要是为了以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价格或条件促成买卖,以实现交易的达成。“质”字之“评估价值”的含义,虽不像其文书契券类含义那样与“质剂”高度相关,但也是商品买卖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且至关重要的环节,对“质剂”这一买卖契约文书的形成和其中所必备的价格等构成要件的确定具有重要的影响。
其三,文书契券。以“质”表示文书契券,是《周礼》所见“质”字的主要含义和用法。“契券”之“契”,是按照相互之间的约定达成,并对双方有约束作用的凭证类法律文书。“契券”之“券”,亦有相互约束以明确法律权利和义务之界限的内涵,故《释名卷第六·释书契第十九》将“券”阐释为“绻也,相约束缱绻以为限也”。[81]《周礼》所见,取“质”文书契券之意,较为典型的代表即是《周礼·地官·质人》“凡卖儥者质剂焉,大市以质,小市以剂”[82]的记载,因上文已有较详尽的论证,在此不重复赘述。
《周礼·秋官·朝士》载曰:“凡得获货贿、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举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83]即按法律规定,凡是得获他人丢失的货物、奴婢或牲畜等财物,应当及时送交外朝并在朝士那里报告和登记。如果超过十天仍然无人前来认领,那么相应的丢失物就应当被依法没收:价值较大的物品收归公家所有,价值较小的物品归得获者所有。在法律规定的十天有效期内,若有失主前来朝士处认领遗失的货物、奴婢或牲畜等财物,需以“质”作为凭据,经过朝士查验和确认后,才能将相应遗失物归还给失主,如“逋逃之臣妾皆得归其主焉。有主来识认,验其质而归之”。[84]由此可知,“质”作为买卖活动中产生的文书契券,既是一种具有原始记录性的法律文书档案,更是一种所有权凭证,其法律效力等同于现今所常用的买卖合同。
4.1.2 《周礼》所见“剂”字及其主要含义。“剂”字在《周礼》之中,主要表示文书契券之意。如《周礼·地官·质人》载曰:“大市以质,小市以剂。”[85]此处的“剂”字表示用于兵器和珍异等小额交易的买卖契约文书。又如《周礼·春官·诅祝》记云:“以质邦国之剂信。”[86]这里的“剂”字也是指契约类文书凭证。再如《周礼·秋官·大司寇》有谓:“以两剂禁民狱。”[87]郑玄注“剂”曰“今券书也”,[88]即由诉讼双方各自提交的陈述事实和缘由的凭证类法律文书。
《周礼》所见,“剂”字除单独使用外,还与其他单音节名词组合成双音节词汇,表示更为具体的含义,但仍从属于文书契券这一大类概念。如与“约”字组合成“约剂”一词,表示“盟书”“质剂”“傅别”和“书契”等契约的总称。《周礼·春官·大史》述云:“凡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有约剂者藏焉,以贰六官,六官之所登。若约剂乱,则辟法,不信者刑之。”[89]郑玄注“约剂”为“要盟之载辞及券书也”,[90]即周天子和诸侯国以及各诸侯国之间会盟所形成的“盟书”(政治契约),还有民众日常生活中所常用的“质剂”(买卖契约)、“傅别”(借贷契约)和“书契”(取予契约)等文书契券。《周礼·秋官·司约》语曰:“司约掌邦国及万民之约剂,治神之约为上,治民之约次之,治地之约次之,治功之约次之,治器之约次之,治挚之约次之。”[91]该处所列举之六种“约剂”,亦主要表现为“盟书”“质剂”“傅别”和“书契”等文书契券。再如“剂”字与“质”字组合成“质剂”一词,特指买卖契约文书。《周礼·地官·司市》记云“以质剂结信而止讼”,[92]此“质剂”即专指在买卖过程中形成的契约文书。
《周礼》所见“剂”字,在主要表示契券这种含义之外,还有一种用法是用以表示统计簿册,仍属于官文书的范畴。如《周礼·地官·遂人》述曰:“凡治野,以下剂致甿,以田里安甿,……”[93]此处所云“剂”字,是指登记有可服劳役人员姓名、性别、年龄、人数等基本信息的统计簿册。所谓“以下剂致甿”,意即按照较轻等级的役法规定召集民众,由此需要征调以服劳役的人员就会少很多,是一种减轻力役、与民休息的治理方案。
总体而论,“剂”字在《周礼》之中所取用的主要含义是“文书契券”,虽因场合之异而具体有买卖契约、诉状、盟书、借贷契约、取予契约、统计簿书等多种含义,但均未脱离“文书契券”这一概念属类。
4.2 “质剂”在《周礼》中专指买卖契约文书。《周礼》原文共见“质剂”5处,涉及2个系统(天官和地官)、4位职官(小宰、质人、司市和旅师),如表1所示。
按照《周礼》原文对“质剂”的记载,与“质剂”概念相关的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
其一,据《周礼·天官·小宰》可知,“质剂”属官府八成之一,且主要适用于买卖关系。成,意为“有成籍可覆按也”。[95]成籍,是指有据可查的凭证文书。官府之八成,即“官府之成事品式”,[96]如《周礼·天官·大宰》所称“五曰官成,以经邦治”[97]。概言之,“质剂”是在买卖关系中所形成的官方凭证文书。
其二,据《周礼·地官·质人》记载,在买卖交易中,根据市之大小,“质剂”分为质、剂两种。质人在审理有关“质剂”的诉讼时,按照距离远近规定有明确的时效期限,超期者不听(不受理)。
其三,据《周礼·地官·司市》所述“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质剂结信而止讼”,[98]“质剂”具有建立信用、进而避免讼争的作用。
其四,据《周礼·地官·旅师》而论,“质剂”是官府发放给民众的一种信用凭证。《周礼·地官·旅师》所云“质剂”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应用,它不是用于买卖关系之中,而是用于发放和接收赈灾粮食这种特定的关系之中。属于地官系统的旅师一职,主要负责掌管储存在野地的锄粟、屋粟、闲粟等互助救济粮和惩罚性税粮,并力求使它们发挥最大效用。当春季田地尚未出产或遇有灾荒等凶年致使农民缺少食粮和用于春耕的粮种时,旅师可根据法律规定将民众召集起来,凭借“质剂”将上述三种储备粮食合理地分配给民众,以使民众得到救济并借此度过春荒或凶年。在春季凭借“质剂”分发出去的救济粮,在秋季粮食收获之后须凭借“质剂”再收取回来。此种“质剂”在性质上更接近于取予契约,但却借用了买卖契约的形式,在官府和民众之间就春季分发与秋季收回粮食这一关系建立了一种信用凭证和原始记录,并据此起到预防争讼的作用。
综上,据《周礼》原文而言,“质剂”主要是指在买卖关系中形成的,具有建立信用和避免讼争作用的官方凭证类法律文书,而这正是先秦以降所称买卖契约文书的专有含义,即“质剂”在《周礼》中专指买卖契约文书。
4.3 买卖契约文书专有名词“质剂”起源于《周礼》。据目前可考的史料而言,作为买卖契约文书专有名词的“质剂”起源于《周礼》。得出这一结论主要是基于两个基本事实:
第一,在《周礼》出现之前,包括甲骨文、金文、先秦简牍以及《尚书》《春秋》《逸周书》等目前可见且能够识读的文献史料之中,均未发现有“质剂”一词。
第二,“质剂”一词在《周礼》首次出现以后,尽管在后世文献中屡有发现,但经笔者逐一细核原文,确证目前所见后世文献对“质剂”一词的应用,仍是本于《周礼》对“质剂”的有关记载。如宋代李昉等人根据“博采群书,以类相集”的原则所纂修的大型类书《太平御览》所见“质剂”一词,即是对《周礼》相关记载的征引,其卷八百二十八资产部八《卖买》有谓:“以质剂结信而止讼”,[99]即源出于《周礼·地官·司市》“以量度成贾而征儥,以质剂结信而止讼”[100]之记载。属于这类情况的还有唐代的《通典》和《文选》、清代的《通俗编》,等等。它们都是对《周礼》“质剂”相关记载原文内容的辑录。另外所见较多的有关注疏类著作,如宋代王安石所撰《周官新义》,是对《周礼》原文和注疏的训诂之作,书中所见“质剂”一词必然是源出于《周礼》原文,其卷七《地官二》有云:“质剂之治,宜以时决,久而后辨,则证逮或已死亡,其事易以生伪,故期外不听,亦所以省烦扰。”[101]考其本源,这是对《周礼·地官·质人》所载“凡治质剂者,国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国朞。期内听,期外不听”[102]的注解。属于此类情况的还有唐代的《周礼注疏》、清代的《经义述闻》《周礼正义》等著作。总之,后世文献所见“质剂”一词及有关论述,皆源于《周礼》。
在研究一个名词的起源问题时,除了要尽最大可能穷尽目前可以查考的史料往前寻找和确证这一名词最早的出处,还要往后广为查阅,以便寻找与这一名词起源相关的记载。这是因为成书时间越是距今久远的古籍,越有可能在后续的传抄、刻印、保管等流传过程中,出现讹误或散佚,但得益于其他文献尤其是类书和丛书的辑录或征引,部分散佚的古籍仍有部分内容得以留存至今。如东汉郑玄撰写的《周易注》,全书原本应有九卷,但在后世流传初期就已散佚,后经南宋王应麟、明代姚士粦和清代惠栋等多位经学鸿儒历次辑录和编校,现存世者共有三卷。也就是说,部分古籍可能已经散佚,但在与其同时期的文献和在其之后的后世文献之中,仍可能会有已经散佚古籍所记载内容或名词的蛛丝马迹。
具体到“质剂”一词的起源,在《周礼》之前,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的文献史料有使用过“质剂”一词。如果仅就这一论据,那么这可能只是囿于目前已出土的甲骨文、金文和先秦简牍等文献史料尚不完整而得出的暂时结论。但在《周礼》之后的历代各类传世文献之中,所见对“质剂”一词的应用与论述,几乎全都本源于《周礼》,并未见提到有比《周礼》形成时间更早的文献和出处。综合这两个客观事实,判定“质剂”一词起源于《周礼》当属较为可靠的结论。
5 结语
在买卖契约文书的发展演变历程中,其专有名词“质剂”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基于一定的历史基础和一定的语言文字发展阶段而逐渐形成的。根据目前已知的史料,“质剂”一词最早出现于《周礼》。在此之前,“质”“剂”这两个单音节名词的产生和发展及其相关内涵为“质剂”一词的诞生做好了语言文字方面的准备,而“质要”“质律”等与“质剂”相近且更早出现的契券泛称类双音节名词,是买卖契约文书进化到专有名词阶段——“质剂”的重要阶梯,它们为“质剂”一词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前期的历史基础。
自《周礼》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用以指代买卖契约文书的专有名词——“质剂”正式出现,并在其后三千余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坚守着买卖契约文书的涵义内核,成为契约文书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一种专指性符号名称,具有较为突出的专业性特征,是为中华民族早期文明在法律类文档名词领域的杰出结晶之一。厘清“质剂”一词的起源及其嬗变为买卖契约文书专有名词的过程,不仅有利于纠正学界关于“质剂”研究存在的误读误用,以更加准确和深入地认识“质剂”这一名词和事物,而且对买卖合同制度之溯源、现代合同制度尤其是电子合同制度之构建与完善以及全国性文书档案管理制度改革,都具有历久弥新的现实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档案史史料学”(19BTQ095)、广西民族大学科研资助项目“《周礼》‘质剂’之来源与形制研究”(2022MDSKYB05)和广西民族大学引进人才科研启动项目“质剂的名称、制度与流变”(22SKQD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与参考文献:
[1]朱亦凡.试论古代“九州”的意涵演变[J].档案与建设,2023(11):102-103.
[2]张传玺.契约史买地券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8:9-38.
[3]乜小红.中国古代契约发展简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7:127-165.
[4]白小平.中国古代买卖契约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06.
[5]高玉玲.宋代买卖契约的法律效力问题研究[D].芜湖:安徽师范大学,2015.
[6]刘高勇.清代买卖契约研究[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8.
[7]温慧辉.试论先秦时期两种主要的契约形式:“傅别”与“质剂”[J].史学月刊,2004(12):20-24.
[8]春杨.论明清时期买卖契约的类型和构成要件[C]//霍存福,吕丽主编.中国法律传统与法律精神: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暨2009年会论文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209-220.
[9]丁海斌.《周礼》中记载的法律文书与档案[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02):3-5.
[10]丁牧羊(丁海斌),王鹤淇.《周礼》文档名词再研究[J].档案学通讯,2015(06):32-39.
[11]康胜利,丁海斌.关于《周礼》的档案史史料学研究:兼论档案学界之《周礼》误读[J].档案学研究,2020(05):4-10.
[12]丁海斌,梅双双.中国古代“会要”档案史史料研究[J].档案与建设,2022(07):41-44.
[13][14][17][45][63][68][72][75][76][77][82][83][84][85][86][87][89][91][92][93][97][100][102](清)孙诒让周礼正义[M].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1076-1077,167,1077,2750,167,167,177,167,167,2374-2375,1076-1077,2824,1077,1076-1077,2061,2750,2081-2082,2845-2846,1057,1123,62,1057,1079.
[15][16][64][65][69][70][74][78][79][88][90][96][98](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654,737,654,654,654,654,654,842,830,870,817,645,734.
[18][19][20][21][22][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7:102,105,200.203,207,102.
[24]张守中.睡虎地秦简文字编[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96.
[25][26][40][41][42][51][52](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尔雅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2575,2575,2581,2581,2581,2576,2576.
[27][48](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555,510.
[28][29][43][49][53](汉)许慎.说文解字(影印陈昌治刻本)[M].北京:中华书局,1963:130,130,92,93,213.
[30][33][47][50](汉)许慎.说文解字注(影印经韵楼刻本)[M].(清)段玉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281,281,181,183.
[31][32][73](汉)班固.汉书[M].(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2779,2779,2244-2245.
[34][35](汉)司马迁.史记[M].(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59:1655,1678.
[36][3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第五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7:3704,3704.
[38][39]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41,41.
[44](汉)扬雄.太玄集注[M].(宋)司马光集注,刘韶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112.
[46](晋)陈寿.三国志[M].(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799.
[54][55][56](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87,87,87.
[57]传,音zhuàn,是古代的一种文体,指用以解释和说明经义的文字.因《春秋》原经文简约难通,后世出现了许多对《春秋》的注解之作.《春秋左传》,即左丘明对《春秋》的注释说明,该书中的“经”是指《春秋》原文,“传”是指左丘明的注解.
[58]指赵盾,其谥号为“宣”.
[59][60][61][62][71](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1843,1843,1843,1844,1843.
[66][67](清)王先谦.荀子集解[M].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228,228.
[80]周公.周礼[M].徐正英,常佩雨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627.
[81](清)王先谦撰集.释名疏证补(影印清光绪二十二年刻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301.
[94]此表为笔者自制.
[95]彭林,严佐之.方苞全集 第2册 周官集注[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56.
[99](宋)李昉,李穆,徐铉.太平御览(影印宋本)[M].北京:中华书局,1960:3692.
[101](宋)王安石.周官新义附考工记解(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7:96.
(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康胜利,博士,讲师,硕士生导师;丁海斌,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通讯作者 来稿日期:2024-0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