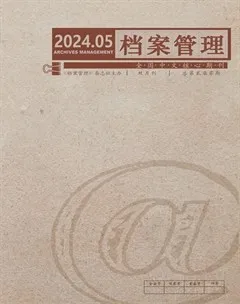解铃须从系铃处
摘 要:笔者的“四正”,从名分、本义、学理、法律上已弄清Records的含义,但坚持“Records文件观”者依旧质疑:若Records是档案,那Archives是什么?两者并列时又怎么翻译?还有人说Records是记录。既然是英语和法语带来的问题,循着英法档案历史去寻找,才是解铃的关键:以英法八百年档案工作中重要人物和事件为主线,探求其档案的源流、本质、内含及演变,为档案概念正史。
关键词:卷档;录卷归档;档案;皇家档案;馆藏档案;现行档案;概念;历史
2.2 法国档案概念的嬗变(1794—1979)
2.2.1 从馆藏档案到档案。法国大革命雅各宾专政时期的显著特点就是恐怖主义,而诞生于恐怖高峰的《穑月法令》天然具有“档案恐怖”的基因。今天所谓其开创的现代档案馆事业,实际上是“歪打”“正着”于六年后第一执政拿破仑的《牧月法令》。大革命所创生的现代档案馆概念,则是来自于教堂、修道院的藏室和17世纪欧洲的“档案馆法权”理论。19世纪中叶因爱屋及乌而衍生出的所谓“档案”概念,是与“档案馆”同词共轭的概念,本是指馆藏档案(或档案馆藏)。1961年,为应对机关档案大量产生而出现的“三个时段”理论,才使馆藏档案概念跳出共轭窠臼,逆向溯源到其出生地的机关档案。但这种档案概念的嬗变,不仅给法国档案馆及机关档案工作带来困惑,而且影响到国际档案馆界的专业交流。
大革命中的档案命运。旧制度档案是特权、权力、财富的记录和象征,而毁灭档案则是法国大革命的起始标志和重要“成果”。从1789年7月至1794年7月的五年间,历代封建王朝积累六百多年的历史档案,遭到革命的“汪达尔主义”无情摧残!如果只是一时的愤怒,邪恶也不会持续这么多年,但那是一种想要毁灭一切的坚定愿望在驱使。[1]①烧毁封建档案。1789年7月开始,巴黎、马赛、斯特拉斯堡等地,都发生过大规模毁坏、焚烧旧档案和文件的暴乱;立法议会下令在旺多姆广场Place Vendôme焚烧来自法国最具盛名的历史家族的大量原始文件;农民起义,档案有时会成为攻击目标;甚至有专门的法令针对圣灵修道院藏室的档案;在阿布维尔,地区档案管理员在“恭敬的沉默”中将“皇家特权及特许头衔、教皇的诏书、封建文件”点燃;在南特,他们烧毁了刻有前任市长贵族头衔的金皮书。②变卖回收资金。出售档案以回收资金,也是革命性销毁的创意:在科多尔,在共和国四年(1796年)芽月,一部门因出售“违反自由和理性原则的簿籍和文件”而收到了66 638镑。③制作弹药筒袋。为抗击反法联盟,法国军队需要大量装弹药的筒袋,结实的羊皮卷档案被派上用场,同样在科多尔,14 000张羊皮卷被送往土伦制作弹药筒袋。当时有人民代表呼吁:公民们,让我们把羊皮纸档案当作弹药袋,西班牙人死在封建档案titres上是光荣的。[2]1792年6月24日的法令,要求各省在8月10日的节日期间烧毁所有家谱档案、虚荣和不平等的记录。1793年1月5日的一项法律要求将凭据、档案以及羊皮纸文件(古老、重要的档案才用羊皮纸)发送到兵工厂,用它们来制作弹药袋。1793年7月17日,废除封建特权的法令宣布,无条件地废除封建义务,烧毁全部封建地契档案和文据,对私藏档案titres者处以五年铁镣徒刑。1793年12月10日的法令,强制要求持有国家财产的契约档案者要申报。至此约有4 000个档案室chartriers被摧毁。所谓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现代档案馆的出生证。档案馆是档案的永久保存场所。大革命在摧毁旧制度档案的同时,也为新档案的保存创建馆室。法国现代档案馆体系从构想、动议、出生到发展,每一步都是在革命或政府的法令之下。1789年7月制宪会议制定的《制宪会议条例》règlement de l'Assembléeconstituante最后一章中规定,在秘书处设档案室,并委托巴黎议员卡缪将议会文件保存在档案室“有三把钥匙的铁柜”中。1790年9月,路易十六批准的《国家档案馆组织法令》将议会档案室命名为国家档案馆,明确其是“王国宪法、公法、法律及发给各省所有法案文件的保存馆库dépôt”,每周开放三天。(1792年9月,曾改为法兰西共和国档案馆Archives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1790年11月《关于建立行政区档案馆的法令》颁布。1794年的《国家档案馆重组法令》(穑月法令)就像弗雷特瓦起点。但真正使法国国家档案馆成为国际典范的,是1800年5月第一执政拿破仑签署的导致国家档案馆独立的《牧月法令》。此外,1796年省级档案馆的设置、1836年国家档案馆接收范围、1941年省级档案馆藏分类等,也都是以法令形式的规定要求。1808年,拿破仑将苏比斯公馆(Hôtelde Soubise)划拨给国家档案馆,使其成为既保存劫后余生的历史档案,也接收国家机构移交档案,甚至保存没收/劫掠来的几乎整个欧洲档案的真正国家档案馆,且直到21世纪初都是国家档案馆的主要馆址。此后法国的档案馆事业完全是在《牧月法令》的框架下发展起来。
馆藏档案概念的形成。大革命虽然建立了现代档案馆,但由于革命和反封建的政治原因,一方面早期档案馆除接收政府现行文件外,还收藏什么没有定论;另一方面为避嫌封建,将想保留的旧制度“涉及历史、科学和艺术的档案”改称为历史记录monuments historiques,但实际上就是“涉及历史、科学和艺术的档案文件”。[3]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法国并没有档案馆藏物的定义,档案的概念还是沿用旧制度的chartes、titres等概念,前述法令中也是如此。如,①1821年路易十八批准创建的档案chartes学院;②设立档案titres分拣办公室,处置档案titres;③1809年—1812年法国从欧洲没收/掠夺档案chartes;④关于第二档案宝藏Trésor des chartes的动议等,都是用旧制度的档案概念。此外,档案馆从建立所收藏的内容就不断变化,从最初的排除旧制度档案、只收议会文件,到接收历史档案、但图书馆也收藏,最终接收机关档案、甚至是私人档案。因而,馆藏内容的称谓也一直变化。直到1860年代,在与国家图书馆争夺旧制度档案无果的情况下,档案馆才开始以“档案馆藏”Archives来区分与“图书馆藏”Bibliothèque的不同。所以迄今图书馆依然保存有大量档案,也只能是属于图书馆资料Bibliothèque而非档案馆藏Archives。
馆藏档案到所有档案。档案并非产生于档案馆,而是形成于机关。针对二战后机关档案大量产生,出于确保档案进馆质量的考量,档案馆界才不得不关注机关档案的形成和管理。1952年,国家档案馆向一些国家机关派驻特派档案馆员,协助机关对进馆档案进行选择和整理。1961年,法国塞纳河-巴黎省档案馆长佩罗汀,在研究、效仿美国机关档案管理和档案中心做法上,提出档案的“三个时段”理论,将Archives范围前溯至机关档案,使原本仅指馆藏档案的概念,嬗变为指现行、中间、最终三时段的所有档案。此后,法国依据该理论开展了预进馆档案中间库的不太成功的实验。同时,档案概念的嬗变也带来理论与实践上的纠结:由于理论的提出者是站在档案馆而非机关或全局的角度,因而以馆藏档案Archives、而非机关原本就有的档案概念dossiers,建构了现行、中间档案概念,致使Archives及其相关概念脱离其本义,带来人们对理论理解的歧义和质疑。Archives的含义由馆藏档案转为可以指代尚未进馆所有档案,打破了100年的与档案馆共轭的传统。但由于两种概念含义(馆藏档案、所有档案)都没有法律上的定义,在实际应用中,法国档案馆界又约定,若Archives单独使用,依然仅指馆藏档案,不包括机关所保存的档案(见AAF词典),而讲机关档案时则必须用现行或中间档案来表示。
档案概念的现实困扰。从1792年到1870年,法国在共和国—帝国—王国—共和国—帝国间反复转换,其间帝国、王国时期62年,远大于共和国时期的16年,也是档案馆事业Archivéconomie(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HENRI PIRENNE为法文版《手册》作序时所用术语。économie:资产财富的管理、经营、协调、布局,这里译为事业)大发展时期。如:1800年国家档案馆的独立是拿破仑签署的法令(第一执政已具有帝国的气质);1808年国家档案馆得到独立馆舍苏比斯公馆;1821年档案学校成立;1841年统一管理省级档案馆;1854年出版馆藏清册;1855年、1867年出版对档案宝藏的研究成果等,特别是1860年代确立的“馆藏档案”与“档案馆”形成同词Archives双义的共轭概念。到20世纪60年代的百年间,这一概念成为法国档案馆界引以为傲、具有专业含义的“高贵”称谓。实际上从本质上看,法国现代档案馆200多年发展的历史表明,作为馆藏档案,Archives内含着历史、文化、遗产的理念,而作为几百年来政府机关的档案,dossiers(相当于英美的records)则主要服务于行政、管理、权益的效用。用Archives取代dossiers既突破原来的共轭,又扰乱了机关对档案的常识和认知,给档案馆工作与机关档案工作的协调、交流带来混乱,既与法国机关档案概念不通,也与国际认知不符。
2.2.2 档案馆概念的由来。1789年7月29日《国民议会组织条例》最后一章,是关于大会秘书处及其文件保存。其中规定:“在本届会议期间,应选择一个安全的保管室dépôt,存放与大会运作有关的所有原始文件,并应配备有三把钥匙的铁柜armoires fermantes。”[4]也就是说,最初的议会秘书处文件保管室就是一间有带锁铁柜的安全库室。1790年9月,在律师、学者、公民阿曼德·卡缪ArmandCamus的推动下,立法会议颁布《档案馆组织条例》(16条),专门设立议会档案馆。主要内容是:将议会档案库室改称为国家档案馆,专门保存建立王国的宪法、公法、法律及法案;设置档案馆员(卡缪以最多的172票数当选)并居住在档案保存之处;档案馆每周开放三天(卡缪提交的草案是每天开放,被改为三天);存放在档案馆的法案和文件只能根据议会的明确法令才能从档案馆中移除。《条例》颁布的同时还有一份说明报告。其中建议针对旧制度各类档案处置,起草和研究有关档案titres及文件保存、分类理论和处置方法,并建议再设立一个跨委员会comités的档案馆专委会Commission des Archives。1790年11月的《设立省档案馆》法令,赋予卡缪一项责任:对大革命收缴、集中在卢浮宫保存的皇家档案、土地及财产登记档案、宗教档案及省档案馆进行监管。1793年1月,档案馆委员会成立,负责研究档案馆项目实施以及针对卢浮宫所收集的各类档案的处置。该委员会的工作成果之一就是后来的《穑月法令》。
由前述可知,大革命前王国各机构保存有大量档案,但无论是档案保管机构还是档案本身都没有被称为Archives的。1790年议会之所以采用档案馆这一新称谓的主要原因是:
①去封建的新形象。在旧君主制下,作为皇家档案存放场所的宝藏Trésor,使用已有六百年之久,简直就是封建王国的君主专制象征和标志!而新政权要割裂与封建的联系,树立新的国家形象,就必须有新称谓来与之割袍断义,而社会曾经在使用的馆、室、库、册等其他称谓:如dépôt、armoires、chartrier、greffe、cartulaires等,与Archives相比,似乎都有局限性,或者不够高大上。
②教会传统的影响。18世纪初,一些教堂、修道院开始用Archives指称自身保存文件和档案的场所。法国大革命时,虽然把矛头指向宗教,没收教会财产、取消宗教特权,但也利用宗教巩固其统治。罗伯斯庇尔认为,宗教以前是封建制度的主要支柱,现在它应该成为共和国的坚实基础,因为它有益于社会。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指出,法国革命对基督教表现出来的仇恨,并非针对宗教教义本身,而是以宗教革命的方式进行一场政治革命,是通过废除所有的旧社会政治秩序,建立以人人平等为基础的新社会政治秩序。所以大革命虽埋葬了君主制,但仅改造和利用了宗教,其革命的话语体系中不少是诉诸或改造于宗教修辞。如法国大革命三大口号之一博爱fraternité,就是来自宗教;后来颁布《教士的公民组织法》《教士宣誓法令》等法令,也使得宗教重生Régénération;法国的省département基本就是依照教区diocese来设置(《教士法》将136个教区缩减为83个,后又将其设为省),而法国议会档案馆的起名也正是来自教堂、修道院的用法,就如同旧制度王国的档案宝藏也来自教堂一样。
③档案馆法权理论。1700年前后,欧洲大陆在识别、确认文件真实性方面形成两大学派:一是古文书学派diplomatica。以法国学者让·马比昂(Jean Mabillon)1681年所著《古文书概论》(De re diplomatica )为代表,专注于将单份文件的材料及其文本特征与真实样本进行比较,以区分真实与虚假。古文书学方法强调对单个文件的文献学考证,如字迹、形式、内容、印章、签名等对文件细节的鉴别,导致其成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二是档案馆法权学派ius archive(the right toestablish an archive)。以德国法学家阿赫斯维·弗里奇Ahasver Fritsch于1664年出版的《论档案馆藏权与官府》(Tractatus de iure archivi et cancellarie)为代表,强调官方设立档案馆所收藏和保护档案的权威性,是一种主权权利。档案馆法权学派强调文件的真实性来源于对君主档案馆的公共信任,而不是直接鉴别文件。即单个文件细节不敌保存机构的法律地位及君主的权威。弗里奇借鉴了新罗马法中的公共信任(public faith)范畴,授权小公国设立档案馆。他认为:“公共档案馆中的文件scripturae,即使不是公共文件,也具有完全的信任及充分证据性。”1680年,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发表了《论档案馆是有用机构》(On the Useful Institution of an Archive)的论文,则将档案馆作为秩序井然的官僚机构和行政知识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所谓档案馆法权,就是通过档案馆保存archival preservation而赋予档案records合法性的原则。即,档案的真实性推定,是通过特殊保管人和特殊场所(如公共档案馆)保存,并被司法制度赋予的特殊合法性。[5]
④卡缪本人的贡献。早在大革命前的1783年,由三位巴黎律师修订出版的《丹尼萨尔法理学集》Collectionde jurisprudence de Denisart 第二卷中,有一个专门的部分讨论Archives,由律师卡缪撰写。卡缪在将几种保存文字记录的场所进行对比的基础上,将“Archives”定义为:“该词在我们的语言中的意思是存放并保存真实文件的地方”。实际上议会档案馆建立之初也正是仅仅保存宪法法案acte constitutionnel、法律原始记录minutes deslois,以及法令décrets文件。[6]因此,Archives成为法国国家档案馆的称谓,可能就是由身为学者兼革命家的卡缪所提议,因为法令就是他起草的。身处革命激流之中的卡缪,还是有些理智和保守的情结,在1790年制定国家档案馆组织法时,他还曾提出一个有关建立大型旧君主制档案库的提议,希望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能够被保存下来,但是没有被接受。
总之,基于大革命反封建的需要和要求、借鉴教堂修道院保存档案场所的称谓、依据档案馆法权理论,在卡缪的倡导下,现代意义上的档案馆在法国破土而出。这种由建立的权威性赋予其所藏物真实性的机构,在欧洲开始普遍出现,而古文书学则成为法国档案学校的一门主干课程。
2.2.3 《穑月法令》的真面目。1794年6月25日,法国国民公会在听取了朱利安·杜布瓦Jullien-Dubois代表档案馆委员会Comité des Archives和公共安全、财产与转让、立法、公共教育和财政等五个委员会所作的关于国家档案馆重组的报告后,颁布了《国家档案馆重组法令》(即《穑月法令》)。该法令被普遍认为“标志着档案管理新时代的开始”,特别是其被后人解读出来的所谓“国家档案集中、档案开放、国家档案馆网络”的三原则,更是为档案人所耳熟能详。但是,这是一个流传了200多年的神话。在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年之际,法国一些学者终于站出来戳穿了这个有意或是无意的解读:《穑月法令》不仅没有那么高大上,而且是恐怖时期暴力毁灭档案的典范。
恐怖背景下的法令。①时间上。1794年6月,正是雅各宾专政的恐怖Terreur高峰。《穑月法令》15天前的6月10日,国民公会在主席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主持下,刚通过了“惩治人民之敌”的《牧月22日法令》。该法令加快了革命法庭的工作并发动了恐怖统治,将镇压措施系统化。法令颁布48天内,仅巴黎一地就有1376人在没有审判的情况下被送上断头台,而《穑月法令》颁布当天,就有44名17岁至67岁的男女被送上断头台。在这一被马克思称为恐怖主义法律统治的恐怖时期,你认为处于恐怖风暴指挥中心的国民公会中的各位议员,是否有兴趣、有时间、有理由,为了文化、历史和遗产来讨论档案馆重组?②内容上。(限于篇幅,仅举主要内容。)《穑月法令》由组织的基本原则、档案titres总体划分与分拣、分拣方法、巴黎档案馆库构成、处置总则等五章构成,共48条。需要说明的是,档案Archives在17世纪、18世纪的法国通常被称为titres。[7]其对重组后国家档案馆的定位是:在国民代表处建立的档案馆Archives是整个共和国的中央档案馆库dépôt central(第1条)。该馆库现主要收藏:⑴ 1789年议会的前期文件汇集;司法部扣留或收集的所有内容。⑵ 国民公会及其各委员会的材料。⑶ 选举机构的会议记录。⑷共和国的印章。⑸ 各种钱币。⑹ 度量衡标准。将来要接收。⑺ 负责选举立法机构和执行委员会成员的会议记录。⑻ 与其他国家签订结果。⑼ 财产和公共债务的产权档案。⑽ 在外国的国家财产的产权档案。⑾ 人口普查的计算东西。⑿ 共和国各馆库dépôt中保存档案titres的摘要。⒀ 立法机构命令存放在该馆库的所有的条约(第2条)。《穑月法令》其余大部分条款则旨在组织一个让任何正常档案馆员都感到不寒而栗的操作:分拣triage,也就是销毁档案的代名词。为此规定设立档案分拣办公室,对全国所有的档案库藏dépôts de titres进行分拣。经分拣后分两类:一是即日起予以销毁的档案,包括:纯粹封建档案titres;判决被拒绝的;财产已收回和转让后不再有用的;1790年后永久授予的财产的(第9条)。二是属于历史、科学和艺术的或可用于教学的档案和手稿,将被送往巴黎的国家图书馆以及各地区的省级图书馆(第12条)。③动机上。在大革命恐怖顶峰时出台的《穑月法令》有两项主要动机:一是销毁所有“带有可耻的奴役印记”的旧政权档案;二是加快对革命中没收财产的处置。对此杜布瓦解释说,当暴君的雕像被推倒时,第一个行动是将所有档案付之一炬,消除一个可憎政权的历史记录中哪怕是最轻微的痕迹。然而,对公共或私有财产的尊重,要求必须仔细研究任何有助于证明财产的东西。所以将保留有关“国家财产、法院判决以及有关历史、科学或艺术”的内容,并设立档案分拣机构和分拣官来处理。杜布瓦进一步解释道,公民们,你们的财产委员会一直忙于追回国家财产,已经认识到收集这些财产档案的重要性,并认为最可靠的方法,就是将财产档案titres domaniaux的收集与请您审议的提案里的中央馆库,即您的档案馆,联系起来。为此,必须制定适用于档案titres查询和保护的立法,但这只是为处置财产的临时举措。在解释这些财产档案的去向时,杜布瓦说,不要害怕这些档案titres会以一种永久的形式积累起来,也不要害怕它们会继续存在下去,因为档案titres在暂时为您的委员会(指上述五个委员会)服务之后,注定会消失,因为它们所提供的房地产通过不断成功的销售重新进入市场,这是我们革命的绝对保证。[8]④效果上。⑴闪电般销毁历史档案。国民公会主席乔治·库东Georges Couthon在解释《牧月22日法令》时声称,共和国必须“以闪电般的速度”打击敌人。杜布瓦则与之相呼应地威胁道,要“以闪电éclair般的速度”让档案消失。可见《穑月法令》的本质是破坏性法律:其实施将使对档案的破坏成为规则,而保存则成为例外。恐怖统治与《穑月法令》之间何其相似:消灭人与消灭档案毫无违和感!幸亏《穑月法令》在法国大多数省份很少得到实施,并且在其颁布四十个月后就停止生效。⑵把新形成文件当作馆藏。从法令第2条可看出,国家档案馆主要就是收藏大革命以来的议会、公会的立法文件,历史档案并不在收藏范围之内,有些涉及财产的档案也是暂存。⑶将历史档案判给图书馆。这不失是一种对毁灭的妥协和曲线救档,因为《穑月法令》下的国家档案馆根本就不收藏历史档案,这也是为什么法国很多图书馆都保存有大量档案的原因。⑷使毁灭档案更加系统。如果说大革命中各地销毁和焚烧档案是自发的行为,那么《穑月法令》颁布后,销毁档案就成为合法、全面和制度性的行为。以档案分拣办公室的名义设立的革命法庭办事迅速,无数的羊皮纸档案被赋予了致命的资格:封建档案,也就是说完蛋了。[9]在革命的背景下看,《穑月法令》“对议会刚形成文件的尊重与对历史档案的蔑视并不矛盾”。
档案三原则的神话。长久以来我们被告知,《穑月法令》具有开创性的档案三原则。但须知这仅是法令48条中的3条(第1、第3、第37条),其他45条都是在讲如何系统、全面地销毁或放逐(到图书馆)旧制度档案,而这种选择性解读法律、随意演绎历史的,竟是以历史为生的档案馆界!①国家档案馆的集中化。《穑月法令》标题是重组国家档案馆,为此赋予其中央档案馆库的地位,集中的目的是统一对封建档案进行分拣、处置和销毁。名义上,国民公会实现了君主制无法实现的国家档案统一管理的目标,但事实上其集中化仍然是理论上的,因《穑月法令》规定只能收藏共和国各馆库保存档案的摘要,且集中化的理想还面临缺乏存储空间和手段的窘境。1796年的法令使各省建立档案馆;1800年雨月28日(2月17日)法令委托各区的秘书长管理省级档案馆,也未提及国家档案馆的“共同中心”;1800年牧月8日(5月28日)法令,更没提及省档案馆。所谓的档案馆管理集中化,仅几年后就被其他法令所抛弃。②档案开放。《穑月法令》第37条规定:“任何公民都可以在规定的日期和时间,到所有档案馆库dépôts,请求利用其所保存的文件pièces。”这如同1790年法令第11条“档案馆每周开放三天”一样,开放的是档案馆库,不是文件。它一方面呼应了1789年《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关于“社会有权要求任何公共代理人对其管理负责”,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加快没收财产的处置,并非为了方便学者的研究。所谓“档案的自由查阅”,是完全不了解立法者的真实意图:它仅是为了加快财产变卖回收资金而让人们来利用财产档案。将其奉为对档案馆管理的贡献和新阶段,不过是一个真正的神话mythe。[10]实际上直到安托万·勒特朗Letronne任馆长后的1842年,国家档案馆才创建阅览室!但档案也是基本禁用或需要特批的。1898年的法令虽然用50年的期限代替了禁止利用,但又附加了“任何文件利用均须获得移交档案的行政管理部门的批准”的创新。这完全违背了档案是国家财产、可供所有公民查阅的原则。[11]实际上在旧制度下,法国就已经出现公众自由利用文件。如一些档案馆至今仍然保存着16世纪的利用及文件借阅记录。本笃会教士雅克-尼古拉斯·勒努瓦Jacques-Nicolas Lenoir致力于研究诺曼底的历史,从1766年开始到审计法院档案馆查阅档案。他居住在离法院不远的圣日耳曼·德普雷修道院(Saint-Germain des-Prés),每天去审计法院两次,最早进,最晚出。二十五年如一日,除了睡觉、吃饭以及假期,就是查阅、摘抄档案,利用超过10万册档案。[12]莫罗的档案藏室绝大多数文件,都是到各类档案馆室库(trésor、greffes、chartriers、dépôts)查阅、抄写复制而来,说明除需要保密的文件外,档案利用在大革命前是很普遍的事。③建立国家档案馆网络。《穑月法令》将历史档案都划归图书馆,所以杜布瓦说,这“理所当然地”属于“你们在每个地区建立的图书馆,为此法国将感谢你,作为你对她的最大好处之一”(即接管这些档案)。[13]而根据1796年雾月5日(10月26日)的法令建立的省档案机构,后来也归属内务部管理。显然《穑月法令》完全没有,甚至反对将档案馆网络视为国家永久记忆守护者的想法。直到1897年成立档案馆局,才开始统一管理全国的档案馆。总之,这三条与整个法令其他条款是统一整体,是服务于消灭封建档案的革命目标!仅将这三条打造成档案管理开创性原则而不讲前因后果及另外45条的内容和目的,既脱离了大革命的历史背景,也是对该法令的初衷与动机的曲解。
《穑月法令》的真面目。诞生于雅各宾恐怖高峰时期的《穑月法令》,是一个服务于稳定革命财政状况的“财务和功利主义”法令,对历史来说则属于毁灭档案的“革命的汪达尔主义”vandalisme révolutionnaire法令,[14]并使全国范围内销毁档案制度化。它既不是为了历史,也不是为了档案,因为一切封建的档案,国家档案馆都不保存;为了处置财产暂时保存的,最终也要销毁;涉及历史、科学和艺术的档案还将送到图书馆。建立档案馆与销毁档案看似悖论paradoxe,但在该法令中是一致的,正如历史学家安妮·乔丹(Annie Jourdan)断言:为了保护,必须摧毁Pour conserver,il faut détruire。国家的现代性是从见证可恶过去的文献灭绝bibliocide的灰烬中诞生的(ARCHIVES LOST)。了解历史才明白,《穑月法令》的本质显然是有计划地销毁封建档案titres féodales,[15]所谓“三原则”不过是后人对该法令无背景的片面演绎。
2.2.4 拿破仑的牧月法令。法国之所以有今天独立的国家档案馆,主要归功于拿破仑的《牧月法令》。拿破仑之前,所谓的国家档案馆只是议会的附属机构,既不独立,还要跟随议会游历。从1789年在凡尔赛制宪会议创立于卡缪的办公室,到斐扬修道院Feuillants图书馆及原卡布钦修道院(1790年10月),再随议会前往土伊勒利城堡(1793年),然后前往波旁宫(1800年),其收集范围也主要是议会法案文件。1800年5月28日,雾月政变(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从督政府Directoire改为执政府Consulate)后半年,日理万机的第一执政拿破仑,签署了关于国家档案馆从议会独立的共和国八年牧月8日法令。《牧月法令》Arrêté du Prairial共13条,虽然不长,但不像《穑月法令》那样,90%都是在讲对档案的分拣、销毁、处置。《牧月法令》是真正的国家档案馆法令:一是使国家档案馆从附属于议会到成为独立的机构(第1条,国家档案馆将设在执政官指定的地点);二是明确规定了将来要通过立法,规范国家机构的档案移交(第4条,应向立法机构提出一项法律,以确定共和国各组成机构向国家档案馆移交文件的性质、形式和时间);三是首次提出由第一执政选择国家档案馆馆长(第8条,档案馆长由第一执政任命和罢免,并受其直接管辖);四是明确要求立法机构应当以立法形式为档案馆提供资金保障(第11条,根据其报告,立法机构每年应当为国家档案馆提供资金);五是规定国家档案馆的工作直接向拿破仑汇报工作(第13条,档案馆长应向第一执政报告其执行情况)。从此国家档案馆被置于第一执政的权力之下。[16]同年7月23日拿破仑任命卡缪为馆长。《牧月法令》中构建档案馆的人、才、物、业务范围等核心要素齐全,因而实际上是国家档案馆机构及其工作制度的创新,更体现了拿破仑对档案馆的认知和高度重视。试想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的档案馆由一把手负责,哪个国家立法要求议会每年都要为档案馆提供资金保障?哪个国家一把手直接听取档案馆长汇报工作?历史地看,《牧月法令》借壳《穑月法令》中的国家档案馆概念,但使其内涵变化而重生,或者说《穑月法令》的“歪打”“正着”于六年后的拿破仑的《牧月法令》。
知人善任。拿破仑既独断专行,也知人善任。多努作为历史学家、教授和作家,享有受人尊敬的声誉,1799年曾被拿破仑内定为第三执政官(执政府三人执政官之一)。但在参与起草宪法草案时,多努因不同政见与拿破仑本人进行了“温和但坚定”的争论,为此拿破仑改变了主意,仅任命他为法官。卡缪去世后,几个人觊觎馆长的职位,但拿破仑认为这个职位适合多努的才能和思想。1804年12月15日,拿破仑称帝半年后,任命多努为馆长;多努也因为拿破仑的信任而态度软化,于1805年1月28日报请拿破仑,将国家档案馆更名为帝国档案馆。后人评述道,“帝国时期的11年是国家档案馆的最艰苦和最辉煌的时期”,这与拿破仑的重视和主导分不开。因为正是拿破仑的《牧月法令》,才使档案馆在机构及馆址上成为真正独立于国民公会、直接向拿破仑汇报的名副其实的国家档案馆。
苏比斯宫。1808年,为了兑现了八年前《牧月法令》的承诺,拿破仑又将位于巴黎市中心马莱区的苏比斯宫(公馆)划拨给多努,使国家档案馆有了独立和永久的馆址。之前有不少重要机构都惦记着该建筑,当地居民也曾向皇帝提交请愿书,希望在那里设立证券交易所和商业法庭。1806年4月23日,拿破仑在请愿书上批示道:“内政部长将答复他们。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忽视他们社区感兴趣的一切,并为人民提供更多的活动场所。”但最终还是将其划拨给多努的国家档案馆,且在2013年国家档案馆新馆落成之前,一直是法国国家档案馆的主要馆址。
1810年2月5日,拿破仑在首席副官杜洛克Duroc陪同下,来到苏比斯宫的国家档案馆视察。与大革命初期及《穑月法令》对待历史档案态度截然相反,拿破仑表示,“在凡尔赛宫、罗马、各省départements”存在“许多对行政有用的文件papiers”,希望收集路易十五统治之前无论是对外关系、政府还是司法的一切文件。拿破仑强调,希望成为档案直接继承者,使其成为行政和外交关系的工具、主权档案的储备、帝国权力的展现。这表明了他对档案的认知和兴趣。1812年3月21日,随着在欧洲大量掠夺的档案来到巴黎,为实现拿破仑建立“世界档案馆”Archives du monde宏图,内务大臣蒙塔利维Montalivet签发法令,规划在塞纳河左岸耶拿桥Pontd'Iéna与协和桥Pont de la Concorde之间的天鹅岛,建立一座10万立方米、容纳帝国所有档案的建筑。在当年8月15日新馆奠基仪式上,蒙塔利维宣称,在此将汇集“十个世纪的档案titres,以及大部分杰出文明世界的档案titres”。[17]后因拿破仑的战败而未完成。
档案馆藏。拿破仑非常重视历史,关注档案收集问题。他将自己视为法国历史的幸运延续,并喜欢将自己与最伟大的历史人物进行比较。为此,他特别重视档案,尤其是这些档案对于管理被征服的领土也具有实际价值,所以据说他曾讲过:“一个好的档案馆员比一个炮兵将军对国家更有用。”档案当时被政府视为武器和工具。[18]《牧月法令》颁布半年后的一项法令提案中,拿破仑打算将立法决定、公共行政法规、命令以及政府机构其他文件的原始记录minutes集中在帝国档案馆中,但法令提案被立法机构拒绝。进入帝国时期后,拿破仑再次推行将档案集中的计划。1805年3月15日的法令规定,旧制度下的所有巴黎档案收藏都必须遵守这一义务。为此拿破仑在1808年3月6日(1804年称帝后,就不用共和历了)下令购买苏比斯公馆作为帝国档案馆的法令中声明(第5条),苏比斯宫将接收巴黎现有的所有档案,无论其名称如何,同时明确要求,塞纳省、洛林宫廷府和法庭的国家文件应于1809年运送到苏比斯公馆。
1809年10月14日,在对第五次反法联盟的战役结束时,法国和奥地利在维也纳附近的美泉宫Schönbrunn城堡签署了和平协议。根据《美泉宫协议》第8条,保存在维也纳或其他地方的法国控制领土内的档案移交给胜利者。《协议》签订后不久,即1810年1月,皇帝命令宗教事务部长“命令米奥利斯将军将罗马教廷的所有档案打包,并在良好的护送下送往法国”,这开启了帝国胜利者掠夺/没收欧洲档案的盛宴。这些档案在一名专员的监督下被军队移走,并暂时存放在斯特拉斯堡,等待分类整理,以便能够识别与和平条约有关的文件。同时拿破仑命令比戈特和内政部官员到档案馆宫le palais des Archives(前苏比斯公子的罗汉公馆),检查他是否可以容纳如此大量的文件papier,由此拉开世界档案馆的大幕。
2.2.5 多努的世界档案馆。作为演说家、牧师、教授、图书管理员、历史学家,皮埃尔·多努Pierre Daunou在大革命期间是督政府的重要人物,他以立法机构图书管理员的身份,亲自参与了1795年—1799年的法国政府没收战败国资产的行动。他支持将欧洲遗产集中到法国计划的合法性。1796年,他准备了从罗马图书馆收集的古版本清单;1798年,在担任督政府民事专员期间,他利用自己的技能对教皇的书籍和梵蒂冈的藏品进行了分类,这是他后来主持没收/掠夺欧洲档案计划的思想、理论和实操基础。雾月政变时,多努站在了拿破仑一边。1804年卡缪去世后,他被拿破仑任命为档案馆长。
世界档案馆。拿破仑帝国的扩张为多努的理想提供了舞台,苏比斯宫的库房空间使大规模收藏欧洲档案的计划有了底气。1809年,拿破仑战胜奥地利和英国领导的第五次反法同盟后,夺取了神圣罗马帝国和罗马教皇的档案。此后,法国萌生了将被吞并领土和卫星国的历史档案汇集的想法:世界档案馆,而其背后的主导就是多努。所谓没收confisquer,是从帝国角度讲,而从受害国角度,则是被掠夺pillage。在《世界档案馆:当拿破仑没收历史》一文中,法国学者玛丽亚·多纳托Maria Donato坚持认为:她更喜欢谈论没收而不是抢劫。因为在领土征服期间,档案从一个主权国家转移到另一个主权国家是正常的。[19]在深谙谁拥有档案、谁就拥有历史,谁掌握了历史、谁就掌握了未来的拿破仑眼中,多努之于历史档案,正如德农 Vivant-Denon 之于艺术品(维旺·德农男爵BaronVivant-Denon是法国艺术家、考古学家和博物馆馆员,曾随同拿破仑远征埃及,并建议从被征服国家掠夺艺术品。现卢浮宫的一个馆就称为德农馆),都是为彰显帝国荣耀的得力干将。两人在1804年被拿破仑任命为档案馆馆长和博物馆馆长。多努想让巴黎成为历史之都,德农则梦想是艺术之都。随着拿破仑的扩张,多努成为欧洲范围内没收/掠夺档案政策的真正推动力。在制定没收/掠夺档案的计划后,他也正是计划的实际执行者。
1806年至1808年间,拿破仑的士兵将大量档案带到巴黎。1809年7月在击败第五次反法同盟后,奥地利承认拿破仑在欧洲的霸权。“与战败国签署的停战条约中增加了有关文件转让的条款。”此后他决定掌握梵蒂冈和神圣日耳曼帝国的所有档案。因此,从1809年起,在欧洲各地发起了一项巨大的档案没收/掠夺行动。数十名官员、文人、宪兵和工人被动员起来。将附属国家和卫星国最重要的档案转移到巴黎的苏比斯公馆——世界档案馆。相比较《穑月法令》的消灭历史档案,拿破仑、多努是个进步,但“法国的荣耀映照着他国的耻辱”。[20]
事业的中断。世界档案馆成为多努的一项巨大事业,他也深深投入其中。在他的指挥下,1810年1月10日,米奥利斯将军接到“将罗马教廷的所有档案打包并在良好的护送下送往法国”的命令。在法国战争部长达鲁Daru的支持下,档案馆也派人随军队,“从欧洲大陆拥有的所有馆库中挑选文件,分类、打包并装载到滚轴车上,送往巴黎苏比斯公馆”。1811年春天,有212个箱子从西班牙西曼卡斯档案馆运来。尽管英葡联手反攻,多努却梦想着夺走瓦伦西亚、巴塞罗那、塞维利亚和马德里的档案。1811年冬天到1812年夏天收到了412箱萨瓦档案。1811年8月底,多努本人也前往罗马检查并选择意大利的档案,特别是负责整理和运送梵蒂冈的档案。在佛罗伦萨,多努挑选了13 598个包裹、盒子和簿籍;在锡耶纳和比萨数千件羊皮卷册中,他“就像一只被光吸引的蝴蝶一样,冲向与历史、政治、外交有关的一切”。[21]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世界档案馆馆藏除120 000件“法国”原产的包oX5CPn9p1dumn1qjKQew7g==裹和盒子之外,增加了近220 000件来自罗马、西班牙、佛兰德斯、维也纳、都灵及其他地区没收/掠夺来的羊皮卷、包裹和登记册。为此多努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组织来对到达的货物进行盘点、分类、归档、编目和存放。
1815年滑铁卢战役后不久,世界档案馆失去了支撑,苏比斯酒店被普鲁士龙骑兵占领。奥地利遣返从其馆藏中盗取的2 000箱文件;锡耶纳也找回了它的档案。但西班牙西曼卡斯档案馆藏,直到1941年才被归还了部分。最终除了丢失或毁坏的文件,大多数档案在王国复辟期间被送回原籍国,世界档案馆如南柯一梦灰飞烟灭。
多努的理想。大革命后一系列档案馆藏法规中,Archives仅指档案馆,而何为现代意义上的档案在19世纪初并没有统一的认识,因此当时还是用过去的称谓指代档案,这与多努的理想分不开。多努认为,应当建立一个档案总宝藏Trésor général des Chartes,也就是档案总馆,并将其称为第二档案宝藏second Trésordes Chartes。在谋划对欧洲档案大规模没收/掠夺计划时,他向拿破仑报告说:当(托斯卡纳大公国)利奥波德大公在佛罗伦萨收集了8万份羊皮纸档案chartes surparchemin,引起了欧洲所有学者的注意和钦佩。今天,只有皇帝陛下才能汇集这样的档案Chartes,不是8万份,而是至少80万份,包括帝国档案馆中已经拥有的档案Chartes。当古老的法国档案宝藏形成时,我认为所有这些档案Chartes都应该从意大利、西班牙和日耳曼的各地区中提取出来,形成并加入一个统一时间序列的收藏中。历史和古文书研究哪一天会在这一收藏中取得多大的进步,是无法预先衡量的。[22]显然在多努的宏大憧憬中,Chartes指的就是档案,Trésor général des Chartes等同于Archives de l’Empire,指档案馆。显然在19世纪初,现在我们认为是档案的Archives还籍籍无名,因为多努的理想是让新制度嫁接到旧制度上开花!
帝国后的王国时期,多努再次担任王国档案馆长到1840年,狂热、理想和雄心恢复了平静。多努历经共和、帝国、王国时期,从学者、牧师、官员、第三执政人选到档案馆长,先后参与过国家档案馆、执掌过帝国档案馆、谋划了世界档案馆、又回归到王国档案馆。和卡缪一样,两人都是基于图书馆的经验,先后主导开创了法国档案馆事业。卡缪基于旧制度教会的传统习惯,创建档案馆Archives,而对档案的指称,两人都还是青睐于传统的Titres、Chartes。
2.2.6 档案馆藏概念形成。基本概念是一项工作或事业的基础,也是在长期实践中逐渐形成。法国大革命不仅摧毁了旧制度,也是对封建档案观念的革命。旧制度的档案Chartes、Titres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用来指称档案,即那些用于确立权利、资格的法令、法规、书面文件及真实材料,但毕竟是旧制度的代表。在历经多年对档案认知的艰难选择,1860年代,法国档案馆界最终将档案概念锁定在与档案馆概念共轭的Archives,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概念嬗变。
大革命后的档案。1 7 9 0 年国家档案馆建立后,Archives一词主要是指档案馆,而档案概念还是沿用传统的chartes、titres,或papiers、actes,没有统一叫法。如穑月及牧月法令中,没有定义档案的概念,而代之以旧制度的档案titres或文件;如早在1751年,《百科全书》将Archives解释为“旧档案Titres et Chartes”,卡缪也认为,“档案馆只收藏档案Titres、真实的文件、文凭、档案Chartes、合同;相反,在其他馆库中收藏各种书面材料,偶尔和偶然也有法案文件”。[23]而且在实践中,档案馆仅保存刚形成的国民公会文件及1789年后形成的议会文件,这些旧档案恰恰被档案馆扫地出门送给图书馆。当然这仅是大革命之初的共和国反封建的政治考量,当雅各宾专政的革命高潮过后,历史档案也属于档案馆的收藏范围,甚至已存在600年之久的档案宝藏也被纳入馆藏。1801年,为了避免旧制度档案titres、chartes遭受分散的危险,国家档案馆希望将新政府的档案集中到国家档案馆,并宣布了将各部委和组成机构的所有文件转入该中央储存库的措施。直到1821年国家档案学院École nationale desChartes成立时,档案仍是用chartes,可见当时对什么是现代档案的认识尚未成熟和统一。
概念抉择的困难。概念或者称谓是对事物的指代;事物不变,但称谓可能随时代、民族、习惯等而改变。档案事物,通常是指机关履行职能活动中形成或收到、为参考凭证目的而归档保存起来的文件,这是现在通常的认知。但站在档案馆的视角,馆内收藏的文件才是Archives。如卡缪将国民议会档案馆的收藏分为五类:国民议会的文件acts;国民议会收到的文件;书籍和邮票等奖章物品;回忆录和期刊;委员会编制的记录。显然,由于革命的原因,最初国家档案馆只收1789年后的新文件,不要、也不介意图书馆保存历史档案。[24]这与今天的认知大相径庭。
随着大革命走出燃烧档案的激情,档案概念开始酝酿、演化。1839年8月8日,主管地方档案馆事务的内务部,向各省长发出通知,明确各省档案馆藏应收藏两类文件:一是 1789年之前具有历史或古文字意义的旧档案;二是1789年以来的行政文件册摘录extraits des cartons。但因为各地的不同认知和不同实践,这个界定范围在1846年1月5日路易·菲利普国王颁布的关于王国档案馆的法令中消失。直到1855年,《帝国档案馆组织法令》草案中确立了“历史纪录”monument de l'histoire的概念:“帝国档案馆收藏属于公共利益的文件;它不再是政府或行政的通常工具,而是成为国家的历史纪录。”[25]国家档案馆在确定馆藏,特别是接收机关档案方面的努力长达半个多世纪,因而档案或者说档案馆保存物的概念的确定也一直未确定。有学者将其归结为三个馆长连续的失败échecs,也反映出对档案概念确定的艰难抉择:①卡缪未能扩大他的权力。虽然《牧月法令》提出应就共和国机构文件移交进馆进行立法,但当1800年国民公会专门讨论文件移交进馆的法案时,被米歇尔·雷尼奥Michel Regnaud所拒绝。雷尼奥是拿破仑政治上最依靠的人,拿破仑最重要的法案,包括拿破仑法典都委托他起草。但他不太看重档案事务,或者为平衡各方权力而否决该法案,也就是说各部委自己保存档案,不愿向档案馆移交。②多努未能规范档案移交。多努虽然在没收/掠夺欧洲档案方面很成功,但其规划帝国总档案馆收藏的设想,却面临权力的挑战。如国务秘书处声称拥有“多努先生档案馆”的控制权,而其他部委则继续拒绝移交其档案。1812年,多努修改了他的计划,“我并没有意识到几位部长非常重视完整保存他们的特定档案,因此我避免将部长档案列入必须定期转移到帝国总档案馆的档案中。……我还避免提及和平、联盟和通商条约”。但即使缩小的移交规划也没有获得任何法令批准。③拉博德对图书馆的失败。1860年代,帝国档案馆馆长莱昂·德·拉博德Léon de Laborde参与国家档案馆与国家图书馆就各自收藏进行协商和交换,但图书馆不愿交出其收藏历史档案。这对档案馆的收藏范围及其称谓难以确定。
馆藏档案的概念。无奈情况的转机还是在法律。1855年12月22日的法令首次明确规定:“所有被认为涉及公共利益文件,当不再需要为依赖它们的部委或行政部门提供服务时,均应存入帝国档案馆。”1898年1月12日的法令、1936年7月21日的法令重申不再用于日常事务管理的行政档案移交档案馆的要求。[26]经过60多年的酝酿和努力,1860年后,鉴于机关移交前也将长期保存自身档案dossiers,图书馆也保存历史档案Titres、Chartes,法国档案馆界逐渐形成了共识:站在档案馆的角度,档案的概念只能限于馆藏材料。这意味着机关的档案dossiers只要没进馆,就不是Archives;图书馆保存历史档案Titres、Chartes也不是Archives。反之Archives概念也意味着实际上并不代表或包括所有档案,而仅是馆藏档案!因此直到1961年的近百年间,Archives(以下用a表示)成为一个具有双重含义的共轭概念。(百度:两头牛背上的架子称为轭,轭使两头牛同步行走。所谓共轭,即为按一定的规律相配的一对)其中的一个概念(馆藏档案)限定在其所共轭的另一概念之中,反之亦然,两者互为条件。即:只有在档案馆中才能称为a(未进馆的材料不叫a);反之,只要是称为a,肯定是已存放在档案馆(在别处的都不是a)。显然a仅指馆藏档案,机关中的档案另有称谓dossiers(见后面2.2.7)。对中国档案界来讲,必须理解和认识到:Archives仅仅是馆藏档案,而非所有档案!
档案馆界的喜好。虽然直到1979年前,Archives没法律上的定义,但法国档案馆工作者协会AAF的定义得到本国档案馆界多数的认可。但是这个共轭概念因其站位和视角过于褊狭,而且在本国机关团体有自己的档案称谓dossiers、其他国家语言中通常采用同词根的不同词来区别档案馆与档案的情况下,(其他国家的档案馆与馆藏档案是不同词,如,德国:archiv;archivalien。丹麦:archivet;archivalier。荷兰:archief;archieven。意大利: a r c h i v i ; a r c h i v i o 。西班牙: a r c h i v o ;archivos;美国:Archives;records。)法国档案馆界依然非常喜欢这个不太科学的共轭词,这种自豪的尴尬是法国(也许是法语国家)所独有。①从工作环节看。有人总结档案馆的核心业务5C:控制contrôle、收集collecte、整理classement、保存conservation、利用communiquer。显然5C对应的是纯档案馆工作,不包括机关档案dossiers的形成归档业务环节。②从职业偏好看。19世纪下半叶,随着档案馆管理的基本原则的出现,档案馆员作为一种独立的职业出现了。法国档案馆人自豪地说,“我们是档案馆员,因为我们在档案馆工作”on était archivisteparce qu’on travaillait aux Archives。[27]可见档案馆员与档案馆也是绑定的。1829年11月11日的法令又创造了“古文字学家档案馆员”archiviste-paléographe的称号,并为档案学校毕业生chartistes在档案馆和图书馆工作保留了优先受聘的权利。在1831年至1847年间的毕业生49人,有30人在档案馆工作,7人在图书馆工作。③从理论著述看。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70年代,法国有关档案工作著述、手册、概要(见后)及AAF词汇表,都是介绍、阐述档案馆工作。法国这一“馆”与“藏”同词的概念偏好存在一个问题:有时会出现理解上的困惑。在实际应用中法国档案馆界为避免歧义,使用了普遍接受的书写惯例,即以大写A表示档案馆机构,小写a表示档案馆藏文件。
档案馆藏的含义。综上可知法国档案概念特点:①概念上同词共轭。与其他非法语国家不同,法国档案馆界,Archives是个两个概念(档案馆、档案馆藏)同词的共轭体,它所带来的麻烦是,在没有上下文时,不知说的是馆,还是材料,即便有上下文,也避免不了“a保存a”“到a查阅a”的尴尬。②内涵上馆外无档。1961年以前,法国档案馆之外的档案都不叫Archives;1961年后,尽管将机关档案称为现行、中间档案,但AAF的词汇表中说明,当a单独使用时,还是指馆藏档案。正是这种因热爱忽视逻辑、用浪漫代替科学、依主观损害认知的概念体系不严谨带来的麻烦,给概念转义及创新带来混乱。
2.2.7 佩罗汀的三个时段。国家机关档案如同一片沃土,是法国档案馆藏的主要来源。然而馆藏档案与档案馆的概念共轭,限制了与机关档案的联系。为应对二战后档案文件的激增、优化档案进馆,国家档案馆开始将业务逆向延伸到机关。1952年设立“档案馆特派团”(特别任务组)Missions Archives,向主要部委派驻“特派档案馆员”Archiviste en mission;1961年提出三个时段理论,引起馆藏档案概念内涵的第一次嬗变。
机关档案与特派团员。①国家机关档案。由前述法国档案历史可知,机关自己保存的档案不叫Archives,而是纸张普及后广泛采用的dossiers。法语“dossier”是指与事务有关并放置在卷夹中的文件集合,相当于英语中的案卷夹folder、案卷file和档案records三个词的含义。folder指物质性;file表明经分类整理;records强调有机整体及其本质。[28]如文书档案dossiers documentaires、人事档案dossiers de personnel、技术档案dossierstechniques、许可档案dossiers d'autorisation、诉讼档案dossiers de procédure、传统档案dossierstraditionnels、病历档案dossiers medical、纸质档案dossiers papier、档案类别catégorie de dossiers等。这与英美的records一样,都是在文件documents立卷归档后形成,甚至在进入到当代档案馆藏中心也称dossiers。如,仅在巴黎地区的170个拥有国家职能的机构,每年就形成大量档案dossiers。在《中央行政机关当代档案的处理》[29]《国家档案馆当代档案馆藏中心处理和保存的公务员档案》[30]这两篇文章中,档案dossiers共107处,而所谓档案馆工作所遵循和运用的所谓“来源、原始顺序、全宗”原则,均指向原生态机关档案dossiers,因为档案馆中处理的主要对象就是机关的dossiers。“全宗”概念是档案馆藏组织的基础:文件不是单独处理的,而是在同一来源的档案dossiers集合体,dossiers的出现要早于Archives。
②档案馆特派团。为应对档案文件暴增的压力,为减轻将来移交给档案馆带来的压力,1952年法国国家档案馆在局长查理·布雷班特Charles Braibant主持下,开始向主要部委派驻档案馆特派团,指导和协助机关档案的整理和移交准备。布雷班特早在海军部任职时,就产生了应当管理“活档案”Archives vivantes即dossiers的想法:为什么档案馆员不应该负责指导机关的档案整理aménagementen dossiers呢?[31]由于机关档案过去不受重视、缺乏人员培训,有些机关案卷dossiers有的同一主题有多个副本,有的包含着重复文件,有的没有规律和秩序,有的没有时间顺序。储存上也处于混乱:没有适当的分类标准,堆放在橱柜里,没有管理和查找的标识。档案馆特派团通过监督档案销毁或转移到枫丹白露的方式,定期清除不再使用的机关档案dossiers(相当于驻部委档案移交业务指导),而出于对特派档案馆员工作的肯定和信任,有些机关的档案库magasins后来被移交给特派团。截至1987年底,特派团管理的机关档案dossiers达到36km。在完成对准备移交档案的处理的同时,特派团设法组织对机关所形成、积累的所有档案进行检查,但受到有些机关的冷淡,甚至是敌意,因为没有法律文件要求他们接受。但档案馆开始意识到机关档案管理的重要性。[32]
三个时段理论的形成。1961年,法国塞纳河-巴黎大区档案馆长伊夫·佩罗汀Yves Perotin,在多次考察英美档案工作后认为,法国行政机关和档案馆之间彼此忽略的“无知”,对行政管理和历史研究都造成了严重的损害,特别是对法国档案管理保存,仅是从dossiers离开机关那一刻才开始表示痛心疾首,因此必须“向我的同胞们布道”[33]:法国应当将行政机关文件归档后的“命运”分为三个时段:Archives courantes、Archives intermidiaires及Archives archivées,对应美国的现行档案current records、中间档案intermediaterecords及馆藏档案archival records,即档案“三个时段理论”théorie des trois âges。佩罗汀将中间时段称为档案dossiers的“主要价值降低的时代”并在“沉淀”décantation中,“使档案dossiers得以成熟mûrir”。[34]他还提出创建法国式档案管理recordsmanagement的想法,因为如果不在档案形成阶段进行改革,档案馆藏空间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同时他建议档案形成部门对现行和中间档案开展预进馆pré-archivage工作。
三个时段理论打破了传统共轭概念的束缚,将档案馆的业务向前延伸至机关,同时引起档案中间库的实验。新理论看似跳出共轭概念,但基本概念的改变将牵扯到一系列概念和问题,并把简单的东西搞复杂了。这一理论引起法国档案馆界大讨论,国家档案馆内部也意见不一,特别是对设置中间库的争议及对档案新概念体系的质疑。如archivage是archiver名词化,相当于versement,是向档案馆移交、进馆之义。虽然已经应用,但迄今未收入新版《法兰西学术院词典》。现在由于将机关档案也视为Archives,所以archivage又用作归档,那pré-archivage到底是进馆前、还是归档前?成为一个悖论。如何定义pré-archivage,是档案馆员“对尚未分类的文件在最终进入档案馆之前的临时归档”,还是“移交之前在管理场所进行的分类工作”?[35]法国档案馆员专业友好协会曾专门将pré-archivage作为年度研究主题,各省档案馆的意见也不尽相同,更多的是质疑中间库的效果及经费、人员谁负责。
迪香的档案概念认知。法国档案总局技术处处长迪香,曾任驻建设部特派档案馆员,对机关档案dossiers熟知,也赞同介入机关档案管理。他在解释和阐述三个时段时就是用dossiers而非Archives。迪香认为,档案过程的两端,一端是机关的现行档案dossiers courantsd e s b u r e a u x , 另一端是进馆的最终档案d o s s i e r sdéfinitivement archivés。[36]显然法国有现成的机关档案概念。如1970年他的文章中28次使用dossiers解释机关档案。但档案馆界的主流不认同迪香的认知,权威决策者也不情愿接受,而代之以基于传统观念的gestion desArchives或gestion de l'archivage的近似等价的迂回说法,以维护Archives突破共轭的概念扩张,就是不愿意直接简洁地采用dossiers来描述机关档案管理。法国档案馆界根深蒂固的、僵化的心态根源,来自于对档案馆工作者的传统教育,即档案学院150多年里完全聚焦于馆藏历史档案管理、保存和古文字识别,根本不关心档案的形成和管理。
在比较美法档案概念体系后,迪香更喜欢并主张优先采用Records Management概念术语,也就是法国的gestiondes dossiers。[37]其原因是:①概念关系清晰。英美的document是已形成但尚未验证的文件;“records”是已验证、归档的档案;“Archives”是指具有历史价值并进馆的馆藏档案,三个概念关系递进、逻辑合理、清晰明确,而法国原本只是馆藏才是Archives,机关则不是。②倒叙不如正说。因为a是馆与藏互为条件的,现在用更多解释性概念来描述机关档案,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而records就没这个问题,无论在机关还是在档案馆,都是指档案。所以a向前端延伸实际上是倒推,不得不加上现行、中间的限制词来区分。③适应信息时代。档案形成于机关,信息时代依然如此。应当依据现实建立概念,而非用尚不存在概念套现实。④高傲回归正常。法国档案馆界不允许采纳records或dossiers的根本原因,就是放不下身段尊严和高傲。所以只有回归平常心态、合理逻辑,才能更好地协调档案工作。即使不用records management,也有法语的gestion dossiers。
失败的预进馆中间库。1967年法国退出北约后,政府将位于巴黎郊区枫丹白露的北约总部大楼划给了三个时段理论引导下的中间档案馆库dépôt d'Archivesi n t e r m é d i a i r e s 实验项目。该项目由国家档案馆与财政部预算司的中央机关及职能处Service C e n t r a ld'Organisation et Méthodes(SCOM,负责从财政角度审视和协调机构设置及工作方法)共同管理。1969年在此建立了库容达2 8 0公里排架的部际档案城c i t einterministerielle des Archives,与特派档案馆员协作,收存中间档案,相当于预进馆的中间库。与此同时,一些省也组织了预进馆实验,在省政府办公室建立“小型档案室”petites Archives。
什么是预进馆?这种“法式预进馆”,就是效仿美国的档案中心Records Center,管理中间档案,相当于records management,即将档案馆的业务由馆内延伸到档案的形成与管理。[38]英国公共档案馆的Hilary Saw用法国理念向法国同行介绍英国机关档案管理时,用的就是préarchivage。[39]
总体而言,法国的预进馆中心有助于改善组织与档案工作者之间的关系,确保档案更合理地移交到档案馆。然而,它未能改善组织本身的档案管理,除非是临时、示范性的业务指导。但对预进馆试验项目的必要性和利益,法国档案馆界分歧严重。支持的认为“预进馆使档案dossiers成熟”,档案馆、研究人员和管理部门都受益;坦率的敌意则直言,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意义;反对的认为,这是在不了解整体机制的情况下添加齿轮。“特派员”不会对他发送到中间馆库的收藏负责,他只是与现行政机关的联络员,也不会融入后者的结构,因而无法发挥真正积极的作用。[40]随着档案的涌入,档案城在管理方面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保管费用纠缠不清,也有很大争议:是机关负责还是档案馆负责?1985年,SCOM在改革中被撤销;该项目不得不放弃其最初的目的——预进馆库,而回归档案馆保存永久档案的使命。1986年,部际档案城改名为当代档案馆藏中心Centre des Archivescontemporaines(CAC),“是国家一级当代行政资料documentation administrative contemporaine的永久馆库”,由国家档案馆总局管理,1996年开始接待研究人员。
档案馆藏概念的嬗变。根据一般档案工作知识可知,形成档案的是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长久保管档案是各级各类档案馆。机关企事业档案工作始于文件的立卷归档;档案馆工作源于对历史档案的收藏,两者的起点不同。但在法国,由于档案馆界对档案工作的认知和思维是基于历史和馆藏,而不是整体视角及所有档案,因而在1960年前,档案馆和馆藏档案概念共轭于Archives,不包括机关档案dossiers。在三个时段理论指导下,内容突破了容器,向前溯及其来源,致使100多年共轭概念解体。为了尽量维护这种共轭的尊严,法国档案馆界也是拼了,绞尽脑汁发明了现行、中间Archives,同时为了解释档案馆藏的主体和主导性,又发明了预进馆(或预馆藏)pré-archivage。但这里出现了不可调和的逻辑悖论:因为archiver(动词)、archivage(名词)原本就是进馆,也就是移交versment。预进馆就是还没进馆,那到底是不是档案?所以一个基本概念不准确、不科学,还要用其他概念去修补,结果越补越是漏洞百出,形成对其他国家烧脑的概念体系。
为何法国档案馆界不采用原本就是档案的dossiers、就像英美用records指代档案一样,非要用繁琐的现行、中间Archives代替简约的dossiers呢?有几个原因:站位上,以档案馆为基点和视角看待一切,绝不接受其他档案概念。认知上,档案馆藏具有高贵意义sens noble,进馆是dossiers或文件高贵化anoblissement的过程。[41]宁可含混、复杂地再造,也不用明晰、简约的现成概念!这涉及档案馆界的面子和尊严。心态上,档案馆员是有专业的职业,而机关档案管理者则没有。体系上,法国没有统领所有档案的机构,1959年成立的法国档案馆总局属于文化部,不管机关档案业务。总之,如果法国档案馆能放下“历史”“遗产”“馆藏”的高傲身段,采用原本就是档案的概念,比现在用一个困惑的概念解释另一个要好得多。遗憾的是,高傲的档案馆界不但不会向现实低头,反而在1979年以法律的名义向自己的源头——文件发起挑战。
2.2.8 档案馆藏管理手册。①档案馆管理员手册。为了给正在蓬勃发展的地方档案馆的事业和档案馆员提供服务,1860年,曾是皇家图书馆手稿部雇员,后担任法国内政部“档案馆局”Bureau des Archives主任艾梅·商博良-菲雅克(他是巴黎卢浮宫埃及藏品馆长、法国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号称破译罗塞塔碑古埃及文字的商博良的侄子)出版了《区县、市政厅及宗教慈善机构档案馆管理员手册》Manuel de l'archiviste des préfectures,des mairies et des hospices 。他的背景和职位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是最适合的人。《档案馆管理员手册》(简称《手册》)分为五个部分,前面有古代档案馆历史和现代公共档案馆的介绍。第一部分,省级档案馆。它细分如下:1841年以来国家及省市有关档案馆工作的立法、法令、通告、指示、清单公布、政府下令进行的研究、一般检查、咨询委员会;以及1841年之前的同类文件构成了该系列的历史或先例的立法和行政文件汇集。第二部分,市档案馆。第三部分,宗教慈善机构档案馆。第四部分,区县行政图书馆。因大革命后很多档案被划归图书馆保存。第五部分,1860年区县、市政厅和宗教慈善机构档案馆名录。[42]这最后一部分实际上是个特殊的附录,主要介绍一些文件及档案馆的情况:包括省级、区县的档案馆员,他们的名字、荣誉称号、待遇、出版物;关于某些省、市档案馆的通告、清册编辑、理事会审议、行政决定、目录编辑等,其中还穿插有注释、评论或意见,可满足档案馆员的管理知识需求,为档案馆和档案馆员提供了实用的参考。
②档案馆藏管理手册。1860年《档案馆管理员手册》出版后,历经帝国、第三共和国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的法国,无暇顾及档案馆发展。面对1898年荷兰的《档案馆藏分类和著录手册》Manuel pour le classement et ladescription des Archives、1928年意大利尤金尼奥·卡萨诺瓦Eugenio Casanova的《档案馆藏》Archivistica、1953年德国阿道夫·布伦内克Adolf Brenneke的《档案馆藏学》Archivkunde,法国仅有1883年加布里尔·里丘Gabriel Richou的《论公共档案理论与实践》Traitéthéorique et pratique des Archives publiques。意识到这一差距,AAF于1961年6月15日决定开始完成法国档案馆界所缺失的整体工作短板。在AAF组织下,42位具有档案馆经验和专业实践成果的专业人士参与,共同编写了《档案馆藏管理手册》Manuel d'archivistique。
该手册于1970年出版,是法国公共档案馆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第一本涉及档案馆藏管理所有问题的书,包括概要和四个部分。概要部分,介绍了档案馆一般定义及有关档案馆藏的理论;法国档案馆的组织、立法和演变。第一部分,一般档案馆藏管理概论。这部分是本手册的“核心”,涉及一般档案在其存在的各个阶段的处理所带来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包括:办公室中档案的形成formation dans les bureaux和预进馆préarchivage;定期移交versements réguliers;分拣和销毁triages et éliminations;分类和编目classementet cotation;研究工具instruments de recherche;研究和利用recherches et communications;副本交付和摘要délivrance de copies et extraits。第二部分,档案馆藏管理。分为两部分:特定类别收藏与特定类型文件。前者包括市镇档案馆Archives communales(包括城市档案馆Archives des villes、农村社区档案馆Archives des communes rurales);医院档案馆Archives hospitalières;公证人和其他公共及部级官员的档案Archives des notaires et des autres officierspublics et ministériels;家庭和个人档案馆;协会档案馆Archives d'associations,即所谓的“经济”档案和商会档案;宗教档案馆Archives cultuelles(包括天主教catholiques、新教protestantes、犹太教israélites)。后者包括:印章和密封文件sceaux et les documentsscellés;地图文件documents cartographiques;图像文件documents iconographiques;印刷品档案Archivesimprimées;报纸和期刊集collections de journauxet de périodiques;缩微胶片和各种形式的缩微拷贝microfilm et les diverses formes de microcopie;视听文件documents audio-visuels;机械和电子文件documents mécanographiques et électroniques。第三部分,文件的实体保存保护。主要面向专业人士,总结了档案建筑和设施以及受损文件的处理和修复两个领域的经验和理论。第四部分,档案馆藏在科学、文化和行政方面的作用。将档案馆置于当今社会的总体框架中,探讨了档案馆与科学生活(如作为历史研究的中心;图书馆);与文化活动(展览和档案博物馆;档案馆的教育活动);与行政文献的互动作用。[43]
通过章节内容可知,《档案馆藏管理手册》主要是针对档案馆,开头提及机构档案的形成和预进馆,是依据20世纪60年代出炉的三个时段理论、面对机关文献大量增加带来的“新挑战”的拓展,但三个时段理论的拓展也遭到档案馆界内部的激烈批评。国家档案馆的艾丽丝·吉耶曼Alice Guillemain当年就撰文剖析档案馆界以历史为立足点看待整个档案工作的弊端。[44]
2.2.9 档案概念话语体系。在了解法国大革命后国家档案馆工作的历史后,我们可以在英、法对比中来理解法国现代档案馆藏概念的话语体系:如果说英国的档案工作始于王国中书省及财政法庭的行政、司法及管理中文件的形成归档,那么现代法国档案工作的起点或Archives的形成,就是始于“将机关档案dossier移交进档案馆之时”。[45]换句话说,英国有形成和保管档案的机关档案工作和永久保管档案的档案馆工作,而法国只有档案馆工作,没有机关档案工作(实际上不是没有,而是不叫Archives,所以不在其档案馆人的法眼中)。
国家档案馆库。档案馆A r c h i v e s 或d é p o td’Archives;前者主要指机构,后者指馆库实体。法国的各级档案馆遍及全国省区市镇。国家档案馆成立后,在共和国、帝国、王国时期,直到1897年,都是单一独立机构;1897年至1970年,与国家档案馆局是合一机构。档案馆所有工作都基于传统的历史观,目的是确保国家书面记忆的收集、保护、科学处理、利用和价值延续(迪香·爱丽丝),其本质上是履行遗产使命vocationessentiellement patrimoniale,因而档案馆基本上与行政治理、管理及司法无关,是个纯文化、遗产机构。
法国档案馆局。1 8 9 7年,国家档案馆A r c h i v e snationales和内政部档案馆局合并后,在公共教育部下设立了档案馆局Direction des Archives(不是档案局!因为不管机关档案,只管全国的档案馆),成为两种职能合一的机构;1936年改为法国档案馆局Direction desArchives de France。1959年2月和7月的法令将档案馆局改为总局,归文化事务部。20世纪70年代,法国档案馆总局组成是:①技术处(负责省级档案馆管理、档案馆藏管理问题研究、组织到档案馆实习等);②人事办公室;③财务控制和材料管理办公室;④国家档案馆。法国档案馆总局的行政职能是,档案馆收藏与利用政策的设计和实施;法规拟定;对档案馆的监督、组织协调;技术支撑及资源持续进馆。显然,法国档案馆局没有对档案形成机构的监督职能。对此吉耶曼认为:我们不应该仅凭历史标准、只关注“晋升为‘历史档案’级别的文件”。这种对机关档案行政管理的缺失表明,我们仍然是19世纪历史学派的囚徒。[46]
档案馆藏档案。《穑月法令》以来的2 0 0 多年,Archives指档案馆是没有争议的,但在档案材料实体含义上,在1979年以前却一直没有法律的界定,只是档案馆界或行业学术词典将档案馆中保存物称为Archives:广义上指档案馆藏,即档案馆收藏物,哪怕是文件、图书、奖牌、手稿、海报、剪报、字画等;狭义上是指馆藏档案,即机关形成满50年或若干年、并已经移交给档案馆的档案dossiers。20世纪60年代三个时段理论在得到某种程度认可后,在法国档案馆界(而非全社会),Archives由馆藏档案之义嬗变为指所有档案,即包括机关形成并保存的所谓现行档案及中间档案,原本互为条件的同体概念被撕裂。但在实际应用上,如果行文中只出现Archives一词,那么还是指馆藏档案;只有明确写出Archives courant,才表明是指机关档案,即dossiers。
档案馆工作者。在法国,不存在“档案工作者”,只有“档案馆工作者”(档案馆员),即Archiviste;从法国档案学院毕业后进入档案馆的,称为古文字档案馆员archivistes paléographes。在档案馆工作还有一个称号就是保管员conservateur。据说法国大约有2000名档案馆员、7000名机关资料员和10000名有资格人员。国家档案馆及后来的档案馆局、法国档案馆局负责人的头衔为:档案馆总馆长Gardes généraux(1789—1852);档案馆总馆长Directeurs généraux(1852—1870);档案馆局局长Directeur des Archives(1897—1936);法国档案馆局局长Directeur des Archives de France(1936)。
机关团体档案。机关团体档案Dossiers,是档案馆界主流不承认、但在实践中广泛存在的档案概念。Dossiers只有被档案馆选中并进入到档案馆才是法国档案馆界眼中的档案。这是法国档案馆界视角和思维的局限所导致:仅站在历史、遗产的角度看待档案事物的结果。实际上法国机关本来就有机关档案dossier,比Archives还早,如文书档案dossiers documentaires、人事档案dossiersdes personnels、病历档案dossiers medical、客户档案dossiers client等。联合国机构中档案管理的英、法文分别是records management和gestion des dossiers。档案dossiers进入联合国档案馆后才称为馆藏档案Archives。(见联合国文件JIU/REP/2013/2)法国档案馆界视而不见地将其改称为现行和中间Archives,反过来却又说法国不存在类似英美的records。
档案馆藏法律。除前述1794年穑月法令(国家档案馆重组)、1796年雾月法令(设立省档案馆)、1800年牧月法令(国家档案馆独立)之外,法国还有不少有关档案馆的法令:1841年关于省档案馆的法令。1855年12月法令,将所有公共利益有用的文件移交帝国档案馆。1887年5月法令,要求中央行政部门将不再需要的所有文件直接移交给国家档案馆。1897年法令,设立档案馆局Direction desArchives。1936年7月的法令,关于部委及所属行政部门的行政管理档案dossiers移交到国家档案馆;12月的阿尔伯特·勒布伦Albert Lebrun总统法令将档案馆局称为法国档案馆局direction des Archives de France。[47]但法国没有关于机关档案dossiers形成、积累、管理和利用的法令,机关是根据自身的档案规章来管理。
传统观念固化。理解法国档案工作概念体系最大的困惑是,本来档案概念dossiers形成在先(14世纪),馆藏档案在后(18世纪),以dossiers指代所有档案,如同英美的records,所有概念混乱即可迎刃而解!但现代法国档案馆界非常喜欢Archives这一共轭概念,甚至自我培养出莫名其妙的高贵感觉,还不惜在跳出共轭时靠添加时段的烦琐和悖谬,也要牢牢戴紧Archives这顶“贵冠”(不是桂冠)。然而现在除讲法语的国家外,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档案与档案馆都不是同一词。这一两种含义的同体词,还不如法国中世纪的宝藏Trésor与档案chartes,或档案室chartrier与档案chartes科学!如果是档案馆界自娱自乐还马马虎虎,但当试图向前延伸到机关,或者遇到信息时代的电子档案(后面会看到),必然带来混乱和麻烦。因为档案与档案馆本非同体:档案是形成且来自于档案馆之外!用Archives取代dossiers“是在建立一种倒退的概念”。[48]我们将在1979年看到法国档案概念嬗变之再嬗变的混沌!
参考文献:
[1]Michel Duchein,Requiem pour trois loisdéfuntes,La Gazette des Archives,1979,104,p.12-15.
[2]Paul Delsalle,Le recyclage des archives pourla fabrication des gargousses en l'An II,Revue duNord,1993,299,p.116.
[3]Pierre Santoni,Archives et violence.A proposde la loi du 7 messidor an II.La Gazette desarchives,1989,146-147,p.212.
[4]Henri Bordier,ARCHIVES DE LA FRANCE,Paris,1855,p.2.
[5]R.C.Head,Documents,Archives,and Proof around1700,The Historical Journal,Volume 56 ,Issue4,2013,909-930.
[6]Isabelle Chave,Napoléon Ier aux Archivesimpériales(1852-1870) :stratégie des preuves etaffirmation dynastique,Dans Napoleonica.La Revue2016/2(N° 26),P.105-173.
[7]Paul Delsalle,L'archivistique sous l'AncienRégime,le Trésor,l'Arsenal,et l'Histoire.Histoire,économie & société,1993,12-4,p.462.
[8]Jullien-Dubois,Rapport,Archives Parlementaires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Tome XCII,19 juin au 8juillet 1794,pp.177-180.
[9]Pierre Santoni,Archives et violence.A proposde la loi du 7 messidor an II.La Gazette desarchives,1989,146-147,p.208.
[10]Pierre Santoni,Archives et violence.A proposde la loi du 7 messidor an II.La Gazette desarchives,1989,146-147,p.212.
[11]Odile Krakovitch,La responsabilité del'archiviste :entre histoire et mémoire,La Gazettedes archives,1997,177-178,pp.236-240.
[12]Germain Poirier,LENOIR,BÉNÉDICTIN,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France,1835,Vol.2,No.2,p.254.
[13]Pierre Santoni,Archives et violence.A proposde la loi du 7 messidor an II.La Gazette desarchives,1989,146-147,pp.207.
[14]Michel Duchein,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esarchives :la mémoire et l'oubli dans l'imaginairerépublicain,La Gazette des archives,Etudesd'archivistique 1957-1992,1992,p.65.
[15]Michel Duchein,Requiem pour trois loisdéfuntes,La Gazette des Archives,1979,104,p.12-15.
[16]Isabelle Chave,Napoléon Ier aux Archivesimpériales(1852-1870) :stratégie des preuves etaffirmation dynastique,Dans Napoleonica.La Revue2016/2(N°26),P.105-173.
[17]Maria Pia Donato,Des hommes et des chartes sousNapoléon.Pour une histoire politique des archivesde l’empire(1809-1814),Dans Annales historiques1814),Dans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française,2015/4(n° 382),p.85-95.
[18]Bruno Texier,Napoléon,un "confiscateurd'archives" désireux d'écrire sa proprelégende[EB/OL].[22-01-2021].https://www.archimag.com/archives-patrimoine/2021/01/22/napoleonconfiscateur-archives-ecrire-legende.
[19]Maria Pia Donato,Les archives du monde :quandNapoléon confisqua l’histoire,PUF,2020,pp.276.
[20]刘平.《蒙娜丽莎》的旅程:艺术品的迁移史[J].美术,2022(09):122-128.
[21]GUY STAVRIDES,Quand Napoléon confisqual’histoire - Les archives du monde,HistoireMagazine,N°9,Napoléon,2022,6 JANVIER.
[22]DE LABORDE,LES ARCHIVES DE LAFRANCE,PARIS,1867,P.191.
[23]Amédée Outrey,Sur la notion d'archives enFrance à la fin du XVIIIe siècle,Revue historiquede droit français et étranger,1953.No.2,p.282.
[24]Françoise Hildesheimer,Échec auxArchives:la difficile affirmation d'uneadministration,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chartes,1998.156-1,p.95.
[25]Françoise Hildesheimer,Échec auxArchives:la difficile affirmation d'uneadministration,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chartes,1998.156-1,pp.104-106.
[26]Françoise Hildesheimer,Échec auxArchives:la difficile affirmation d'uneadministration,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chartes,1998.156-1,pp.101-104.
[27]Sandra FULLENBAUM LENFANT,Les archivistesentre identité professionnelle et identitépersonnelle,Universite angers,7 juin 2019,p.31.
[28]Johnatan Joly,Dossiers documentaires:techniques et enjeux,p.12[EB/OL].[2013-3-21].https://memsic.ccsd.cnrs.fr/mem_00803362.
[29]Christine Pétillat et Anne-Claude Lamur-Daudreu,Le traitement des archives contemporainesdans les administrations centrales,Gazette desarchives,1988,141.pp.35-56.
[30]Christine Pétillât,Les dossiers des agents dela fonction publique traités et conservés par leCentre des archives contemporaines des Archivesnationales,Gazette des archives,1999,186-187.pp.227-231.
[31]Charles Braibant,Les Archives de France.Hier,aujourd'hui,demain,La Gazette desarchives,1951,9.p.13.
[32]Édouard Vasseur,French archivists,themanagement of records and records managementsince the nineteenth century,ARCHIVES ANDMANUSCRIPTS,2021,VOL.49,NOS.1-2,p.113.
[33]Yves Pérotin,L' administration et les «troisâges » des Archives,dans Seine et Paris,n°20,octobre 1961.
[34]Robert Avezou,Synthèse des conclusions desréunions régionales d'archivistes français de 1963sur le pré-archivage et l'avenir des archives,LaGazette des archives,1964.Suppl.44.p.7.
[35]Robert Avezou,Synthèse des conclusions desréunions régionales d'archivistes français de 1963sur le pré-archivage et l'avenir des archives,LaGazette des archives,1964.Suppl.44.p.7-9.
[36]Michel Duchein,Le pré-archivage:quelquesclassifications nécessaires.La Gazette desarchives,1970.71,p.227.
[37]Michel Duchein,Le pré-archivage:quelquesclassifications necessaries,Gazette desarchives,1970,71,pp.229.
[38]Françoise Durand-Evrard,L'évolution de lanotion de pré-archivage en France,Gazette desarchive,1995,170-171,pp.370-376.
[39]Hilary Saw,Le pré-archivage des archivesminist3y9icbW9hLPcgeOjAr69Wg==érielles anglaises et galloises,Gazette desarchives,1995,170-171,pp.364-369.
[40]Alice Guillemain,Les archives en formationet le pré-archivage:réflexions à propos d'unchapitre du Manuel d'archivistique,La Gazette desarchives,1970,71.p.258.
[41]Mathieu PASQUIER,L'acculturation du recordsmanagement dans la pratique archivistiquefrançaise,Universite de Lyon,2016,p.23.
[42]Auguste Vallet de Viriville,Les Archivesdépartementales de France:Manuel de l'archivistepar Aimé Champollion-Figeac.Bibliothèque de l'Écoledes chartes,1861,22.pp.298-299.
[43]Gazette des Archives,Le Manuel d'archivistiquede l'association des archivistes français,LaGazette des Archives,1970,71. pp. 221-224.
[44]Gauye Oscar,Association des archivistesfrançais.Manuel ďarchivistique.Bibliothèque del'École des chartes,1971,129-1.pp.149-151.
[45]Michel Duchein,Législation et structuresadministratives des Archives de France,La Gazettedes archives,1988,141.pp.7-18.
[46]Alice Guillemain,Les archives en formationet le pré-archivage:réflexions à propos d'unchapitre du Manuel d'archivistique,La Gazette desarchives,1970,71.p.258.
[47]Michel Duchein,Législation et structuresadministratives des Archives de France,1970-1988,La Gazette des archives,1988,141.pp.7-18.
[48]Alice Guillemain,Les archives en formationet le pré-archivage:réflexions à propos d'unchapitre du Manuel d'archivistique,La Gazette desarchives,1970,71.p.258.
(作者单位:国家档案局 王岚,博士,研究馆员 来稿日期:2024-0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