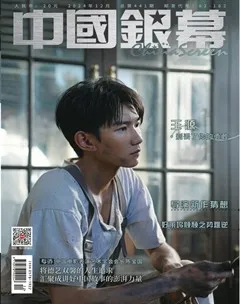管虎 这次真是类型片







《东极岛》
新作挑战难度:★★★★★
2024年6月24日,由管虎、费振翔联手执导的电影《东极岛》官宣开机。在转身拍了作者风格强烈的电影《狗阵》《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后,管虎又将目光转回商业主流大片制作,继《八佰》《金刚川》之后时隔四年执导《东极岛》。这一次,管虎想将类型片放在首位,“拍摄《八佰》时,我没有特别想做类型,反而片中有很多反类型叙事,但《东极岛》就是类型电影。”制片人梁静则透露,“《东极岛》很难拍,其耗资和制作时长几乎相当于三部同题材电影。片中水面、水下和岛三个场景的控制都很难,操作难度极大。” 可以预见,相较《八佰》《金刚川》,《东极岛》在制作上将全面升级,承载着管虎探索中国电影工业化的野心,同时亦是他“回归”中国电影最具商业票房号召力导演行列的又一力作。
导演挑战:
高难度“海难”拍摄
在第六代导演中,管虎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既有强烈作者风格表达的《斗牛》《狗阵》等影片,也有取得巨大商业成功的《八佰》《金刚川》等影片。同时他的电影几乎都聚焦于小人物的命运起伏,其内核大多蕴含着对现实的严肃反思。在《东极岛》中,管虎一边挑战战争大场面,呈现巨轮沉没的浩大海难以及“百舸争流”的热血海战等等,一边不忘将镜头对准“小人物”——渔民,探讨战争背后的残酷与人性。如其所言,他在筹备《东极岛》过程中始终没有怀疑的,是“一群普通人能在这么大的海难中,去营救一千多国际友人,这是一个很动人的故事,我每次回顾都会热泪盈眶”。关注大历史,但更关注小人物;一面是战俘海上渺茫的“求生”,另一面是渔民海底更渺茫的“救人”,都是管虎将这一真实历史事件搬上大银幕的意义。
关于《东极岛》的拍摄难度,或许可以从公布的概念海报窥知一二。海报上,岸边和远海犹如两个世界,岸上和近海的渔民在眺望海中;而海上巨风卷浪、巨轮倾覆在即,货轮中的战俘犹如身处人间炼狱。横亘在管虎面前的“第一个难”,便是《东极岛》涉及大量水戏拍摄。据他透露,团队花费了4年多时间克服技术和剧作难题,这大概也是《东极岛》迟迟未开拍,管虎转而先拍摄《狗阵》《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原因之一。迄今为止,中国电影从未有过呈现超千名战俘遭遇巨轮海难的先例,诸如吴宇森的《太平轮:彼岸》关于海难的制作并不尽如人意。放眼全球,《泰坦尼克号》《敦刻尔克》等影片的“海难人数规模”大约也不及《东极岛》。而且巨轮造景的一切构想,最终转化成一个土木工程的施工方案。这个巨大工程的细节以及“演员调度”的复杂程度,都极其考验管虎掌控商业大片的能力。据悉剧组仅1:1复刻“里斯本丸”号货轮就花费了大量时间。
对管虎来说,他的“难”既包括《东极岛》水戏拍摄规模,也在于还原海难场面。尽管经历了《八佰》《金刚川》等商业大片的“洗礼”,管虎还是认为《东极岛》的挑战难度是空前的。他感慨,“这是中国电影首次尝试这样的技术难度”。海难再现、海上实拍、海岛搭建、海船复刻,《东极岛》无疑是继《八佰》《金刚川》后,管虎导演为探索中国电影工业化之路又迈出坚实一步。
新片猜想:
直面残酷战争
电影《东极岛》于2021年8月立项公示,其筹备可以追溯到更早之前。影片讲述在二战后期的1942年,满载英军战俘的货轮“里斯本丸”号在我国浙江东极岛海域沉没。事故发生后,日军将战俘锁于船底,当地的中国渔民发现后,不顾危险展开了一场极限营救。如果说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让观众了解这一真实历史事件的“前世今生”,那么《东极岛》在“有史可依”的基础上,插上想象的翅膀和中国电影工业化的力量,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八十多年前的“惊心动魄”。
制片人梁静透露:“《东极岛》拍摄一半在海上,一半在海下。”此外,影片两位主演朱一龙、吴磊提前进组接受高强度的训练。他们的训练项目包括长时间水下闭气、自由潜水等基础训练,以及水下威亚操作、翻滚腾挪姿势控制等动作特训。据管虎介绍,“现在我们的主演闭气能力已经达到了四分半钟,并且不是静态闭气,而是在运动中的”。从这些曝光的细节不难看出,管虎对“水下拍摄”的严苛要求,以及海中营救场景融合了真海实拍与海景视效,对表演和制作提出了双重挑战。但这样的实拍,带给观众的震撼必然是成倍增长的。
从《八佰》《金刚川》来看,管虎在创作面向市场的主流商业大片时,常常保留了其一贯“粗粝”的影像风格和叙事手法。他喜欢以直白镜头描写和强烈的情境对比方式,呈现战争残酷,并使之成为影片的卖点。在《八佰》中,当四行仓库的将士们拼死抵抗侵略者时,一江之隔的租界却仍花天酒地,头顶盘旋的各国观察团、租界中麻木不仁的同胞,与战争的场面形成了强烈而残酷的对比。在《金刚川》中,吴京饰演的关磊在被敌机击中后,几乎立即变成四分五裂的肉块,以及张飞的断臂、刘浩的尸体等等,管虎直接呈现了这些画面,最大程度上展示了战争的残酷。而从《东极岛》公布的概念海报和故事梗概来看,类似的叙事手法极有可能出现在该片中。从真实历史事件到小人物,从岛上到海上,都给足了管虎发挥的空间。
可以说,管虎拍《东极岛》毫不意外,从《斗牛》开始他的历史世界观就在同代导演中显得与众不同。而走到《八佰》《金刚川》乃至《东极岛》,管虎开始从看个人,到看时代的过渡。同时他以往展现出的对历史题材的掌控能力,足以让《东极岛》备受期待。(文 伯曼曼)
路阳 首拍科幻硬碰硬
《我们生活在南京》
新作挑战难度:★★★★
2024年4月18日,第二届科幻星球奖获奖名单揭晓,作家天瑞说符创作的小说《我们生活在南京》获文学奖·最佳科幻长篇小说奖。就在这一天,《我们生活在南京》也传出启动影视化改编的消息,影片宣布由路阳执导,并公布了概念海报。诠释这部曾霸榜起点读书的畅销之作、呈现未曾尝试过的科幻类型作品,是路阳在《刺杀小说家》之后所面临的全新挑战。他曾经在采访中表示,他拍摄一个故事的前提是“相信这个故事”,故事“真实缝隙下的想象力”,才是他释放自己导演才华的原动力。《我们生活在南京》正是这样一个真实又充满想象力的故事。
导演挑战:
拍好本土新科幻
《我们生活在南京》是导演路阳第一次尝试拍摄科幻电影。在此之前,他执导的《绣春刀》系列电影充满浪漫与人生哲思的江湖斡旋;他执导的《刺杀小说家》也凭借其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真挚的情感底色斩获一众好评。出生于1979年的路阳,拥有中生代导演所具有的探索性和冒险精神,他的作品风格兼具个人特色与大众审美,观众看得过瘾,影片也不乏解读的空间。
尽管《刺杀小说家》已经凭借奇幻世界无缝链接现实世界的奇特构思,展现了导演改编文学作品、呈现异世界图景的能力,但《我们生活在南京》依旧是他导演生涯又一次“跳出舒适圈”的挑战。原著《我们生活在南京》是一部硬科幻小说,有真实严肃的科学技术为依据,小说中关于短波通信及其相关技术的描写缜密细致,这就要求导演对影片涉及的通信工程等专业知识都要有相当的了解,对其中涉及的无线电爱好者以及社会组织等情况也要进行调研,这在路阳的电影中无疑是陌生的第一次。
末日影像视觉呈现是路阳的第二个挑战。小说和电影的名字,指明了这部影片的故事地点就是南京市。如果按照小说的叙事进行拍摄,那么故事将从2019年的视角和2040年的视角分别展开。2040年的南京城,则是“废土末世”版本的南京,明故宫成为废墟,午朝门公园变成原始森林,旁边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道路上都是杂草,马路上有溜达着的鹿、猴子、居住在楼下人类房间里的黄鼠狼……而2019年的现实南京,会让现实生活在南京的观众有强烈的即视感,苜蓿园大街上的梅花山庄、新街口、河西金鹰、南京图书馆这些故事涉及的重要地点都会出现在影片中。2040年南京的呈现,将直接决定这部影片能否取得成功。
新片猜想:
跨越时空 人类自救
在《我们生活在南京》的概念海报上,我们能看到影片的两位主角——荒芜中的少女和骑着单车疾驰的少年。在原著小说中,宇宙未知生物“刀客”来到地球,对人类生命进行收割,末日时代到来。2019年,距离这场末日灾难降临还有5年,生活在南京的高三生白杨,通过无线电与2040年同样身处南京的唯一幸存人类半夏共同抵挡末日危机,展开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救援行动。
路阳将如何呈现末世南京这部分内容?其实在《刺杀小说家》这部电影里,我们就看到他“还原”双雪涛原著小说中异世界的能力。神庙中,赤发鬼身型巨大,有四只手臂,足足15米高,给予了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整部电影色调冷峻凌洌,极具高级感。当时,路阳的制作团队使用了20多个摄影棚和先进的“动作捕捉”和“虚拟拍摄”技术完成了这部影片。或许,在《我们生活在南京》这部电影里,相似的技术也能重新派上用场。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同为废土末世设定,《我们生活在南京》在西方废土末世设定的科幻电影《沙丘》《疯狂的麦克斯》所呈现出来的内容有很大的区别,这部电影更具有东方文化特色和哲学审美。如何将东方美学融进电影的视觉呈现中去,是非常考验导演的地方。
如果说《三体》的科幻设定是浸泡、脱水、智子封锁,《流浪地球》系列电影的科幻设定是太空电梯、Moss人工智能,那么,《我们生活在南京》的科幻设定,则是末日危机、跨时空通信。影片将在现实和未来两个时间位面上展开故事,通过男女主角如何克服时空冲突这个带有悬疑性的情节设定,将观众牢牢吸附在“人类跨时空自救”这个故事情节当中,以及,除了如何埋置和递送时间胶囊、探索实现“时光慢递”的条件等核心情节,故事中还始终隐藏着一个情感细节——抚慰半夏的精神,帮助她解决困难。半夏作为未来世界最后一个人类个体,被塑造为一个拯救“过去人类”的英雄,让这个故事具有了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这一重大社会意义。
《我们生活在南京》现实感非常强,宇宙浩大、人类渺小的图景在这个故事中一一展开。从网络文学诞生出的故事,注定了这部电影的底色更诙谐、灵动,有无数的“梗”可以戳动年轻观众的心。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生活在南京》在路阳导演以及团队的努力下,可以完美呈现在银幕上,既为观众展现出科幻另一种时空交织的魅力,也为华语科幻电影添上一抹全新色彩。(文 斑马木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