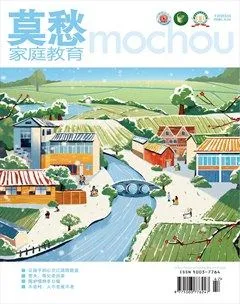围炉慢熬冬日暖
爷爷去世后,爸爸和叔伯们都劝奶奶来城里生活,可她执意不肯。我想不通老家有什么好的,那里没有小桥流水、绿树环绕,不过是些矮墙土房罢了。特别是进入秋冬季节,一天比一天沉寂,除了几声鸟鸣和狗吠能显出些生机,就只有光秃秃的山和灰扑扑的路了。我们拗不过奶奶,只好多回去陪她。看到我们来,奶奶嘴上嘟囔着“人老了也不得清静”,眼角的笑纹却又深了几分。
奶奶不会像其他留守老人那样,每逢周末就徘徊在村口张望。她总是悠闲地坐在院子里,脚边盘着一个火盆,双手像是虚抱着心爱的宠物,还时不时搓摸几下。她的眼神随着跳动的火苗流转,不知是想到了谁,脸也变得红通通的。等我们走近了,她才喊道:“来了,先来烤烤火吧。”我们随便搬块石头或者树墩,将火盆围在中间,挨着奶奶坐下,形成一个圆。
等到冻麻的手指恢复些知觉,身上也暖和了,大家就会掏出口袋里的瓜子花生嘎嘣嘎嘣嗑起来,一边嗑一边往火盆里扔果壳。这时候,奶奶就会站起来咳咳两下说:“哎哟,你们沾了口水的柴火直冒烟啊,能把人熏死,我还是去给你们熬菜吧。”一听熬菜,小孩子们又追着奶奶跑到土灶台前,抢着要干烧火的活儿。堂弟太急躁,总是在秸秆刚点燃时,就把灶膛塞满,没一会儿,火灭了,浓烟呛得他直咳,他猛拉几下风箱,火“呼”一下又蹿出了灶口,他一边叫着:“哎呀,我的眉毛……”一边跳着跑远了。“人心要实,火心要空。”奶奶像唱曲一样重复吟着这句朴素的谚语。我和堂姐相视一笑,她捡起烧火棍捅捅,抽柴,添柴,再用钩子掏一掏漏下的灰烬;我拉风箱,树枝燃烧噼噼啪啪,风箱拉扯呱嗒呱嗒,共同演奏着一首灶台欢歌。
熬菜似乎没有太多的技术要求,因为不管熬什么菜,都很好吃。奶奶常常是先起油锅,爆香葱花和蒜瓣,然后问我们要吃什么,我们会喊出各种各样的选项,比如土豆、海带、小酥肉、豆腐、粉条等等。奶奶把它们陆续加进锅中,并顺着锅沿轻轻翻炒几下,然后盖上锅盖,剩下的只管交给火,慢慢熬煮。我看着这些食材融合在一口锅里,你挤我一下,我拍你一下,你包裹着我,我依偎着你,就像我们一家子大大小小性格各异的人一样,只要抱在一起,就能消弭所有界限,最终散发出绵柔馨香。
奶奶常说:“熬菜软烂又有营养,热乎乎地吃着最是暖心养胃。”就连一向挑剔的小婶婶也赞叹:“真没想到这大锅菜还挺好吃的。”我赶紧抢功劳:“是因为我们的火烧得好。”“是我让放了土豆才好吃的。”大家端着碗吃着笑着,其乐融融。
我看过105岁的日野原重明医生的访谈录《活好》,当被问及家庭是什么时,他的回答是:“家庭就是围在一起吃饭。”我想,我终于明白奶奶为何不肯搬离老屋了。那里虽然只是矮墙土房,但院子里小小的火盆足以照亮每一寸暗淡。家人们围在一起,烤火取暖,共享一锅包容性极强的熬菜,多幸福啊!
岂止奶奶,我们不也眷恋着吗?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最舒适的居所并非豪华别墅,最难得的美食也不一定是精致的米其林大餐。或许,任何人的世间岁月,最动情的部分都是因为家庭团圆和亲情陪伴。
我感恩冬天,感恩我的家人,感恩奶奶,因为他们让我懂得了老家存在的意义;因为他们,我会更加坚定地走过人生的每一个寒冷冬天。
编辑"东篱"62335841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