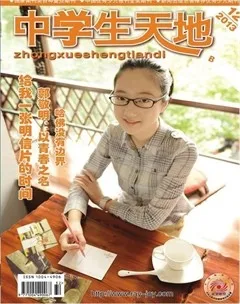鱼
我发了一张照片给罗,照片上是波光粼粼的海面。我说:“这里的海这么宽、这么暖,你应该来看看。”我犹豫了很久,最后决定发送这段文字,打破对话框维持了许久的沉寂。风和,云淡,大海的确能使人的心恬静下来。我目视闪动的海面,想起了罗。
“啪——”清脆又舒心的击球声传入耳中,我看着球在空中画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像鱼跃出水面一样快活。这是我和罗第一次打羽毛球。我俩合作,打得奇烂无比,时不时断球,随后大笑起来。
罗从不嫌我“菜”。后来我发现,无论他和谁打球,都能打得有来有回,势均力敌;而他双打时发挥出的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队友的实力。因此,每当我做他的队友时,总感到愧疚。当我犯了低级错误,比如连发球都失分时,他只是笑笑,什么话都不说。周围的人觉得我们都菜,只有我知道罗深不可测。他接球的眼神平静又辽远,好像深海鱼一般沉潜机敏。
时间回到三年前的一个傍晚,夕阳的余晖从教学楼顶溢出来,溅人满眼。那时我和罗刚相识,很快成了要好的朋友。原因之一是在快节奏的重点班里,罗随和又不失从容的态度让我感到亲近、安心,与其说这是一种“摆烂”,倒不如说这是一种能自我调整的表现;原因之二是我们很相似——都很怀旧,又幼稚,且喜爱想象和写作。
但不得不说,罗的见识比我广得多,无论是理科方面的专业知识还是天文地理、唐诗宋词、时事热点,只要他愿意,总能和别人聊起来。
“你知道‘超弦’吗?”他很有兴致地对我说。我摇摇头表示不知道。当晚我查了一下,是有关时间方面的深奥理论。“没关系,你只要知道我最新的章节会用到这个理论就行。”他说的是他那本想象类小说,至今已创作了九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框架,里面记载着一些冒险故事,人物则以他怀恋的人为原型。他滔滔不绝地对我讲,一边用手比画着,我听得津津有味。沉浸于对话的我们不会知道,那晚的放学铃声早已响过,而班主任竟然也饶有兴趣地站在我们后面听了许久。仔细回味那个傍晚,我只记得空气湿润,地面潮湿,落日投在罗的眼睛里,光线透过他的镜片淌出。有一种错觉让我感到光有了质量,光在罗身上游走,看上去像是滟滟的水波荡漾在蜿蜒的河流上。
“罗,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变成了一条鱼。”
“然后呢?”
“然后你把我钓起来了。”
我俩在吃饭的时候笑起来,笑得很畅快。
高三来得很突然,时间流逝之快让人感到错愕,而罗依然会很热情地和我讨论故事的走向。在我看到高三那“愿君生羽翼,一化北溟之鲲”的标语后,我有些不安地跟他说,也许我们现在不该做这些。令我惊讶的是,罗没有认同我,反而满不在乎地指指标语:“这前后有什么因果联系吗?”他并不完全认同“尽人事,听天命”这一说法,他说命不该被定义,未来也并不唯一。他说人可以焦虑,也可以后怕,但得想到什么就去做什么,而不是在做的时候才想。
“其实也不该想这么多。”他说得透彻,并盯着我,让我产生了一种无言以对的信服。但我心底仍害怕因接受这种观念而耽误正事。此后,我与罗投入聊天的时间愈来愈少,那段故事似乎也被搁置了。
天变得燥热至极,人在外面像奄奄一息的鱼,被烫得无力呼吸,懒得动弹且烦闷,唯有在空调房内才得以存活。一次罕见的假期里,我在一轮复习的书堆中翻到这样一段话:“所有脊椎动物的胚胎在其发育的早期都有这样一个阶段:有一条相当大的尾,有鳃裂,脑子很小。成年鱼仍保留了鳃,而在其他脊椎动物的成体中,鳃消失了。”我沉思良久,突然产生了一个很蠢的问题:动物们为何会选择到环境更恶劣的岸上生存呢?我把这个问题发给罗,可很久他都没回我,我有些失落。
晚上我去赴一场宴会。在酒店大厅里,我看着那些水箱中的鱼,有的条纹丰富,有的色彩鲜艳,有的纤细,有的粗野。它们一个劲儿地吸着不断灌入的氧气,在逼仄的水箱里游动;它们专注于当下的饵料,又将陷入七秒一周期的健忘。我忽然有些难过,觉得人们期望的具象虽然不该是像鲲鹏、黑马那样富有纯粹野性力量的事物,但也不该只是一条搁浅的鱼。那晚的饭很没味道,我想起了和罗吃饭的日子。
夜晚,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又成了一条鱼,困在一潭死水里。绝望之际,我突然发现旁边出现了一个小巧白亮的钩子。我咬住它,它便轻盈地将我提起,我跃出水面,落到罗温热的掌心里。我激动地淌下一滴泪,泪流成一片海,随后,罗把我放生到大海中,他也和我一起成为鱼,永不止息地畅游。
一缕微光钻入眼缝,我缓缓醒来,天已大亮,而我边上的手机收到了罗的回复:
“人们的追求不止于呼吸。”
大考的前一周,我发烧至三十八摄氏度,浑身发冷。起初我不以为意,披了三件外套继续复习。我记得当时在看《红楼梦》的情节概要,尽管是概要,却也引人入胜。当我看到末章写着“全书完”时,我撑不住了,感觉身体酸痛得每一根神经都仿佛要断掉。于是我不得不回家。在穿过走廊,路过罗的班级时,我瞥了一眼,看到他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正专心致志地写着什么。
“对白你想好了吗?”我想起罗上周对我说的话,到现在都还欠他一个答复。对白指的是他给我分配的任务,如今我是他小说的副编。我们正为一个情节的对白发愁。主角在时空乱流中被未来的自己搭救,而我们需要想出未来的自己会对主角说些什么。我看着罗,他拿起紧握的笔,左手的两根手指慢慢摩挲下巴,双眼微眯,流露出一种郑重的神色沉思着。我抿抿唇,打算走之前和他好好聊聊,但因病痛,同时也不想打扰他,作罢。下课铃响了,出乎意料,罗放下笔,轻快地拿起旁边的球拍和同学出去打球,留下那空荡荡的座位,让我恍惚觉得这前后的一切都在一场梦里。
我也该走了,我对自己说。
坐在摇晃的公交车上,只见黏稠的夜包裹了窗外的一切。车上的冷气吹得我脸更加发烫,我本就不适,加上容易晕车,顿时想吐,索性闭上双眼。一些杂乱的记忆有意无意地混进我的思绪:我对罗说我经常做梦,罗说梦是个好东西,很多人想做都做不了。想来梦是浪漫的产物,它的确值得被撰写或铭记,如海一般引发人无尽的遐想,退潮后又留下深深的回味与思考,在干涸的结尾使人于怅然中拾掇感伤与珍视的事物,仿若宝玉与贾政在大雪中的诀别,我和罗将天各一方——那是既定的事实。
好像人总有这样一个阒寂的时刻,为思索与发掘留有扩容的余地,或是一个场景,或是一场滂沱大雨,或是皑皑白雪,总之,一切都会归于平静。一段旋律萦绕在我的脑海里,这是罗向我推荐的游戏背景音乐。当玩家操控角色站在废墟场景中时,音乐就会响起,其中一线邈远的女声会把思绪拉过久远的时空,领人觅见一些震撼的哲理。我觅见无数的水域,发觉一种被迫的苦衷,也有一种置身汪洋的行进自如。我隐隐看见罗在垂钓,在打球,在写作,隐隐听见水潺潺的流动声,我想起了罗笔下的主角。在罗的故事里,他出身平凡,为了不向邪恶势力妥协而一路披荆斩棘,成为受迫害者们的领袖,最后却因不敌邪恶势力的首领而被打入轮回,饱受折磨。现在他企图在与前世的问答中找到突破口,却又陷入时空乱流。
“你不觉得这个主角太累了吗?”我曾对罗说。罗说这毕竟是故事,要有吸引力。我突然觉得主角和反派都很可怜,失去了圆形人物应有的深刻。主角一定要成为英雄拯救所有人吗?反派一定要恶到极致被赶尽杀绝吗?或者说,故事一定要这么编才有人看吗?我忽然想到这个对白应该怎么开头了,接着,好像有一股强悍的水流把我卷入旋涡,带到主角面前。
“对白你想好了吗?”
“嗯,我想好了。”
“啪——”我又断了球,罗只是笑笑。
我们打得大汗淋漓,在边上坐下喝水。我们迈过了人生关键的一关,又即将奔赴下一站。
这是我和罗最后一次打球。
我说:“罗,你以后想做什么?”
我以为他会说作家之类的,但不是。他说自己要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什么都可以,再在那个基础上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当我问他为何不把理想作为工作时,他却说当理想变成工作后,就不再是理想了。
“做自己想做的事。”我在告别时说。他还是笑着点头,转身离去。这句话也是那个对白的开头,当晚他就决定采纳。
“你知道吗?其实主角的某一特点是以你为原型设计的。”那晚他对我说。我很惊讶,又很感动,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会抽空帮他整理那本小说的情节,和他讨论故事的发展,直至时间冲淡痕迹,留下曾经的对白。
如果可以,我想回到我们相遇之初,去问问罗,如何掌握文章笔法与写作技巧,是什么支撑他写了九年的书并广泛涉猎,以及他在现实中进行选择的坦然与轻逸从何而来。罗似乎真的被赋予了一条鱼应有的鳃与鳍,呼吸自如,灵动矫健,可以不逡巡于任何一片水域。他的行进不是为了超越、征服或是成为迢迢的领先者,而是用来潜跃与遨游,成为一条真正的鱼。
我面向大海,闭上眼。在寂静里,海水的声音被无限放大。我开始幻想罗的身影,罗出现在海边,随着哗哗的水声从沙滩那边蹚过来,向我招手,相视而笑,随后向海里纵身一跃,变作一条鱼。他轻盈地晃动鱼尾,转眼消失在浪花里,而水声清晰可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