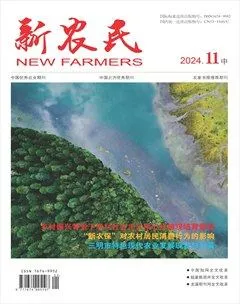“新农保”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
摘要:我国老龄化加速叠加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新农保是我国政府帮助农村居民应对不确定性的重要途径。本文采用2013、2015与2018年三期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微观数据,通过模糊断点回归方法,从不同贫困脆弱水平的异质性群体出发,识别新农保养老金对农村中老年人消费水平与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2013年,新农保正向效应显著,尤其体现为对非贫困脆弱组总消费与享受型消费的促进;而在2015年与2018年则体现为对贫困脆弱组总消费水平的负向影响,且存在对基础型与享受型消费的挤出。
关键词: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消费;贫困脆弱性
学界普遍认为,在充满风险且高度不确定性环境中,贫困是一种动态状态。自1976年Sen提出可行能力理论以来,学界已将贫困从单纯的收入低下扩展到了对个体能力的剥夺,并提出了脆弱性概念,Sen[1]将脆弱性定义为一种在面对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与未来走势带来的冲击时,失败并陷入更糟境遇的可能性。贫困与脆弱性往往相伴相生,长期贫困往往代表着内部的高脆弱性[2]。
在此背景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作为农村居民首次拥有的政府普惠型养老保险,充当了降低农村中老年人养老压力、平滑农村居民面临的潜在风险以及改善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保障角色。考虑农村中老年人的环境风险水平及抗风险能力,我国新农保养老金的给付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消费行为?
1 实证方法设计
1.1 断点回归方法设计
基于新农保自60岁起可以领取养老金的政策规则特点,本文采取断点回归方法进行识别分析。如图1所示,领取养老金的样本比例在60.5岁附近出现跳跃“断点”,符合领取规则,但考虑到实践中,各地实际支付时间不同,该“断点”并非精准地出现在
60岁,因此,本文选用模糊断点回归,以年龄为60.5岁为断点(本文亦以60岁为断点进行了回归估计,结果基本相同)。
1.2 数据选取与处理
本文使用北京大学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仅保留只参加了新农保的45岁及以上农村样本,最终在2013年、2015年与2018年的样本中分别得到4 006个、4 696个与7 355个有效观测样本个体。
1.3 变量选取
1.3.1 被解释变量(结果变量)
分别为样本个体所在家户的人均总消费支出水平以及不同层级的人均消费支出水平,取对数平滑处理。(1)人均总消费支出:加总CHARLS提供的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及日用品、医疗保健、文教娱乐及其他消费性支出后除以家户规模。(2)不同层级的人均消费支出参考王建英等的分类方式[3],将居民家庭人均消费分为基础型、发展型和享受型三个层次。
1.3.2 自变量(处理变量)
是否领取新农保养老金。
1.3.3 驱动变量
年龄。本文定义年龄精确到月份,将“年龄~60.5”作为驱动变量,即形成0~1工具变量。
1.3.4 协变量
(1)性别:男性为1,女性为0;(2)健康水平:依据是否存在日常活动能力(ADL/IADL)障碍判断,无障碍的赋值为1,存在障碍的赋值0,ADL与IADL分别代表“日常生活能力”与“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因此,根据CHARLS提供的数据,本文定义下“存在障碍”的标准为完全无法完成某一日常动作,或完成某一日常工作存在障碍且需要他人协助;存在障碍但可以自己完成的视作“无障碍”。(3)教育程度:根据最高教育水平定义,初中及初中以下的定义为0,高中及以上定义为1。(4)已婚且同居个体赋值1,其他状态赋值0。
1.4 贫困脆弱性估计方法
当前,预期的贫困脆弱性(VEP)是当前学界主要采取的测度方法。该指标基于对未来变化的估计,预测了家庭或个人在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该方法将个体在未来t+1期的家庭人均支出水平落至选定贫困线之下的概率作为t期的贫困脆弱性,若高于“脆弱线”,则是“脆弱”的。
为定义“贫困”,本文分别选取“相对贫困线”与“绝对贫困线”:相对贫困线为居民人均支出中位数的50%;绝对贫困线参考《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19)》发布的2018年现行农村贫困标准,即每人每年支出2 995元,并根据各期不变价指数换算。
为定义“脆弱”,本文选取概率50%为脆弱线。
2 实证结果
2.1 整体断点回归结果
样本整体的模糊断点回归的二阶段识别结果如表1所示。
首先,2013年调查开展时,新农保政策全面铺开不到2年,对消费呈现促进效应,但仅对2013年人均总消费的影响在10%统计水平上显著。其次,就基础型和发展型消费而言,新农保在2013—2018年的样本中均未形成显著影响.最后,在新农保政策全面落地较久的2015年与2018年,领取新农保养老金的个体表现出享受型消费在10%与0.182的水平上显著减少的特征。
就全样本实证结果而言,新农保作为全国性的农村公共物品,当前阶段的养老金给付水平与保障能力有限,带来的预期养老收入也无法满足当前及未来的农村居民养老需求,更难以平滑农村居民60岁后的预期收入风险与劳动能力下滑风险。但是,考虑到贫困脆弱性这一异质性因素的存在,还需要进一步的分类讨论,才能得出更具针对性的研究结论。
2.2 异质性研究结果
通过表格进一步进行了异质性讨论(见表2)。
首先,总消费水平而言,贫困脆弱组在家庭人均总消费指标上受新农保养老金的正向影响不显著,且2015年与2018年的绝对贫困脆弱样本在10%的水平上受到养老金给付的负向影响。这说明,对于绝对贫困线标准下贫困脆弱的这部分个体,由于抗风险能力过于脆弱,新农保养老金难以改善他们的处境。
其次,分年度来看,显著的新农保政策效应主要出现在2015年与2018年样本中,而在2013年样本中,仅有绝对贫困线标准下的非贫困脆弱组受到人均总消费与享受型消费的正向促进作用;同时,2015年与2018年的识别结果为显著负向效应,新农保养老金反而对高贫困脆弱性居民的总消费、基础型消费与享受型消费形成了挤出。
最后,组间对比,新农保养老金对享受型消费的抑制效应在相对贫困线标准下的非贫困脆弱群体的中并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高标准下的非脆弱群体自身对新农保养老金的依赖度偏低,处境也不会因为养老金的给付发生显著变化。
2.3 结果与讨论
就实证结果而言,新农保养老金对于农村老年个体的消费行为影响整体显著性不强,可能源自以下原因:
第一,新农保现行缴费比例与替代率偏低,收入效应有限。参考《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新农保每月养老金领取额度计算基本公式为: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139,其中,基础养老金由国家补贴,最低给付标准为55元/月,但地方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适当提升,参考各地最新新农保实施办法,大部分地区的基础养老金标准在85~155元/月不等;个人账户为参保者一生缴纳的保费总额+利息。根据有关数据,当前,200元/年的缴费档次是最多参保人的选择,因此,以完成最低缴费年限15年的情况为例,年利率取4%,在达到60岁后,参保者每月领取额度仅115~185元,仅占2020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0.6%~1.0%;而最高6 000元档位的替代率也仅为5.7%~6.1%,
第二,新农保养老金额度在地区维度与档位维度上不匹配,预期效应有限。地区维度上,由于起步较晚,新农保养老金至今尚未实现省级统筹,因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基本养老金差异较大,北京与上海市政府给付部分早在2018年已经上调至超700元,其他地区则在100~200元水平。档位维度上,个人账户方面,缓慢下调的存款利率难以补齐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差异。基础养老金方面,由于大部分地方政府给付部分为不随缴费档位变化的固定值,故200元/年档位最短仅需约1个月即可收回缴费阶段的一年“成本”,而6 000元/年档位至少需9个月。结构化设计呈现“累退”。
3 政策建议
第一,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动态优化养老金计算公式。一方面,进一步优化个人缴费档位,降低个人缴费负担,地方政府可提供补贴;另一方面,政府给付部分应适当随缴费档位的提升而成比例或超比例上浮,且每年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进行适当评估调整最低给付基数。
第二,加强新农保政策宣传力度与缴费阶段的讲解辅导。受限于农村受教育水平与新农保实施时间过短,潜在参保人对养老社会保险功能与运作原理的认识存在偏差,影响档位选择的合理性与预期形成的有效性,不利于政策效应发挥。因此,应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扩大保障范围、加深保障渗透;同时,为缴费群众提供讲解咨询服务,帮助参保人选取承受范围内最合理的参保档位,最大化参保人收益。
第三,构建以新农保为中心的多维农村养老体系。新农保养老金的低给付水平对农村中老年人的收入水平保障与预期支撑作用均不理想,导致政策设计效能难以充分发挥;同时,长期老龄化趋势下,新农保更加难以支持。因此,应充分利用现有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资源,加强新农保与新农合、低保、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等的衔接与组合,以组合拳模式分担农村中老年人在多维养老需求上的压力。
参考文献
[1] Sen A K .Capability and Well-Being[J].Quality of Life,1991:30-54.
[2] 韩峥.脆弱性与农村贫困[J].农业经济问题,2004(10):5.
[3] 王建英,何冰,毕洁颖.新农保对贫困脆弱农户消费的影响[J].消费经济,2021,37(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