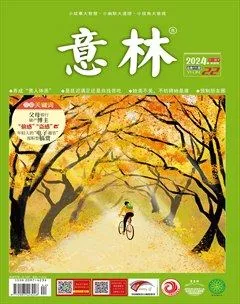面羊
我老家在冀南太行山下,翻过嶂石岩便是山西。逢年过节,到山西那边看姥姥,拜亲戚,总是稀罕她们做的花馍。
做花馍,在我看来,是很浪漫的一种活计。
我的姥姥姨姨妗妗们,一边做着花馍,一边谈论着家长里短的高兴事、稀奇事,悠然,放松,笑语盈堂。然而,她们手下却轻拢慢捻抹复挑,搓,团,擀,剪,切,一压一按,一捏一卷,一扎一挑,盘枣点豆,插面花儿。旁观者眼花缭乱之际,一个个活物生生从手下蹦出来:跳起来的兔、憨威威的虎、绵善善的羊、活溜溜的鱼;狮子、小猪、小鸡、小狗……每个物象,都被施之于智慧,注之于情感。饧好上锅,急火猛蒸,等出锅来,看吧,一个个白白胖胖,鲜嫩灵活。
稍晾一下,点施花红,装饰渲染。素朴平常的日子,忽然间,开了花儿,荡漾出一波波繁华热烈的味道。
山西山环水绕,盛产玉米和小麦,号称是中国的面食之根。这个省份,东到娘子关,西到黄河边,南到风陵渡,北到雁门关,每个家庭的主妇,皆以做面食为擅长。我姥姥说,往常年,是玉米面;如今,都是麦面了。麦面,没有怡甜快辣的味,没有繁华绮丽的色,只有温馨平淡、从容踏实的质;在山西女人的巧手创作之下,奇异孤绝的形,会一点点被塑造出来,这就使普普通通的馍,带上了一种憨朴天真的雅拙之美。

山西的一位文友告诉我,山西的花馍,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了。2000年魅力不减,其真实活力,当是来源于民间那种生动活泼的想象力吧。
作为母亲的长女,姥姥的第一个外孙女,我享受到了姥姥家送“面羊”的礼遇。第一次,接受“面羊”,是在十二晌,也就是出生十一天的时候。想必那时,我尚是襁褓中一个双眼不睁、混沌未开的小孩芽芽,除了啼哭、吃奶,余事一概不知。因此,姥姥家全家出动,为我隆重送羊的热闹,我是无缘见到的。此后,在一年一度、年年送“羊”的礼仪中,我一节节长高长大。
民间认为,孩子到12岁,灵魂长全了,也便成人了;于是在这一年,送羊的仪式,来个高潮兼华美的落幕,叫作圆羊。
圆羊,让一个孩子感觉到在这个世界的存在感;那隆重喧哗的场面,饱含亲人多么厚重的一种恩宠啊!
那年,姥姥为我蒸的面羊,出奇地大,光羊头就有二三斤,羊身近2尺长。它神态安详地蜷卧在高粱秆儿篦子上,椭圆的羊头,用梳子梳出了顺溜的羊毛线条,搓面为条,安成犄角;细短面条,安成眉毛;黑豆做眼,麦粒点出嘴唇;拿锥子压成了胡须。
面羊脖子上的红绒绳儿,穿了铜钱,是给“羊主”的,我自然当仁不让地解下来,挂在了自己脖子上。
面羊背上趴着的12只小羊,几厘米大小,玲珑,可爱;我多想一口一个,把它们吞下肚去啊。可是不许,连同陪着小羊的十二生肖面蒸,也不许;要挂起来的,一直挂一年。
我记得那一年,我时常到挂小羊的帐子角,踮起脚尖儿,去摸它们,直到摸出了一层灰黑的釉儿,像包浆。
最后,那些萌萌的面蒸,都被种到地里去了。
那只大面羊,爹吃头,娘吃脚,奶奶吃个羊尾巴。一个面羊,吃了好几天;面羊吃完,我的12岁生日热潮,就渐渐平息。
若干年后,我又回想起我的“面羊”,不免有好多个疑问。我问山西文友,为什么会是“羊”?他答我,山西人喜欢羊,尊敬羊。炎帝在山西尝百草,救百姓,是让羊先尝的。羊吃了没事,才给人吃。
哦,明白了,这面羊,实际寄托一种民间情感,有一重感恩和爱戴的厚意在其中。送孩子面羊,自然就饱含将这一美好情感传承下去的愿望。
民间饮食,总有生死契阔的深情;面羊,出于俗,脱于俗,亦是这样一种多情的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