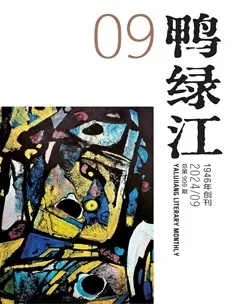杨大群:给后人留点东西
2019年7月1日早晨,我在微信朋友圈里发现军旅诗人胡世宗发了一条消息:军旅作家杨大群辞世,享年93岁。
惊闻噩耗,内心隐隐作痛,更觉得十分遗憾。就在十多天前,我还问胡世宗叔叔是否有杨大群伯伯的电话。他们都是我父亲的老朋友,论辈分是我的叔叔伯伯,其实都是我的忘年交。由于搬家的原因,杨老的电话变了,所以联系不上,冥冥中我感觉杨老是想和我聊一聊,却没能见最后一面,怎么能不遗憾!
父亲在辽宁省作家协会工作,年轻时就与杨大群交情颇深,我猜测“交情颇深”的原因该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当年杨大群在空军大院住,我家住在今张学良旧居,两地距离不算远,骑车往来仅需要十多分钟。我母亲出身大户人家,以热情好客著称,家里经常大摆宴席。尽管那时物质条件艰苦,父母亲却总是竭尽所能拿出家里全部最好的。母亲张罗美食,父亲就和朋友们聊天交流观点和思想。父亲是比较开放的,不管家里来了谁,我都可以上桌,而且可以插话,那时一般家是做不到的。因为父亲的民主,我从记事起就经常享受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盛宴。
正因为如此,我对父辈们聊天的内容也逐渐产生了兴趣。那时候我不懂文学,就是觉得喜欢听杨伯伯讲话,比和小朋友玩游戏还有意思。杨老当时正在酝酿创作《关东演义》《伪满州国演义》《义勇军演义》,都是以东北民国那段历史为题材的小说。主要是反映东北大地民国时期发生的故事。杨老熟悉家乡,熟悉家乡的人们,对家乡的人民充满了感情。杨大群讲话和他的作品一样鲜活生动,我数次听他讲过:“我出生在东北,当过十四年的亡国奴,我最真切的感受就是,一个国家如果不强大,人民就会受欺负,民族就有灭亡的危险。为了写好这部小说,我对伪满洲国历史研究了整整四十年,我有责任让后人知道家乡人民经历过什么样的苦难。”
为了这样的目的,杨大群增添了一个独特的爱好——收集市面上能见到的民国时代的老物件。这些老物件包括民国时期的皇历、老旧报纸和民间生活用品。几十年来,他坚持日出而作,每逢周末便前往旧货市场或者地摊儿,去淘宝,去寻觅,风雨无阻。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了解那个时期的生活,对所描写的时代使用的物品有真实的感受。当时人们普遍生活贫困,隔三岔五变卖些用不上的旧物。特别是在“文革”时期,很多人家里不敢存放“四旧”,变卖的老物件更多。杨大群深知机会难得,他趁着这段时间,淘到了海量的宝贝。
这些老物件儿承载着过去的记忆,也是杨大群的珍贵收获。这些宝贝在外人看来就是一些破瓶子烂罐子和旧报纸旧书籍,在杨大群的眼里价值可就大了。他的追求并非止于收藏,而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些物品,还原那个时代的真实面貌。他深入研究每一本皇历、每一张老旧报纸、每一个民间生活用品,试图从中寻找出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信仰和价值观。这些宝贵的物品,不仅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更是杨大群对于过去的致敬和珍视。
老物件提供了鲜活的记忆、翔实的历史,他不辞辛苦淘来,不辞辛苦研究,又不辞辛苦写到人物、情节中。杨大群的作品既生动又接地气,不明就里的人n/iyGev1G5RQP7z9K2RM7mJgTt6M6b8w6lsjfCqXaAA=们经常当作历史真实引用,和这些老物件有很大的关系。他深厚的文学功底加上对历史的热爱,使他的作品如同时光隧道,将读者带入了民国时代的繁华与沧桑。通过他的笔触,我们得以领略那个时代的生活细节,感受那些曾经被遗忘的岁月。
杨大群收集了海量资料,旧报纸按年代编排有序,老皇历每年一本,花花绿绿的香烟包装纸、旧上海广告彩页在玻璃板下面压着。他的军人身份让他的书躲过许多劫难,后来他成了辽宁作家中个人藏书量最多的人,有三万多册。建在他的故乡新民的“军旅作家杨大群馆”大门上有对联云:“看书写书收藏书书痴书疯,乡情友情关东情情深情重。”
与杨大群一样,我父亲对东北民国史有研究,后来又辛苦积攒,经过几十年日积月累,也曾有上万册藏书,家里仅《文史资料》就整整齐齐码了一面墙。杨老与我父亲聊的多是此类话题,特别是民俗方面的,比如1918年沈阳流行的是老刀牌香烟还是炮台牌香烟等等。两人讲到有分歧的地方,常常是父亲在他的《文史资料》墙上抽出其中一本,指给杨大群看证据,杨大群赶紧拿出他的小本本记下来。他的口袋里总是装着一个本子,他的本子上记录的内容我以前就看过:通常是记录着人们的语言,或者是描写笔记,凡观察到的生活都把它记下来。本上写得最多的就是典故和风土民情。上面密密麻麻的小字,常常看得我眼花缭乱。杨大群自己视若珍宝,小本本从不离身。我父亲等到杨大群在小本本上面记好了,通常就调侃他“本本主义”,两个老朋友一起开怀大笑,这是他们之间的互相调侃和彼此欣赏。60多年,他的小本子满满记了300多本,累计3000余万字。
杨大群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这些小本本上的内容后来变成了精彩的作品:他记录人们的生活、家乡的历史,他的《爱要和爱给》《龙的叫声》《小鼓手》等作品被收入中小学课本和辅导教材;《小矿工》被译成11种文字,发行几十个国家;他创作的30多部长篇小说手稿和2000多万字,成为东北地区名副其实的高产作家。
杨大群的作品中,演义占了很大比重。不过,虽然名为“演义”,却并非胡编乱造,更不是当今流行的各种“戏说历史”的作品。杨大群说,写小说是严肃的事,带着爱国心和责任心去写,写的书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在杨大群的书房中,收藏着3万多本藏书,其中仅仅有关伪满洲国、东北抗战的史料就达七八千种。此外让人注意的还有他多年来写的300多本笔记。杨大群并不写日记,只写笔记。他的笔记分为三种:语言笔记、描写笔记、长篇小说结构笔记。其中仅语言笔记就记了200多本。
让杨大群声名鹊起的是《关东演义》,全书近70万字,初版约30万册,从一般长篇小说的销售情况来看,这部书的印数是很大的。“印数定江山”,由此可见,读者对这本传奇式的历史小说是十分欢迎的。
读者喜欢演义,常常是因为它包含着许多神异、奇特而有趣的故事,情节曲折离奇而引人入胜的缘故。《关东演义》首先抓住了这个特点。它叙写了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九一八事变前夕我国东北的风云变幻,描述了巨流城草头屯闯关东的李、沈、于三家的离合悲欢。整篇小说波澜壮阔,条线交织,写出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悲欢,大人物的无奈,不同的抉择,不同的命运。小人物一直反抗,从未屈服。《草头屯恩仇》《东北王之家》《关东城播火》《辽河套枪声》《九一八风云》《义勇军崛起》《傀儡帝登基》《黑龙江怒吼》《长白山涛声》《八一五光复》是全套十个部分的单册书名,各自独立,却又连贯顺畅,牢牢吸引读者从头到尾阅读,一部也不能落下。
《关东演义》人物有血有肉,语言经得起反复咀嚼,关东风情跃然纸上,是那个时代才有的好书。杨大群主张,要写就坐下来好好地写,不写就出去转,远近都走走。全国大陆除西藏外,他几乎都跑遍了。无论是蚊虫叮咬的野外,还是繁华热闹的都市;无论是寻常的百姓民宅,还是名流要人的深宅大院,他都一视同仁,并且前去一探究竟。无论是三教九流,还是达官贵人,他都去接触。书中有一段写刘少奇来东北播种革命火种,为了弄清历史事实,杨大群竟然赶到中南海想采访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当时杨大群并未获准与刘少奇见面,后来经人介绍,王光美读了书稿《关东演义》中的第二部《关东城播火》,给杨大群提了中肯的意见。
杨老最大的本领是擅长编故事、构思情节。他创作的长篇小说《关东演义》中的许多引人入胜、活灵活现的故事情节其实都是他编出来的,后来被一些影视作品当成史实资料翻拍,足见他的创作是多么符合历史人物特征,多么出神入化,竟使后人以假当真。
半个世纪前一个冬天的下午,我正在大院里玩耍,杨大群骑着他的二八大踹自行车来找我父亲。看见我就冲我招手,我知道,大群先生一来,肯定有好故事听,母亲还会想方设法变出好吃的,所以我就欢蹦乱跳引着杨大群回到了家里。那时作协家属已经被迫离开张学良旧居,我家搬进小南天主教堂,居住环境窄小逼仄。杨大群进门后非常兴奋,说刚写完八千字。不等父亲接茬,我先惊掉了下巴,就问:“你每天都能写八千字吗?”他回答说基本上能做到,风雨无阻。天哪,怪不得他那么高产,简直是神人,要知道那时写作没有电脑,全靠一支笔在稿纸上爬格子,真正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写”,每天八千字,一般人抄都抄不完,我对杨老的勤奋佩服得五体投地。正在兴头上的他又给我讲了一段路上遇见警察的事,我至今记忆犹新:来我家的路上,他一边骑车一边考虑小说情节,在一个十字路口被交警拦住。小警察厉声训斥道:“那位老同志,红灯大家都停了,就你特殊?你赶什么赶?敢死队啊?”杨大群抬头一看,原来是自己闯了红灯。他赶忙停了下来,一边掏出小本子记下警察生气时的语言,一边在心里想:警察把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为称为“敢死队”,究竟用“敢于”的“敢”还是用“赶紧”的“赶”?还没等杨大群想明白,警察又冲他喊道:“绿灯都亮两遍了你还不过?没等到你喜欢的颜色吗?你还写在小本上,你记变天账呢?”杨大群挨了抢白,不但不生气,还感谢警察,感谢小警察的语言很生动,让他的小本本上又增添了新内容。小警察被杨大群感谢得啼笑皆非,一腔怒火丢到了爪哇国。听杨大群讲话比读他的书还有意思,他眉飞色舞,比比画画,让听众身临其境,永志难忘。
除了写作上才能了得,我父亲尊重杨大群更是因为他人品高贵,“文革”期间从不整人害人,而是肯拿出宝贵的时间乐于助人。当年省里有个老领导叫张铁军,刚恢复工作时,是无职无权走资派,别人避之不及。他有个儿子张大军,擅长创作,当时创办正在招兵买马,本想找我父亲看看能否安排在辽宁省创作办公室发挥所长,但由于张大军当时在齐齐哈尔一家工厂工作,两省跨区域,受编制户籍等限制,创办无法接收。于是父亲就和杨大群说,大军写了不少东西,文笔相当不错,是个好苗子,地方受限无法安排,有点儿可惜。杨大群立即说部队有招兵名额,创作组可以特招。杨老出手相帮,奖掖后生,张大军顺利调进了沈空创作组,后来成了大笔杆子,著述颇丰。张大军著有长篇小说《空幻》《少女失足之后》,影视剧本集《从俄罗斯飞回来的鹰》,电影文学剧本《铺满浪花的路》,另发表《首席法官》等中短篇小说100余篇。电视剧剧本《首席法官》获全国首届优秀电视剧飞天奖三等奖,专题片撰稿《生命中有一段当兵的历史》(合作)获空军一等奖,电视纪录片《忠诚的道路》获国家级金剑特等奖,另有评论文章获总政治部文化部奖。
杨大群原名叫杨建生。解放战争初期,他在东北行政学院读书,写了个稿子,想用笔名发表。那时学院正在组织学习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给自己取的笔名就是大群,鼓励自己到广大群众中去。
1950年,杨大群加入东北防空军政治部宣传队,成为第一批入朝参战防空军高射炮部队的战地记者。初上战场的杨大群十分不适应。我还记得他回忆说,实实在在说就是害怕,怕什么呢?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敌机“拉粑粑”。敌机“拉粑粑”,就是指美军飞机投炸弹。那时候,战地新闻稿件要通过志愿军司令部才能转到国内。每次去司令部送稿,杨大群总是万分小心绕道走,很费时间。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的机要秘书“刘大个”负责接收战地新闻稿件,见杨大群每次送稿件都很慢,询问原因后,刘大个鼓励杨大群说:“你站着倒下了,还‘咣当’响一声,如果趴着死了,死也死得窝囊。”杨大群见刘秘书不但身材伟岸,而且英气逼人,不禁被他的这种豪气深深感染,因此与刘秘书结为知己。让杨大群想不到的是,这位刘秘书正是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
毛岸英的豪气万丈让杨大群抛弃了恐惧心理,从此他以作家的敏锐,积极捕捉战地新闻。他写的一篇《高射炮长“腿”》,说的是志愿军为解决高炮射程不够的问题,官兵集体齐上阵,硬是将大炮抬到山顶上,使得高射炮如同长了“腿”。解决了射程问题以后的高射炮威力大振,接连打下美军飞机2架、击伤1架。美军大吃一惊,以为“共产党有了新防空武器”。美军电台也跟着报道:“中国发明了新武器。”从此美军飞机很长一段时间不敢轻易起飞,要小心翼翼观察情况。
毛岸英看到这篇新闻稿后,很是欣赏,就加急将稿件送给彭德怀。几天后,毛岸英告诉杨大群:“你的那篇稿子彭老总看了,他很高兴,称赞说‘这是战争中战士的伟大创举’。”杨大群在抗美援朝前线整整五年时间,他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撰写了三十万字的战地报道,先后发表在《志愿军报》《人民文学》《人民日报》等报刊上。
战争中,和杨大群结下了深厚友谊的刘秘书——毛岸英永远留在了战场上。缅怀英烈,浩气长存,杨大群创作了长篇传记文学《毛岸英》。我在杨大群家里看到他珍藏的一本上面有毛岸英的妻子刘思齐的签名,书的扉页上是刘思齐写的序:“岸英在朝鲜大地上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四十天,而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两年后的1952年我才知道他去了朝鲜前线,对于他赴朝参战后的生活与战斗我知之甚少,杨大群同志作为曾在朝鲜前线与岸英并肩战斗过的战友,饱含深情写下了这一切……”
杨大群把《毛岸英》一书所得稿费十万元全部捐给新民家乡小学,现在该校命名为岸英小学。许多年以后,毛新宇从朝鲜参加纪念抗美援朝活动回国时,路过沈阳和我提及此事,想拜访《毛岸英》的作者以表达谢意,让我帮助联系杨大群。真是无巧不成书,我立刻促成了两人相聚畅谈。毛新宇毕恭毕敬向《毛岸英》作者杨大群致谢,一老一少两双大手紧紧相握,场面感人至深,让我久久难忘。
杨老还是个与时俱进的人。电脑刚刚开始应用时,他和韶华(辽宁作协另一位老作家)同时学习用电脑打字写作,两位老爷子经常争论谁是作家中最先用电脑创作的。争论的结果是没有结果,两人都认为自己才是第一名。他们谁也不服谁,就像两个老顽童。杨老头脑好体力好,一天能打一万字。正是他这种勤奋努力,才创作了《鹰击长空》《西辽河传》《关东演义》《毛岸英》《伪满州国演义》等多部脍炙人口的作品。他一生创作的作品摞起来真的超过了他的身高,是实实在在的著作等身。
杨老八十大寿那天,我陪同我父亲去他家里看他,本以为他家会高朋满座,大宴宾朋,结果除了我们父子以外,没有其他外人,就连他的儿女也都上班去了不在家。杨老这些年勤于笔耕,几乎不参加社交活动,所以去他家做客的人凤毛麟角。我敲开门后,只见杨老戴着标志性的套袖,这让我想起我年少时到他家就问过他为什么总戴套袖,他跟我解释,长年伏案工作,往往是衣服没坏袖子先磨坏了,为了节省衣服,他一回家就戴上套袖。我不解地问:“你们部队衣服不是免费派发的吗?坏了再申请呗。”杨老一脸严肃地说:“我们不能浪费东西,生活不能太奢侈。”这么多年过去,杨老依然戴着套袖,只不过又加了一个大花围裙。杨老身材高大,体态微胖,大花围裙明显不合身,还有点儿喜剧效果。杨老见我们父子俩疑惑的目光,笑着解释说:“老伴儿病了,我得下厨房做饭伺候她。”我父亲不解地说,你都八十高龄啦,请个阿姨来家里不是更好吗?杨老说不行,我老伴儿说别人做的饭没我做得好吃。说到这里,杨老的表情是fNNQgJ9256Qe6w5Oz/9kfA==“扬扬有得色”,好像只有他本人才配伺候老伴儿。
杨老的老伴儿是个典型的农村家庭妇女,她不懂文学,甚至认不了几个大字,但她自打嫁给杨老就一心朴实地生儿育女,操持家务。我每次去杨老家见到她时,她都是面带淳朴的笑容,点头打个招呼就忙家务去了,在她眼里,杨老的一切都是重要、高大、神圣的,给杨老创造最好的生活条件,让杨老安心从事文学创作,就是天下大事——尽管她完全不懂什么是文学创作。无情的病魔使老伴儿卧床不起了,因为照顾老伴儿,杨老晚年非常辛苦忙碌。杨老曾经被老伴儿照顾得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什么家务活儿也不会做。老伴儿卧床后他开始学习做饭,为了能让老伴儿吃上可口的饭菜,杨老坚持亲自下厨,以老伴儿的口味为唯一执行标准。一日三餐,四季衣裳,二人一生,情深意重。《诗经》里面说的“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杨老是真正做到了。
杨老风趣幽默,不拘小节。有一次他穿着一套新旧明显不同的衣裤去作协创联部,恰巧偶遇诗人晓凡。晓凡敏感睿智,擅长观察生活,尤其是每个人的穿衣戴帽,晓凡立马就发现了杨老衣着穿搭不合适,就半开玩笑地对杨老说:“你这裤子与上衣不搭,应该买条新裤子了。”杨老先是一愣,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从来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老伴儿给啥就穿啥。听晓凡这么一说,他沉思片刻,斩钉截铁地说:“不能换。”晓凡不解地问杨老为什么。杨老说:“如果把裤子换了上衣就显得旧了,还得换上衣。上衣换了衬衫就又不搭了,还得换衬衫,全身都换新的了,老婆又显旧了也得换,这问题就太严重啦,我还没有换老婆的想法,所以裤子就将就着穿吧。”杨老还没说完,在场的人们就哄堂大笑,这段子后来成了作协大院的一个梗。杨老可不是说笑话,他是严肃的,也是认真这么做的。杨大群名满关东,伟岸正直,肯定不乏爱慕者,可他却一生零绯闻,始终如一地爱着妻子一辈子。甚至后来老伴儿故去以后,人们劝他再找个老伴儿照顾生活起居,都被杨老婉言谢绝了。他的心思完全不在这些事情上面。
杨老的时间好像比别人多,其实是他善于节约时间。晚年他除了坚持做饭、创作以外,还画国画,尤以画鹰擅长。杨老88岁那年我去他家拜访,只见老人家戴着一副黄色套袖,系着围裙,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厨师做菜呢,其实这是杨老画画的扮相,因为他手里还拿着毛笔,他怕弄脏了衣服还得洗,就套袖围裙上阵,不必清洗,节约时间。
我看到案头上刚刚画好的一幅雄鹰图,画面上一只雄鹰目光如炬,振羽展翅。杨老说,这幅画送给你父亲吧,他十分郑重地签字盖章后给了我。我那时已经从体制内辞职下海了,杨老问我生意做得怎么样了,我有点“烧包”,就脱口而出说已经衣食无忧,实现财务自由。他说:“既然这样就应该搞点儿文化,在文化产业方面投点儿资也是好的,不枉你出身书香门第。”我被他说得满脸通红,不知如何回答。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尴尬,又笑着说:“我是看着你长大的,你还有文学基础,为什么不写点儿东西呢?我现在就是感觉身体跟不上了,要写的题材很多,还有一个关于解放战争的题材,也是大部头,得100万字,我现在一天顶多两三千字,恐怕是完不成了,遗憾啊!你们多好,年轻,想干啥都有的是时间,还是干点儿文化方面的事,给后人留点儿东西。”
杨老一生始终把人民大众放在心上,他家收藏的一幅“同众在抱”是书法家沈延毅送的,他也确实当得起。杨老一生辛勤笔耕,“给后人留点儿东西”,既是他的座右铭,也激励着晚生后辈不断进步。
用手中的一支笔,杨大群为我们留下了一段段珍贵的历史。他的作品不仅仅是文字的数量惊人,对于历史的正视和传承更是令人折服。通过他的努力,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那个时代的人们,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让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回望那段历史的风华。正是因为有了杨大群这样的作家,历史才得以被书写,然后被传承,最后不会被遗忘。
杨老的作品不仅仅是一本本小说,更是一段段珍贵的历史文献,和他收藏的那些文物一样,历久弥香,历久弥坚。他以敏锐的洞察力、扎实的研究以及饱满的感情将那个时代的场景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通过他的笔触,我们仿佛穿越时空,走进了我们民族的风雨沧桑,那些曾经的峥嵘岁月。
杨大群人已故去,但他的作品还在,永远活着。
作者简介>>>>
陆天,原名陆虹,生于1961年,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政治学研究生毕业。曾在辽宁省文化厅等政府机关及华润雪花啤酒公司等央企工作,系知名企业家。现从事文学及短视频创作。
[责任编辑 胡海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