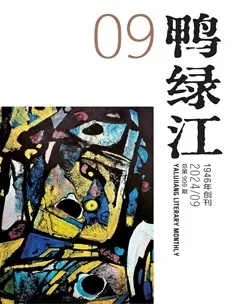醒来明月 醉后清风
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
李建新:
今年3月那次,早兄我们和汪朗、汪朝老师聊天,稍稍涉及酒的话题。早兄说,好像没见到汪先生直接写酒的文章。这么一想,确实。但是他的诗中倒是有不少写酒的,《七十书怀》有句“悠悠七十犹耽酒,唯觉登山步履迟”,《题丁聪画我》中也有“我年七十四,已是日平西。何为尚碌碌,不妨且徐徐。酒边泼墨画,茶后打油诗”。酒是中国传统文人密不可分的伴侣。汪先生更是被人称为“酒仙”,陆文夫回忆他的文章标题就叫《酒仙汪曾祺》。烟、酒这类生活嗜好,也塑造了作家的精神气质。我们这次可以从酒——包括烟这个话题出发,聊汪先生的作品,以及他某些时期的生活状态。酒和烟只是一个道具、一个入口,我们的聊天照例可以是随意的,围绕这个话题展开吧。
杨早:
吴祖光编的《解忧集》里好像就没有收汪曾祺的文章,我印象里他没有特意写过关于酒的散文。就是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出版的那套小书,汪曾祺编的是《知味集》,还有袁鹰编的《清风集》,端木蕻良编的《说画集》,姜德明编的《书香集》,等等。但是汪曾祺的小说里涉及酒的还不少,《安乐居》啊,《七里茶坊》啊,而且写得很细。
李建新:
《多年父子成兄弟》里写道:“我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他喝酒,给我也倒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他一根,我一根。他还总是先给我点上火。我们的这种关系,他人或以为怪。父亲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烟和酒作为可成瘾的嗜好,在某种程度上能让人在精神上抽离现实,有一种暂时摆脱纷杂世事的感觉吧。
汪先生到昆明读大学后,喝酒应该是常事。大学生已经是成年人,那时候是不是管得也不那么严格?他写过不止一次的一个情节,说自己有一回喝醉了,坐在路边,沈从文先生恰好路过,还以为是个难民生病了,“走近看看,是我!他和两个同学把我扶到他住处,灌了好些酽茶,我才醒过来。”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应该也是极少数。他在20世纪40年代写的文章里,有篇短文叫《烟与寂寞》。喝酒也有不少是因为寂寞吧?生活条件的艰苦,工作的不如意,乃至失恋,可能都会去借酒浇愁的。
徐强:
汪曾祺抽烟喝酒都很早。抽烟是受父亲影响,给我的印象,他写到父亲,常伴随抽烟动作,有时整夜吸烟,早起枕上落满烟灰。《花园》记述了他自己刚开始抽烟的场景:“有一年夏天,我已经像个大人了,天气郁闷,心上另外又有一点小事使我睡不着,半夜到园里去。一进门,我就停住了。我看见一个火星。咳嗽一声,招我前去。原来是我的父亲。他也正因为睡不着觉在园中徘徊。他让我抽一支烟(我刚会抽烟),我搬了一张藤椅坐下,我们一直没有说话。那一次,我感觉我跟父亲靠得近极了。”
我觉得,这个动人的场景对汪曾祺具有“成人礼”的性质:一个父亲,对他心爱的儿子不再以“孩子”看待,而是以成人的礼节、以平等的身7V/hTvL0yDQXGHMyTOmQ8PZ+PGj8a/ovg+KTGLOzO5U=份对待,显示了一种极为难得的民主作风,一种毫无家长权威的家庭氛围,这对于汪曾祺此后三观的建立,影响之大可想而知。
杨早:
汪曾祺的生母去世得早。他在文章里说:“我三岁的时候,母亲就故去了。我对她一点印象都没有。”残存的模糊记忆,包括父亲为母亲熬粥,自己随船陪母亲到淮安就医,一直记得船舱里大头菜的气味儿。虽然后来的两位继母对他也不错,祖父母疼爱他,父亲更是宠爱他,但对于一个幼年失去母亲的孩子来说,感情上肯定是有缺失的。汪曾祺的文章里写“多年父子成兄弟”,父子关系非常融洽,也从侧面说明他对特别温暖的一部分记忆的强调和怀念。父亲和还是孩子的“我”分享烟酒的细节,是有象征意义的场景,也有父子彼此慰藉的意味。
《鸡鸭名家》是汪曾祺写于1947年的小说,20世纪80年代又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收入《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我说过,这篇小说的主角看上去是余老五与陆长庚,实际上第一主角是父亲。
在1982年版里,汪曾祺已经大段地去除了父子之间相处的描写,而将更多笔触集中在“鸡鸭名家”上。这种改动,或许与汪曾祺后期对小说“短”的追求有关。在1947年版里,父亲的形象要更丰富、更立体。有一段关于父亲的描写,80年代的修改本删去了,其中包含了对父亲的理解:“他年轻时体格极强,耐得劳苦,凡事都躬亲执役,用的两个长工也很勤勉,农场成绩还不错,试种的水蜜桃虽然只开好看的花,结了桃子还不够送人的,棉花则颇有盈余,颜色丝头都好,可是因为好得超过标准,不合那一路厂家机子用,后来就不再种了。至今政府物产统计表上产棉项下还列有窑庄地方,其实老早已经一朵都没有了。不过父亲一直还怀念那个地方,怀念那一段日子,他那几年身体弄得很好,知道了许多事情,忘记了许多事情,从来没有那么快乐满足过。”
1947年版里还写道:“我自己来了,事前连通知都不通知他!”由此可以看出父子关系的亲密随意,符合后来“多年父子成兄弟”的总结。小说中还写到“运鸡的两口子”,因为车陷进坑里,两位一旁聊天的老人来帮忙,才引出了余、陆二位鸡鸭名家。但这运鸡的两口子并非闲笔,一开始,女的拉车,男的“提了两只分量不大的蒲包在后面踱方步”,还引起了“我”的不平,觉得男的“真岂有此理”,后来车子陷坑了,才知道,一路上尽是坑,男人推车救车的负担更重。这才有了车子“吱吱吜吜地拉过去,走远了”,“我”突然想起的两句《打花鼓》——“恩爱的夫妻槌不离锣”。而在1947年版里,看夫妻拉车时,还有一句“父亲不说甚么,很关心的看他们过去。一直到了快拐弯的地方,我们一相视,心里有同样感动了。”结合下文的“母亲故世之后,父亲觉得很寂寞无聊”,父亲到窑庄务农后“从来没有那么快乐满足过”的描写,这里面,显然有儿子对父母深情的理解。
徐强:
建新兄刚才提到的《烟与寂寞》是汪曾祺1947年的作品,把买烟的过程写得极具仪式感。作者当时在上海致远中学教书,应该具备一些经济条件,至少比在昆明时期要好一些;所以幻想买一种土耳其烟,想寻找一种悠游把玩的乐趣。这篇文章并没有提到任何的“寂寞”,大概是在整体的意义上来“暗传”寂寞吧——把“买烟”这样不起眼的事情小题大做为文章,本身就是寂寞无聊的产物。这透露了当时汪曾祺的生活与心态的一个侧面。
早期作品提到烟很多,或者可以说太多了。《艺术家》开篇:“抽烟的多,少;悠缓,猛烈;可以作为我的灵魂状态的记录。在一个艺术品之前,我常是大口大口的抽,深深的吸进去,浓烟弥满全肺,然后吹灭烛火似的撮着嘴唇吹出来。夹着烟的手指这时也满带表情。抽烟的样子最足以显示体内潜微的变化,最是自己容易发觉的。”这些详尽的描述,可以看出汪曾祺对烟的品味是深入细致的,也同样折射了他的超强的感觉能力,还有生活艺术化的趣味。
李建新:
汪先生是真正地爱酒。有条件喝酒的时候,他写到酒的只言片语,都带着愉悦。他文章里写过年轻时在昆明和好友朱德熙同游遇雨,在莲花池边一条小街的小酒店,“要了一碟猪头肉,半市斤酒”,坐待雨住,四十年后仍忘不了当时的情味,作诗云:“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他后来也曾到朱德熙家自斟自饮。1972年12月致朱德熙信中也有一句,说办公室停电,抽空回了一趟家,“一个人炒了二三十个白果,喝了多半斤黄酒,读了一本妙书。吃着白果,就想起了‘阿要吃糖炒热白果,香是香来糯是糯……’”那种轻松惬意弥漫于平实简单的文字,令人莞尔。
小说《七里茶坊》中,写冬天被派到张家口淘粪的几个农业工人,在车马大店里,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老乔喜欢“白话”自己的见闻,说各种食物,想喝酒而不得,就谈起云南的酒,市酒、玫瑰重升、开远的杂果酒、杨林肥酒……“蒸酒的时候,上面吊着一大块肥肉,肥油一滴一滴地滴在酒里。这酒是碧绿的。”我们谈“饮食书写”那一期,也提到过这个桥段。还有一篇小说《安乐居》,写酒的情节也特别多。里面的酒客老吕、老王、老聂、上海老头、瘸子、白薯大爷,一人一个样儿,气度、声口,都特别有个性,让人过目难忘。汪朗老师说过,安乐居的原型是汪曾祺在蒲黄榆住的时候附近的一个小酒馆,他常去喝酒,也常常细致地观察酒友。
杨早:
《安乐居》里写到一个酒客老聂:“老聂有个小毛病,说话爱眨巴眼。凡是说话爱眨眼的人,脾气都比较急。他喝酒也快,不像老吕一口一口地抿。老聂每次喝一两半酒,多一口也不喝。有人强往他酒碗里倒一点,他拿起酒碗就倒在地下。”简简单单几句白描,非常传神,不禁让人想起《世说新语》写到的“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蹍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
唯有饮者留其名
李建新:
文人爱酒,自古传为佳话者不少。竹林七贤、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等等,留下了太多与酒有关的诗文。饮酒差不多是一种文化现象。想起来一个有意思的事,据台湾学者黄永武先生在《敦煌的唐诗》一书中说,普遍流传的李白《将尽酒》有句“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在敦煌残卷抄本中,这句写作“古来圣贤皆死尽,唯有贤者留其名”。感觉后者更“原生态”,符合李白“洒狗血”(汪曾祺语)的风格。
徐强:
汪曾祺和他的同侪密友,多数深受《世说新语》影响,沾染了较多的魏晋风度和名士做派。这种名士做派往往以烟酒为媒,激发起来。《世说新语》中共出现酒字百多次,其中将近半数出现在《任诞》篇中,说明酒与“任诞”这种品性的关系最为密切。置诸汪曾祺一生的酒事当中,也能验证这一点:他的饮酒、嗜酒、醉酒,最典型地显示出来的就是任诞不羁这一性格侧面。
他回忆他的父亲“少年时节完全是个少爷……春秋佳日常常大醉三天不醒,对于生业完全不经意。”这样的叙事话语让人怀疑脱胎于《世说新语》的“三日仆射”(“周伯仁风德雅重,深达危乱。过江积年,恒大饮酒。尝经三日不醒,时人谓之‘三日仆射’”。)他和朱南铣吃螃蟹喝绍兴酒,两人皆大醉,回不了家,朱德熙把他们两人送到附近小旅馆睡了一夜,这令人想起《世说新语》毕茂世的名言:“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他崇敬闻一多,每每提及他那句著名的课前“引子”:“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原也来自《世说新语》。他的家人经常提及晚年汪曾祺常常和夫人斗智斗勇、躲到小酒馆里贪杯饮酒的情形,直让人想起刘伶为喝酒与夫人斗法的经典场景和他煞有介事地跪地祷祝的“歪理”:“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至于他笔下的人物,嗜酒者也不少,往往同时也是任诞、洒脱、狂狷之辈,汪曾祺写到这些人的饮兴,往往笔端流露欣赏之意,大有张季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之慨。他题五粮液的联语“任你读透四库书,不如且饮五粮液”,几乎就是张季鹰那句名言的翻版。
李建新:
现当代文人、作家中,好饮者也不少。我记得多年前读叶圣陶先生的《日记三抄》,有不少关于喝酒的记录。有一个趣闻,说是 20世纪30年代,叶圣陶在上海为开明书店主编《中学生》杂志,开明书店创办人章锡琛和胞弟章锡珊以及王伯祥、范洗人等成立了一个文友酒会,叶圣陶被推举为会长,规定一次能喝5斤以上黄酒者才能入会。书画家钱君匋也很想入会,但他的酒量只有3斤半,便请会员丰子恺通融。叶圣陶说可以先作为预备会员,并鼓励钱君匋:“要锻炼酒量,早日把‘预备’两字拿掉!”
杨早:
台静农40年代写过一篇短文《谈酒》,写到青岛的苦老酒、济南的兰陵酒,还有在四川白沙喝过的杂酒,又考证杂酒也许是古籍中记载的咂酒,出自苗人土酿。这种小考证式的随笔,汪曾祺也写过不少,如果他来一篇《谈酒》,兼述见闻经历,应该也很有可读性。
汪朗老师说汪曾祺避讳谈酒,好像有点儿把嗜酒当成缺点似的。他没写,我们也少了读妙文的乐趣。
徐强:
汪曾祺的同父异母弟弟海珊晚婚,汪曾祺赠以一联:“金罂蜜贮封缸酒,玉树双开迟桂花”,以“封缸酒”对“迟桂花”,雅致而贴切,因为海珊也嗜酒。后来,又曾援引黄庭坚《西江月》句略改为联题赠海珊:“断送一生唯有,清除万虑无过”。黄庭坚句,本自韩愈的诗句“断送一生惟有酒,寻思百计不如闲”(《远兴》),宋代黄庭坚有词句“断送一生惟有,破除万事无过”(《西江月》),或为该联所本。
为海珊撰题联语相赠,含蓄地总结了酒之于人的功用后果,可谓此道中人的“知言”,既有同好的理解之意,也有手足身份的告诫之辞。这两联,可称嘉话。
李建新:
汪曾祺的人生经历中,有喝闷酒的失意时刻,比如“文革”后被“挂”起来,被无休无止地审查,他曾喝多了酒表示要剁指明志。后来名声越来越大,有更多的欢乐时刻。我记得作家、出版人杨葵写的一则轶事:“1991年春,云南文联组织笔会,邀请汪曾祺等人体验傣族泼水节。从版纳回省城后,文联某作家邀汪赴家宴,知他嗜酒,可又拿不准他到底喜欢喝哪种酒,于是洋酒、黄酒、白酒俱有准备。汪道:既然准备了,就都喝点儿。很快酒至酣处,主人趁机向汪求墨宝。汪慨然允诺,要写云南之行自创的七言绝句一首。无奈人已喝醉,蒙蒙眬眬写完前两句,裁好的那张宣纸已被写满。主人提出更换纸张重写,汪醉已深,强打精神道:不必,后两句写小字好了。于是,后两句诗的字形,呈阶梯状直缩至小楷。好歹写完,汪掷笔对主人道:‘罕见之作,汝当珍藏。’”
酒酣胸胆尚开张
徐强:
汪曾祺乐饮,观其一生,似乎像阮籍那样“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的时候少。更多的时候,是如王卫军所言的情况:“酒正自引人著胜地。”他耽于享受的是那种迷离恍惚、忘却营营的生命体验,客观上说,是带他进入一种艺术创作上的迷狂状态,对于理智状态的暂时超脱,往往创造出意外的作品。看他书画题跋中屡屡出现的“酒后创作”——“曾在大理书此联,字大径尺,酒后,笔颇霸悍。距今已有几年不复记省。”“黄昏酒后,曾祺书。吾年六十六,书字转规矩,少逞意作,姿态尚得,少存韵致,不至枯拙如老经生。否耶?”在文学创作中,酒载人超脱理性、进入非理性和无意识状态,这种功能与梦相同。汪曾祺作品得自梦境的亦复不少,涉及“梦”的甚至比酒还要多得多,盖亦当作此理解。更不用说,酒对于汪曾祺的艺术创作还有一个更明显的作用,那就是题材之助。假如汪曾祺不是一个“饮者”,他绝对无法写出像《安乐居》这样把一群市井百姓的饮兴写得入木三分的作品来。
李建新:
总的来说,汪曾祺的文章还是以婉约为主,豪放的作品是少数。有人说,中国的酒神精神源头是道家哲学,是庄子,六朝的文人因醉酒而获得艺术自由的最多。汪曾祺也喜欢庄子,他在好几篇文章里做过自我剖析,称自己是“一个抒情的人道主义者”,受过老庄、禅宗思想的影响,但本质上还是儒家。当然,不同的阶段他的判断稍有区别。他在1993年写的一篇文章里说:“有评论家说我受了道家思想的影响,有可能,我年轻时很爱读《庄子》。但我觉得我受儒家思想影响更大一些。我所说的‘儒家’是曾子式的儒家,一种顺乎自然、超功利的潇洒的人生态度。”所以,汪曾祺的作品中,真正“幕天席地,纵意所如”的很少。我印象里,他的剧作《大劈棺》是一个特例,很像“醉酒状态”的作品。孙郁先生的《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中也特意拈出这一篇和根据《聊斋志异》改编的《小翠》加以评点。孙老师的书中那一章标题叫作“狂放之舞”,指出“在小说的世界里,他显得矜持,没有一点激进主义的冲动和玩世的态度。其实汪曾祺是个有狂气的人,这一点也是在他酒醉的时候才表现出来。奇怪的是,在小说里他不太表现这样的酒神精神,倒是在剧本里,嬉笑四溅,谐语飞扬”,说《大劈棺》“以嬉戏之笔,写人欲与世情,用的是荒诞的笔法,那些对话与情节, 令人想起加缪和萨特……他找到了一种真正的中国的荒诞精神的表达方式。那里有对庄子哲学的反讽,亦可见江湖文化的野性,还有昆曲式的缠绵。最怪诞的与最柔性的存在都在此间呈现。”
杨早:
当年我去汪先生家里,见到酒瓶的盖子都不是正常开启的,都是在盖子上戳一个洞,觉得特别奇怪。他喝了一辈子酒,在一定程度上有酒精依赖,这是物质上的;也一直有通过酒这种媒介,与精神相得的人交流的一面。“相逢意气为君饮”,是一种潇洒的少年气。
汪先生对烟也很内行。他觉得红塔山烟好,1991年参加笔会时,他不是还写了一首诗吗?“玉溪好风日,兹土便宜烟。宁减十年寿,不忘红塔山。”小说《讲用》中写郝有才嗜烟,甚至达到精通的程度。卖烟叶的怎么作假,都瞒不过他。那些七七八八的“知识”,应该也都是汪曾祺的积累。
我们现在看到的照片里,尤其是他的单人照,有不少是捏着一支烟的。要算典型的日常吧。
徐强:
1987年夏天,《纽约时报》的记者在北京采访汪曾祺,为他拍摄了一幅双目炯炯、手持香烟、在烟雾缭绕中神态自若又若有所思的大幅照片,汪曾祺本人十分喜欢。照片稍后在《纽约时报》刊出,当年年底汪曾祺赴美国爱荷华大学,东道主聂华苓也将这幅照片印了不少分赠国际写作计划的作家们。晚年汪曾祺搬家后,也将长期悬挂的高尔基像,换成自己的这张大幅照片。近年来出版的很多汪曾祺作品集,都收有这一张,被认为是最为传神的一张。这张照片的广为流传,把汪曾祺作为作家中的“瘾君子”形象广为传播。
现代文人嗜好抽烟,林语堂算得上一个深度痴迷者。他主编《论语》时,与同仁订立了不劝人戒烟的公约。据说“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这个口号就是他提出的。他在很多文章中对抽烟这一雅好赞美不绝,他拜服清代文人纪晓岚,尤其对纪晓岚那根特大的烟管崇尚有加。他的名文《我的戒烟》,写“误入歧途”进行三星期“戒烟”、最终迷途知返、下决心“老老实实作吸烟的信徒”的经历。文章幽默之极,把感觉写得刻骨铭心。汪曾祺是熟悉林语堂的,他一定对这一篇有深深的共鸣。有意思的是,他在《老鲁》里也写到过一个“甫来工作不久”的老吴,专管送信,“有发愤做人之意”,乃在自己床前贴字自警:“烟酒不戒哉,不可为人也。”叙述者评论说:“戒自然戒不了的,而且何必。”
在西南联大文人中,闻一多的大烟斗远近闻名,汪曾祺写过他上课抽烟的情形。后来闻立鹏的著名画作《红烛》即以抽烟斗的闻一多入画,成为公众知晓度最高的闻一多画像。潘光旦的自制竹根大烟斗寸步不离,上铭文:“形似龙、气如虹、德能容、志于通。”这些师长的表率无形中产生了同道鼓舞的效应。
李建新:
烟和酒都是能暴露人性弱点的事物,只要不是被嗜好彻底俘获,以弱点示人的人,不失其天真,甚至更让人觉得可近可爱吧。
2019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汪曾祺全集》出版,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举行了首发式。活动结束之后,汪朗、汪明、汪朝老师,还有苏北、龙冬、早兄我们十几个人去聚餐,很热闹。我记得汪先生的长女汪明老师席间讲了一件旧事,说是某一次老头儿到大学去演讲,由汪明的先生陪着,中午吃饭时就问:“要不要喝点儿?”汪先生说要喝。可能喝得确实有点儿多了,下午演讲时说话就不太利索,事后听讲的学生们反映:老头儿肚里确实有东西,但像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这样的小故事,只是漫长人生中的一瞬间,大部分岁月是平平无奇的。但回想一个人,首先想起的便是有点儿故事性的瞬间。“往事回思如细雨”,汪明老师去世也将近四年了。
作者简介>>>>
李建新,毕业于郑州大学新闻系,曾任《寻根》《中学生阅读》杂志编辑,2016 年参与创建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北京分公司出版品牌“星汉文章”,现任职于河南文艺出版社。编选有 《食豆饮水斋闲笔》《汪曾祺书信集》,编订有《汪曾祺集》(十种),策划《汪曾祺别集》 (二十种)并担任分卷主编,为《汪曾祺全集》中后期小说、书信分卷主编。
徐强,文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创意写作研究中心、新文学手稿文献研究中心主任。系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中国叙事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华近现代文学史料学会理 事,世界华文创意写作协会副会长,中国写作学会理事,吉林省写作学会会长。从事文学理论、 叙事学、新文学文献、语文教育、写作教育等领域的研究。著、译、编有《汪曾祺年谱》《小说与电影中的叙事》《故事与话语》《长向文坛瞻背影——朱自清忆念七十年》及《汪曾祺全集》(散文、诗歌、杂著诸卷)等。
杨早,文学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阅读邻居读书会联合创始人。著有《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环境与新文化的登场》《传媒时代的文学重生》《拾读汪曾祺》《民国了》《元周记》《野史记》 《说史记》《城史记》《早读过了》《早生贵子》等著作,主编《话题》系列(2005—2014 年)、 《沈从文集》、《汪曾祺集》、《六十年与六十部——共和国文学档案》、《汪曾祺别集》、 《宁作我:汪曾祺文学自传》、《汪曾祺文库本》(十卷)。译著有《合肥四姊妹》。合著有 《汪曾祺 1000 事》《墙书·中国通史》《小说现代中国》等。
[责任编辑 胡海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