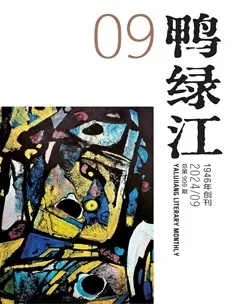辽河的湿地密码
辽河以水为笔,在入海口处肆意挥毫,似依恋又似撒欢儿,似庄重又似随意,在这片土地上信笔涂鸦,留下的笔道或粗或细,或深或浅,或长或短,或直或弯,每一弯都紧握大地,根根分明,条条相通,远远望去,像大地的叶脉,水韵灵动,蜿蜒绵延,又像水在大地上画出的一幅幅画,写意豪迈,工笔精美。
这幅画卷的主笔是辽河,东辽河和西辽河汇合后,一路奔行在下辽河平原,肆意挥毫。因为太过肆意,留给乡村发挥的余地就显得局促且不规则。于是,随着辽河的笔道,一个个村庄就那样随意地横亘在湿地和城市之间。在下辽河平原湿地,湿地、乡村、城市杂乱地堆砌在一起,随着世事变迁、岁月流转,居然长在一起,成为默契融合、色彩瑰丽的图画。乡村如城市的后花园,延展在湿地与城市之间,也如湿地卷起的彩色沟边,把城市与湿地无缝连接。湿地是乡村的最初表象,也是乡村文明的最终载体;城市是乡村发展的高端模式,也是与湿地共生的一种聚落。
水沿着一个个乡村的草木、河流、田土、人家、房屋、街路流淌,留下一个个名称、掌故、轶事、传说。被辽河水网浸润的乡村有着不同的地理物产、精神内核、文化特质、质朴乡情,沿着辽河留下的笔道,可以探寻这些村子的独特密码。生活印记在固态的形式下容易被保存,如古城、旧居、古道等,而水包容万物,也融于万物,水村生活的印记也易于被水洗涤、淹没、消融,因而湿地乡村不同于平原、丘陵、山地上的乡村:后者或依托地利、得天独厚,或分布错落,样貌俊秀,或传承久远、内外兼修,或卧虎藏龙、名人效应凸显;或独具特色,引人寻幽。而湿地乡村虽不具备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但它们也有着鲜明的特征,或蕴含着神秘传说,或承载着淳朴真情,或标志着地理物产,或传递着智慧胸襟等。它们不声不响、不瘟不火却内涵广阔、气度卓然。
辽河行至盘山县古城子镇,与浑河、太子河相遇,形成大名鼎鼎的三岔河。三河交汇,成为当地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相传唐代贞观年间,唐太宗亲统六军从洛阳出发东征高丽。行至三岔河,但见河宽水深,浊浪滔天,汹涌的大河拦住了去路。无桥无渡,数十万大军望河兴叹。雄才伟略的帝王,怎么能受困?唐太宗命先锋大刀王君可在三日之内务必找到渡河之策,否则问斩。军令如山!王君可接下军令,紧锁愁眉,前有大河拦路,后路泥泞不通,实在无计可施。王君可吃不香,睡不着,将至天明,才昏睡在军中大帐内。刚睡着,就见河神进帐,对他说:“明日寅时,河中有渡桥,大军可过河。”并叮嘱过桥后切不可回头看。王君可惊醒,急令探马查看。第一批探马回报说未见桥,王君可很生气,立斩之。第二、第三批探马也未见桥,均立斩之。待到第四批探马去探时,天色已晚,探马心想,实报无桥是死,谎报有桥也是死,不如谎报。于是谎报有桥出现于河面。王君可急忙报与唐太宗。李世民闻讯大喜,命大军紧急渡河。当唐兵行至渡口时,果然看见一座黑黝黝的桥。唐太宗急命连夜渡河,并命令只许前进不许回头看。大军抵达彼岸后,断后的王君可内心疑惑,黑黝黝的,到底是什么桥?他回头一看,原来这桥竟是由螃蟹堆聚纠缠而成!等他看清的一刹那,一声巨响,蟹桥塌陷,王君可连人带马掉入河中,被螃蟹啃食干净。相传,河蟹背上的硬壳,原本光滑无痕,被唐军的马蹄一踩,便留下了马蹄的印迹。如果把河蟹的胃翻过来仔细看,里面还有王君可横刀立马的小小头像。小时候顽皮,还多次翻找过王君可的形象。话说大刀王君可掉入三岔河,那把大刀横劈而下,成为分水剑,把河水清浊分开。到如今,三岔河水仍一半清一半浑,传说这是王君可的大刀落在这里的缘故。
美丽的民间传说当然无从考证,只有三岔河幽幽流淌。三岔河是幸运的,有古城子来承载它的欢乐与哀愁。关于三岔河的千年风涛,终会湮灭在历史的风尘中。在这里,水仿佛是另一种时间,把水下的一切变成历史。
三岔河在古城子汇聚,充分交流之后,转身打个旋儿,成就了一旁的小村青莲泊。青莲泊原名绕沟,为河水绕村而过的意思。因为出了一名关东才子李龙石,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绕沟,变身为充满传奇和文化味儿的青莲泊。也在用河水讲述着李龙石的传奇。清朝末年,天灾人祸频仍,洪水漫天,兵戈不息。天下滔滔之际,关东才子李龙石以才气动乡关,二十二岁中举,之后屡次赴京会试,因得罪权贵,铩羽而归。龙石公为人侠义,豪气干云,常为民请命,发不平之鸣。一次偶然北上昌图探亲,得知怀德县(今吉林省公主岭市)出台新令,将田赋翻了两番,农民不堪重负,纷纷抛家舍业,远走他乡。他基于义愤,代乡民拟状向昌图知府申诉。不料这怀德县令的官位正是重金从知府手里买来的,他伸张正义不成,反被罗织罪名,报吏部褫去举人名分,发配西北萧关。差官李福感于龙石公为人,行至山海关时,毅然焚毁文书,将他释放。龙石公只身亡命京师,藏匿在同年京官徐少云等家中。数年后左宗棠去世,他在友人举荐下代五府六部十三科道草拟挽联。其联搜括世上人间美赞之词,倾尽五湖四海哀悼之情,一时震动朝野,从而有机会面见刑部大员,陈诉冤狱,得以昭雪。回乡后,龙石公筹办“养园”学馆,传道授业,培育英才。当时辽河下游洪水肆虐,为根治水患,他向当局呈请开浚双台子河,获得奉天衙门批准实施,将辽河主道导入双台子河。自此,辽河安澜,无边无际的辽泽洼地,变为鱼米之乡。峥嵘岁月俱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如今的青莲泊伴着三岔河的涛声走过一个个晨起日落,依然炊烟袅袅、杨柳依依。
辽河一路穿村过镇,沿岸村庄多以水命名,如河沿、水库、水岸、河南、沟北等。在水库与河沿之间,小村驾掌寺如辽河一个闲笔,依傍辽河而苏醒与睡眠。驾掌寺这个名字与水无关,却是一个关乎河的故事。据传,明末清初一年秋天,一场暴雨连降七天七夜,河水漫溢,房屋倒塌,一片汪洋。灾民流离失所,衣食无着,乃至饿殍遍地。一位须发皆白的船老大偕子驾舟,循声救人,将灾民运至河沿唯一一处高坡地,把这船人安置登陆,又驶向茫茫天外。从清晨划到深夜,又从深夜划到清晨,一连三日,当他把最后一个人救上岸时,自己竟累死在船头。水退之后,幸存者感其恩德,在高坡上为其立庙,因不知其姓名,取名为驾掌寺。因为当地人把驾船的艄公称为“驾掌”。众人在庙宇周围定居,晨昏祭拜,并相约效法老驾掌,终生行善。潮涨潮落,日月更替。数百年之后,当国家民族遭逢大难,从小村驾掌寺走出的仁人义士,传承老驾掌侠义精神,投身抗日,高举义旗,把爱国的旗帜写在大地上。
一路上沿着水的指引,驾掌寺全貌逐渐显现出来。在苍茫的天地间,白雪覆盖的房舍、田宅,小村如淡墨勾勒的一叶扁舟,稳稳地停靠在辽河边。百十户人家的小村,整齐地排成队列,和谐的配置,流畅的美感,最有名的画家也描摹不出。画面上,北方乡村特有的尖顶瓦房坐北朝南,勾勒出地域特色。村前小桥横卧,小河蜿蜒;村内院落围墙,有序排列;村后沃野千里,直通天际,雪野与蓝天交会在视野穷尽处,把这幅水墨画引入无穷的意境。从外在看,小村的诗情画意与别处的诗情画意如出一辙,然而,若想融入这幅画卷,还需要详读村落密码,审慎做出抉择。驾掌寺村的密码索引是两个关键词:“老驾掌”与“侠义精神”。出来的时候,雪依然不紧不慢地下着,微微地随风打着旋,漫无边际地飞舞,好像一点儿也不急,有充足的时间来演绎这场舞蹈。经过雪的过滤,空气格外清新。相比于春天的鲜活、夏天的泼辣、秋天的斑斓,辽河口的冬无疑是内敛、恬静的。没有了花的喧嚷、虫的聒噪、雷的轰鸣,这里的冬单调,甚至是枯燥的,就如水墨画中大片的留白,这留白虽不动声色,又有独特的韵味在其中,这韵味就是水墨的灵魂。驾掌寺这幅生动隽永的水墨画,是以义字为灵魂,经过长期岁月的浸润,终于长成辽河口人血脉深处的精神图腾。
越临近入海口,辽河越撒欢儿,水把岸浸润得透透的,稻在河与海的滋养下,成片成片地生长。仅仅百余年,黄色的稻浪已经和绿色芦苇荡、红色翅碱蓬一样跻身辽河口湿地三原色。而荣兴村据说是1928年张学良开办的营田公司旧址。营田公司以抽水机引辽河水灌溉,开创了东北地区水稻生产机械化的先河。稻伴随着水与泥,一点一点融进生活。不论是碱滩开荒,还是发展特色农业,人与稻,稻与人,都在相互改变,最后,稻走进人的日常生活,人把稻做成轻博物馆,obDOXIseqKXueyebTxjoGQ==就叫“稻作人家”。荣兴村里不用的老房子也没闲着,做成“稻作人家”民宿,据说运营得还不错。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回到这里,寻找、回忆、收集、集聚、固化,乃至升华。当年点亮稻作文明的人一茬茬老去,“稻作人家”依然立在那里。当人们体验和重温过后,回到各自的生活,稻作仍作为一种文化,深深刻入灵魂。
行文至此,我还想用一处关隘锁住这一方水土,这处关隘就是赫赫有名的黑风关。当初的烽火狼烟已然不见,如今这里白墙黛瓦,屋舍俨然,稻田围绕,水流潺潺,整个村子像一个没有围墙的公园。 信步小巷,房前屋后干净整洁,院墙整齐划一,行道树挺拔葱郁,花草连片覆盖,路灯排排成行,整个村子绿树环绕,花红草绿,天蓝水清,似一幅风光旖旎的画卷。
这幅风光旖旎的画卷在早先却不是这样,它是史上赫赫有名的黑风关,据传是评书《隋唐演义》中“薛礼征东”的重要关隘。那里曾留下烽火鏖战的英雄侠义,也留下毒烟、瘴气、陷阱和“十二把飞刀”的传奇。据传,黑风关始建于隋末唐初,主城、东西南北延长各为一百二十丈,分设东西两座拱形城门,城墙高三丈六尺,底部宽八丈,顶部宽三丈,两侧垛口林立。主城建筑面积为一万四千四百平方尺,与东西两座城门相连,又分别设有二丈八尺高的瓮城,以备战时应急之用。城内分设四条登城马道,东西两座城门顶部又分别设有城门楼、旗杆,内城可容纳三千兵马,东门外设有校军场,城西有下水道,由城内流向南面的大海沟而流淌入海。
自唐朝以来,黑风关城凭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及丰富的海洋资源,成为交通重要门户,也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到了明代末年,这里更成为抵御清军铁骑的重要关口。一茬又一茬的刀兵鏖战过后,黑风关沉寂下来,犹如一座死城。这时,有一户关里的李姓人家,筚路蓝缕,风餐露宿,来到黑风关城下。看到狼烟过后的一片死寂,大着胆子想进城定居,可抬头看见城墙上的大炮,担心军队回来惹出是非,就没敢进城,定居在了城外。黑风关城北有一个打造刀枪兵器的铁厂,城南有一座道观,名叫圣清宫。这李姓人家为了与关里家人通信联系,便以铁厂为标志,给这里起了村名叫大铁厂堡。后来,村名逐渐演变为大堡子村。
三百多年,沧海桑田,世事变迁,第一个来到这里的李姓人家一直没有离开,他们耕读传家,用实际行动诠释自己的家园梦。大堡子的文化带着渔耕文化的内敛和自给自足的味道,也带着移民文化的开放与包容的气息。漫长的三百多年,村民把愿望、诉求寄托在道观圣清宫里的诸神身上。圣清宫始建于清雍正年间,香火繁盛时为东北最大的道观。后来圣清宫因年久失修,湮灭在岁月的风尘中。如今重修的道观静静伫立在村中,绽放着历史文化的光辉。其实,不论是黑风关、大铁厂,还是圣清宫,都是大堡子历史变迁的文化符号。这些文化符号穿越历史,到如今还熠熠生辉。
走进大堡子,仍能感受到历史文化的独特内质。一进村,以廉政名言警句和《传统二十四孝》《弟子规》及古诗词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墙,让村子的文化味道一下子浓厚起来。别的村子该有的文化活动,这个村子一项不落,甚至夕阳下跃动的身影和晨起琅琅的读书声都和别的村子如出一辙。要不是每年都有人从全国各地特意寻访,谁也不知道高出地面近一尺的土堆就是大名鼎鼎的黑风关。看着平平常常的黑风关旧址几个大字,想着脚下这片土地发生的激斗鏖战,再一次对这片人文厚土肃然起敬。从前世到今生,大堡子从烽火狼烟走到生态宜居,从筚路蓝缕走到绿意盎然,辽河口人的家国梦,从来没有如此舒展、温润。
辽河走笔,水村如画,每幅画都是新的。水村的年岁不在外貌,不像古城、古村、古道那样长在脸上,也不像古树、古桥、古画那样比岁月悠长,水村的年龄是长在心里,长在骨髓里。辽河一遍遍冲刷洗涤,冲刷大地,冲刷岁月,也冲刷辽河口人的心田;辽河流过城市,流过村庄,流过红滩绿苇,最终流向辽河口人的心海。
作者简介>>>>
曲子清,辽宁盘锦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盘锦市文联副主席。在省级以上报刊物发表文学作品百余万字。代表作为“湿地三部曲”(《湿地锦年》《湿地繁花》《冰陷湖》)。
[责任编辑 胡海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