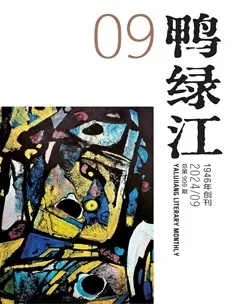好汉帮
老刘是我见过的第一个自我介绍时称自己是老板的人。他说,我姓刘,你叫我刘老板就行。说完,他似乎觉得不妥,又补充了一句,当然了,你是大老板,我是小老板。
我乐了,说,大老板小老板都是老板。他本来脸上就带着笑,这会儿笑意更浓了,黑红的脸上闪着瓷实的光泽。
老刘是我找来打短工的工头儿。过了十一,我自己带的民工有一部分回老家抢秋,这个时候项目上又开始“大战一百天”,进度和节气赛跑,总是想在上冻前多出成果。为了弥补人员不足,我只好托人在当地找打短的民工。老刘就是别人介绍给我的一伙打短工的头头儿,五十左右的年纪,矮矮壮壮,没说话先笑,对方说话时频频点头,表情谦卑。
我问他,你手底下有多少人?他反问,你需要多少人?
我指着前面的一块空地说,那里要建一个涵洞,不大,人多了摆布不开,有十多个人就够了。老刘点着头说,了解,我带12个人过来。我说,12个人半个月怎么也干完了,工钱怎么算?
老刘说,大工一天500元,小工一天300元。算上我,我们是6个大工6个小工。
看着他脸上一成不变的笑,我不由得也笑了,说,你要价太高了,我工地大工才350元,小工180元,而且你这人员配备也有问题,不都是一个大工配两个小工吗?你这是一配一。
他依然笑着点头,先说,老板你说得都对,话锋一转,语气中透着不容置疑,老板,我们打短的就是这个价钱,大小工也是这么搭配的,咱保证给你把活儿干好就完了。言下之意是我计较得太多。
我觉得他提的条件太高,就让他先回去等信儿。
我又通过别人找了两伙人来谈,可是要价更是高得不着边儿。我想肯定是老刘暗中做了手脚,这些当地的小工头儿互相都有联系,也都有各自的属地。全国各地差不多都是这样。我有些后悔当初没同时找两伙人一起谈,也佩服老刘动作敏捷,前脚出门后脚就把消息散出去了。心里虽然生气,却不能置气,项目上一天好几个电话催我把那个涵洞早点儿弄完,说是影响了全段路基畅通,到时候后续的运输、上料都是问题。没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给老刘打电话,说我这边基坑挖好了,钢筋制作完了,模板也拉到了现场,你带工人进场吧。
老刘他们来了,算上他12个人,大都四五十岁的年纪,看着还行,是干活儿人的架势。老刘的助手老郝和他年纪相仿,个子不高,精瘦,和老刘的粗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他人围着基坑转悠相看的时候,他俩一起站到我面前讲细节。
老刘说他们每天工作8小时,早饭晚饭不在工地吃,中午工地伙房得给送饭。
我说,送饭可以,每天就干8小时活儿有点说不过去,我的工人都干10小时。
老刘笑得云淡风轻,没说话。老郝说,老板,我们这就是这样,都是干8小时活儿,再说我们又不在您这儿吃早饭、晚饭,您这也是赚了。老刘在旁边连连点头,脸上的笑意更浓了。
临时打短的都是干8小时活儿,这我知道,不过是想争取一下而已。两个人一唱一和,态度那么坚决,我的“争取”失败,只能应了他们。
技术员放好了线,一项项交代施工要求的时候,老刘悠闲地抽着烟和工人们开着玩笑。他们说着当地的方言,有的话我听不懂,看他们一个个笑逐颜开的样子,不知道老刘和他们说了什么。老郝则拿着图纸颠颠儿地跟在技术员屁股后,问来问去,一边还在小本子上记着。
安排差不多了,我上车发动了车子,准备去镇上买菜。我们施工的地方远离城市,除了买建筑材料,我才开车跑出去几十公里进城,一般的柴米油盐等生活必需品,都在镇上买。镇子叫刘家集,这里叫这个集那个家的地名挺多。刘家集的街面比一个县城的集市大不了多少,东西南北两条十字街,街道上有邮局、储蓄所、五金店、粮油店、超市、学校等,还有零星几个饭店。我买米买菜是在一家超市,去过几次熟了,需要什么打电话跟店主说,他在城里进货时就给带回来,赚点儿差价。
我刚发动着车子,却看见路基上驶来一辆电动三轮车,骑车人身体几乎趴在了车把上,车子后面扯起一路烟尘。本以为这是一辆过路的车子,没想到它却一下子冲到了我的车前。骑车人从车上下来,瘸着一条腿,走起路来一悠一悠地,细瘦的身子就像一根弹簧一样在地上弹来弹去,几下就弹到了我的车旁,一张黑瘦的脸扬起对着我,脸上的皱纹抖动着,高高低低地蠕动着笑意。
我落下车窗玻璃,用询问的眼神看着他。他问,您就是许老板吧?虽然是问,但语气分明已经很肯定。我不能坐在车上了,只好下车。
我站到他面前,才发现这个人是个高个子,虽然他一条腿弯着脚尖点地,另一条腿也微微弯曲,但是也比我这个中等身材高出了半个头。他说,老板,我姓姜,叫姜明山,是来给您送菜的。我奇怪地说,我也没让你送菜呀。他急忙解释,我知道你去城里买菜路太远,镇上卖给你的菜又贵又不好,以后你的菜就我给你送吧,保证菜又好又不贵。说完,他就巴巴地望着我。
原来是个卖菜的。我还没想好怎么应对,远处的老刘就大声说,老板,你可别要他的菜,他的白菜都是烂的,萝卜、土豆也都蔫巴了。我面前的人转过头看他一眼,没搭话。我这才知道原来他们是认识的。
姜明山转身吃力地把三轮车推到我面前,我看见车上装了满满一车菜,有白菜、萝卜、土豆、辣椒,还有一条红鲜鲜的肉,分别装在白色塑料袋子里。他一边翻腾着袋子一边说,老板,您放心,菜都是好菜,肉也是好肉,斤两和价格,袋子上有标签,您要是不相信,可以称称看。我拿起一袋白菜看了下标签,价格倒是不贵,就随手把白菜倒了出来,里面果然有几棵白菜的菜帮是烂的。
这时老刘和老郝也都凑了过来。老刘讥笑着说,怎样?我没说错吧?老板,我跟你说,分量也不足,要不你找个电子秤称一下就知道了。姜明山脸上泛红,却不接言,跨上车开着就走。我以为他要离开呢,谁知他却把车开到了看护房旁的空地上,卸了点儿菜到地上。见他这样,我只好抬高了声音说,你不能把菜卸到这里呀,给我送到伙房去。他大声回道,这里卸点儿给他们吃,他指了指老刘,又说,剩下的我给送到伙房。
老刘哧哧笑着,嘴里却说,老板,你看你看,他就是个无赖,你别搭理他。然后他又冲着姜明山大声说,我说你这人能要点儿脸不?我们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烦死个人。
姜明山还是没接他话茬儿,说了句,我先把菜送到工地,一会儿回来。上车俯着身子把车开走了。
不用去买菜,我就不急着走了,再说人家已经把菜送来了,愿意不愿意也得等着他回来,把菜钱给他,大不了下次不用他送就行了。可是他为啥把菜卸到这里一些呢?
老刘似乎猜到了我的心思,说,他这是要给我们做午饭呢,谁爱吃他做的饭菜,跟猪食差不多。我说,咱不是说好了我供饭吗?他给你们做啥饭?
老刘笑着说,是,是,咱说好了,可是你也看到了,这家伙赖着不走,你说怎么办?
我心里纳闷,要说他们约好了吧,可是看老刘对姜明山的态度又不像,就说,你们要自己开伙也行,就让他做呗,不过他的工钱我可不管。老刘摇着头说,我可不想让他做饭,也没有跟你要工钱的意思。说完,他就招呼老郝下基坑干活儿。
姜明山很快又回来了,车行一路叮叮当当,在看护房旁停下。我走过去,看到车里装着煤气罐、大勺、锅碗瓢盆等一应用具,米、面、油,还有一个装满水的白色塑料桶。他找来工具、木板、木方,叮叮当当忙碌着,很快钉起了一个两米见方的敞口木匣子,往起一立,就成了一个简易小房子。他又用木方和板子钉了一排架子放进房里,然后就把车上的东西往里面搬。
做这些的时候,他一直没和我说话,只是偶尔看我一眼,笑一下,露出白牙。我也没主动和他搭话,倒要看看他这台独角戏怎么往下唱。
仲秋里,风平浪静的日子,天空洁净,没有云彩的遮挡,阳光虽然不像夏天那么炙热,但是光芒尽洒,太阳地里站久了,也是脸红身热。姜明山把东西搬完,解下系在车把上的一条毛巾,一边擦着脸上的汗,一边进了小房子。
这时老刘和老郝走过来,老刘站在小房子的敞口处,说,你是不是闲得裤裆冒火,跑这泻火来了?老郝也站在旁边说,你就跟锅碗瓢盆亲,多少年了,还忘不掉?姜明山像没听见他俩说话一样,闷头抽烟,不时抬头看我一眼,脸上挤出的笑极不自然。
老刘和老郝又打趣了几句,回去干活儿了。我虽然觉得他俩有些过分,但是听不懂他俩说的是什么意思,也搞不懂他们三人之间的关系,也就不便说什么,想着菜钱还没给姜明山,就让他算算一共多少钱。姜明山说,一共375元,您给我370元就行。我加了他微信,给他转过去380元,他说了声谢谢,把钱收了。我趁机问,你和老刘他们挺熟?他说,一个村的。我又问,他和老郝怎么总挤对你?他咧嘴笑了下说,自己不好的人,心虚,才总说别人不好。他俩,一对儿,都不是什么好人。老刘成天和媳妇闹别扭,吵不过就出来撒气。老郝是他的小跟班,从小到大,他就是老刘的狗腿子,这人,天生的一张臭嘴,你还指望他能说出啥好话来?
我还想问下去,或者安慰他一下,他已经开始择菜、切菜,从一个大塑料桶里打水洗菜。看他准备得这么充分,干起来轻车熟路,有条不紊,应该是常这么干。
老刘又从基坑里出来,他走到我们跟前,又用方言讥讽了姜明山几句,似乎和女人有关,听得我云里雾里。没等我琢磨过味儿来,老刘给我使了个眼色,示意我跟他走。
往旁边走了几步站住,老刘瞥了一眼小房子,笑容里的坏若隐若现地藏不住。他说,老板,你也看到了,这姓姜的就像狗屁膏药似的贴着我,跟老太太尿罐子一样,管哧管卤,说啥他都不走。我也是没有办法,这饭不想用他做都不行。
我想替姜明山说句话,就说,你们乡里乡亲的,他实在要做就让他做呗。
老刘瞅我一眼,说,老板啊,你说得轻巧,可我这不又多出一笔开支吗?你当他白给做?
我明白他的意思,就说,你们不在我那儿吃,我把饭钱补给你,每天每人10块钱。他笑了起来,脸上的肉直抖,像极了刚出锅的颤巍巍的猪头肉。笑过了,他说,老板,你可太会算账了,10元钱哪够呢?是,现在这些菜是你给的钱,可是也只够吃一顿的,再说还有煤气、米呀油呀调料什么的,再加上他的工钱,你给我10元钱?
我说,我的工人一天的伙食费才15元钱,你这一顿就给10元钱,你还不满意?再说,他给你做饭又不是我找的。
老刘瞪大眼睛连连摇着头,说,也肯定不是我找的,你也看到了,是他自己赖着不走。再说,你们伙房的伙食我们这里人也吃不惯,我才没有坚持撵他走。
我说,那是你们之间的事,你们自己解决。要么给你补钱,按我说的数,要么让他走,你们去伙房吃。说完,我转身要走。
老刘伸出粗壮的胳膊拦住我,脸上依然挂着笑,话里却带着锋芒,老板,不至于吧,为了十块八块的,咱这就不合作了?
这根本就不是钱的事。我刚想发作,姜明山从木板后探出头,说,老板,你也别跟他生气,他就那样人,计较惯了。10元就10元,不行我少要点儿工钱。
老刘的脸比川剧变脸变得还快,笑容一下子不见了,鼓着圆眼冲他吼,你说得轻巧,你总是觉得自己很能,结果呢?
又是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姜明山回了句,你能,也没见你好哪儿去。说完,头缩回去了。老刘作势要冲过去,我也没拉他,结果,他脚迈出去又收了回来,对我龇牙一笑,说,既然他这么说了,老板你就看着办吧。
到底是不能因为小钱把活儿弄砸了,也真就没什么道理可讲,有时候道理不得不给“规矩”让路。再一想到姜明山瘸着一条腿,别真就等着算账时老刘不给他工钱。我的心思仿佛早被老刘看透了。我是又窝火又没有办法,最后答应每人每天给他补20块钱。
我第二天去的时候,正赶上饭点儿。姜明山把菜盛了两大盆,一盆是土豆片炒辣椒,另一盆里面装着颜色比酱油淡一点的大肉片子,这里的人管这个菜叫卤肉。工人三三两两地围坐在一起吃喝。老刘和老郝隔着一个用木方和板子订的桌子对坐,桌子上摆着饭菜,还摆着两只空碗和一瓶白酒。
我对老刘说,中午喝酒下午怎么干活儿?也危险,想喝酒晚上回家再喝呗。
老刘仰着脸笑嘻嘻地说,喝点儿酒干活儿才有劲呢。
我还要说什么,老郝站起来说,没事,老板,老刘就这样,一天三顿酒,啥事也不耽误,他心里有数,不能喝多。
没等我再说话,姜明山过来把一盆汤放到他俩面前,拽了我一把,转身往小房子走。
老刘大声喊,老姜,你咋走了呢?赶紧给我把酒倒上。
没想到姜明山果然听话,转过身又回来,拿起酒瓶子往老刘面前的空碗里倒酒,足有小半碗。
老刘笑眯眯地看着他,说,你倒酒的水平是越来越差了,瞧瞧,倒外边了,糟践东西呢。
姜明山嘿嘿笑着,哈着腰望着老刘,说,你尝尝,我今天做的卤肉咋样?
老刘夹起一块肉,我以为他能都塞到嘴里,谁知他只咬了很小的一口,嚼都没嚼,只吧嗒了一下嘴,就“呸”地吐到地上,大声说,姜明山,你这是做的啥?喂狗呢?你自己尝尝,这肉能吃吗?
姜明山冲旁边摆了下头说,你再好好尝尝,你看大伙儿吃得多香。
那些工人都鼓着腮帮子吃得满嘴流油,一看这肉就能挺香。
老刘把筷子扔到桌子上,端起酒碗喝了口酒说,他们是他们,我是我,老子吃你这肉就不是味儿。
我心想,这不是胡搅蛮缠故意找碴儿吗?可是姜明山一点儿也不生气,拿起酒瓶子,给他把酒添上,给我使个眼色,转身一耸一耸地走了。
我猜不透他们之间打的哑谜,也听不懂他们话里的意思,不想再看老刘嚣张跋扈的样子,就跟着姜明山往小房子走。
老刘还不依不饶地大声说,我看你小子这手艺是越来越差,我咋就吃不到以前的味儿了呢?你老婆的绝活儿你是一点儿也没学到啊。
姜明山身子耸弹得更快了,不理他。到了小房子,姜明山问我要不要尝尝卤肉。我说我吃过了,他就自己盛了饭菜在案子前坐下吃起来,一边吃一边含糊不清地跟我说,老板,老刘喝酒这事你别担心,他这些年让酒泡出来了,你以为他那张脸是晒红的?那是酒泡出来的。要是不让他喝点儿酒,别说干活儿了,他连吵架都没有力气。
听他这么一说,我的心才安稳了些。
吃完饭,工人们找背阴的地方,在身底下垫块板子休息,要么刷抖音、快手,要么睡觉。姜明山把碗筷盆子收拾回来刷洗干净,然后绕着场地走一圈,把木方、木板归拢到一起,回来又把看护房前空地上的工具拾掇到一起。等他坐下休息的时候,我说,辛苦你了老姜,这应该是我派人干的,可是人手实在太紧,那边抽不过人来,打更的老李岁数又大,干不动这些。这样,我也不白让你忙乎,给你点辛苦费。说着,我点开手机给他转过去五百块钱。姜明山笑笑说,没事,我闲着也是闲着,再说这都是咱们的人造的,老刘这人就这样,活儿干得没说的,就是邋遢,我是替他收拾。
下午干活儿的时候,我暗中观察老刘,果然健步如飞,手底下也有力气有准头儿,一点儿不像是一个喝酒的人。我悬着的心这才彻底放了下来。
我转给姜明山的钱他没收,第二天自动退回来了。我搞不懂他为啥不收,也没再给他发。
第五天的时候,我又到那儿去看进度,绕基坑走一圈,心里焦虑的火苗“噌”就上来了。5天了,涵洞的基础才刚刚打完混凝土,照这个进度,15天哪能干完?我把老刘喊上来,跟他说,5天过去了,你们才把基础做完,这么干可不行啊。
老刘笑着直点头,连连说,是,是得抓紧。可是接下来的话却一点也不软,老板,你也看到了,我这伙人干活儿可不含糊,到点儿来,到点儿走,不迟到不早退,除了喝水抽烟,我们是连喘口气的空都不得呀。再说了,你不能不让他们拉屎撒尿吧?
在见老刘之前,我跟打更的老李头儿了解了情况。老李头儿是我的人。他说这伙人干活儿还行,就是屎尿太多。
我见老刘眼睛直往看护房那瞟,担心我不在的时候他们难为老李,也就不好再说什么。另一处工地正在建一座立交桥,我的主要精力得放在那面,不能被这个小涵洞牵涉太多。可是又不能不来,再不紧着点儿,他们不定给干到啥时候呢。还是得想办法早点儿把活儿干完,早干完早静心。我想了想说,要不你们加点儿班吧。
老刘摇摇头说,我们不加班。说得斩钉截铁。我沉不住气了,不客气地说,老刘,你别太不像话哈,你们挣谁钱不知道?
老刘脸上的皮肉绷了下,笑容像条鱼潜下去又浮上来,说,这个呢,首先得感谢老板你赏我们一口饭吃,让我们有活儿干,有钱赚,然后呢,咱也是卖力气吃饭,加不加班这事咱自己说的算。
我回怼他,你们在我工地干活儿就得服从我的管理。老刘不让步,语气坚决地说,合理的,当然得服从,加班,太累,弟兄们干一天活儿了,受不了。
我说,我的工人每天工作10小时,你们怎就不行?早来点儿晚走点儿呗。
老刘说,咱这地方就这样,咱这里的人也跟你们比不了,不能天刚亮就干活儿,天不黑不下班。
他这副蒸不熟煮不烂的样子真是可恨,我心里给他算账让他滚蛋的念头直往上冒,可是又一想,他们走了这里的活儿怎么办?整到这种地步了,我就算是出高价也没人接手,我那面的工地还抽不出人来。
正在僵持的时候,姜明山从小房里出来,对老刘说,咱上班是太晚了,人家都干一气儿活了,下班也早,太阳老高就回家。老板这边还着急,咱心里能得劲儿?
老刘收了笑虎着脸呛他,滚蛋,两个老板之间谈事,你个做饭的跟着掺和什么?
我简直哭笑不得,就一半逗他一半商量着说,刘老板,考虑一下?
他望着我眨眨眼睛,一副很无奈的样子,说,要加班也行,每人一小时100元。
这不是明抢吗?刚压下去的那个念头又开始汹涌澎湃,我按住它,尽力让自己不露声色,说,咱按照工资核算,大工一个小时60多,我给你70,小工一个小时不到40,我给你50。够说了吧?!
老刘嘎嘎笑了,笑得脸红脖子粗,跳动的肥肉把挺大的眼睛挤成了一道缝,笑过了才说,老板,你这么大的老板啊,账算得这么小气这么细?加班这事还分什么大工小工?
我听出了他话里的讥笑和不屑,却无法发作,就说,老刘,虽然你是小老板我是大老板,但我也是挣人工费的,你这么跟我整,我这个涵洞可是要亏钱的呀。
老刘诡异地笑了下说,老板,一大一小可是天地之差呀,你是赚人工费的不假,可项目上给你的不止这点儿钱吧?算了,反正我们也不想加班,你要是觉得不行,那就还这么干吧。说完,他对我笑笑,转身走回去又下到了基坑。
虽然最后我做出让步,老刘他们也每天加班两个小时,但是计划15天的活儿,他们足足干了21天,我算了下账,让老刘这家伙狠狠赚了一笔。
完工算账那天,我拿出钱给姜明山,让他买点儿酒菜回来,说不管怎样大家都挺辛苦的,这完工散伙儿饭还是要请的,也要吃得好一点儿。
吃饭的时候,我跟他们坐在一起,也喝了点儿酒,大家轮番给我敬酒说着恭维的话。唯独老刘不敬我,他只跟姜明山喝,不停地催促姜明山给他倒酒,还让姜明山给他点烟。姜明山一点儿也不比老刘喝得少,喝得黑脸变成了灰白色,老刘让他干啥就干啥,不急不恼,老刘怎么奚落他他也不生气。
我把碗里的酒喝完,站起来离开他们。
深秋的傍晚,寒意渐浓,清爽的微风吹在发烫的脸上,特别舒服。天边的云彩烧着了一般浓艳,在旷野里投下斑斓的色彩。走了几步,转身看着坐在晚霞光彩里热闹喧嚣的那群人,说不上为什么,我这个成年在外心硬如铁的人,鼻子一酸,竟有了想家的感觉。
老郝似乎是怕我被冷落,跟过来小声说,老板您别介意,老刘就那样,光顾着掐了,他俩掐几十年了。我问,为啥呀?老郝暧昧地笑着,说,还能为啥?当初他和老姜都看好了村里的一个姑娘,姑娘后来嫁给了要个头有个头要长相有长相的老姜。
我问,老刘就为那个姑娘,一直跟他过不去?
老郝说,也是也不是。怎么说呢,老刘觉得损损他才得劲儿,也觉得这样老姜拿钱才舒服,要不,他一个瘸子,能赚到啥钱?
我问,老刘的腿是后来才瘸的?老郝说,是,婚后夫妻俩在镇上开了个饭馆,招牌菜就是卤肉,那是女人家传下来的。饭店开了几年,老姜有次把一个调戏他老婆的人给揍了,自己也摔断了一条腿。饭店开不下去了,老婆上火得了不好的病死了,扔下俩孩子和爹妈。老姜这些年也不容易,拖着瘸腿找不到固定营生,逮啥做啥,倒也把孩子供出去了,老丈人岳母也一直养着。对了,你给老姜钱的事他跟我们说了,那钱他不能要。
能要老刘的钱却不要我的,这个老姜,倒是挺有意思。我打消了想给他补偿的念头。我倒是可以跟他说,虽然这个活儿干完了,但是那面工地伙房的菜他可以继续送。
冬天完工撤场的时候,我去镇上银行取钱给工人开支。下雪了,细碎的雪花稀稀疏疏,倒像似街边槐树抖落下来的花瓣,把整个街道罩在白而朦胧的世界里。
我从车上下来,向银行门口走去,远远看到老刘、老郝和姜明山三个人迎面走来。他们穿着亮闪闪的羽绒服,姜明山走在中间,一弹一耸的,旁边的两个人簇拥着他。
我恍若梦中,心里瞬间落上了一层雪。
作者简介>>>>
薛雪,原名薛宝民,辽宁盖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营口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盖州市作家协会主席。在文学期刊发表中短篇小说数十篇,出版长篇小说《县报记者》、报告文学集《那一条碧波荡漾的河流》。
[责任编辑 陈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