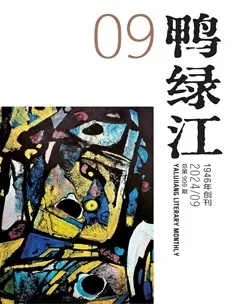圈上
清明刚过,凌晨三点左右,公鸡打过第一遍鸣儿,男人就醒了。里外间两铺炕上,六个孩子还在酣睡。
女人用胳膊肘碰碰男人,接着昨晚没有议定的话题:“今天队长家三儿子结婚的人情,真的不赶了?”
男人没吱声,但能听见喉结咽唾沫声。
老半天,男人挤出一句话:“拿什么赶?左邻右舍和亲戚家都借遍了,再张口借钱,也是白撸一嘴漦水。”
女人沉思了一会儿,说:“我半夜醒来还在寻思这个事儿。这个人情不能不赶。咱家成分高,咱俩这辈子没有什么出息了,可六个孩子我们还得给找出路。孩子们当不了兵,可招工什么的,还是越不过生产队队长这道坎儿。”
男人重重地“嗯”了一声,又陷入了沉思。大姑娘清溪十七岁初中毕业,到生产队劳动一年多了,样样泼实肯干,还没拿到整劳力的工分。大儿子清河十六了,为减轻父母负担主动辍了学,长成大小伙子了,一百五十斤的麻袋包都能扛起来,挑抬铲耪拼死拼活地干,还给“小半拉子”工分……大儿子晚上回家,经常一声不吭,扒拉两碗饭,倒头就睡。
在生产队里,成分高的人遇见什么事,都以缄默为好。
今天队长家这个人情得赶,但是上哪儿去借点儿钱呢?
女人说:“这样吧,把大公鸡卖了吧。”
男人说:“你不是留着做种鸡吗?现在母鸡都到了抱窝季节,离了种鸡怎么办?”
女人说:“是,离了种鸡不行,但现在还没有一只母鸡要抱窝。一旦有了,我拿鸡蛋去邻居家换种蛋吧。”
男人说:“那不得两个蛋换一个吗?”
女人说:“打一棒子躲一躲吧。”
男人说:“这个人情今儿个不赶了。昨天我给队长家帮了一下午工,在院里砌了两个大灶,就算赶了人情了。”
两口子都不再言声,外面的公鸡打了两遍鸣儿。
女人想了一会儿,又催促男人道:“我寻思这事儿还是不妥。倘若队长家以你帮忙砌灶为由,中午请你吃饭怎么办?人家大喜的日子,你就两个肩膀扛一张嘴去白吃?”
一句话戳疼了男人的心。这个人活到四十五岁了,脸皮比纸还薄。女人说:“赶快起来吧,趁天儿没亮,把大公鸡捉了,到集市上卖了吧。顺便你买双解放牌单鞋。脚上还穿着过冬的棉胶鞋,也该趁这个日子换了。”
男人在心里点头。是呀,昨天去队长家帮忙,男工女妇的,就他还穿着一双棉鞋,借着砌灶累出了汗,他脱光了脚。这桃杏花儿都谢了,单鞋还没有着落。
“好吧。”男人吐出两个字。夫妻俩立即爬起,穿好,堵在鸡窝门前,打开了窄窄的鸡窝门。
往常,大公鸡是家鸡之王,打开鸡窝门总是第一个钻岀鸡窝,拍打拍打翅膀,踱着方步,昂首叫两声。今天它像会掐算似的,没有第一个出来。李凤举一把抓住头一只鸡,一看不是,放下了。又抓第二只,借着曦光一看,还不是,又放下了。就在这个当儿,大公鸡“嗖”地蹿出了鸡窝。张伯利撸了一把没撸着,大公鸡顺势跳上了墙头儿。
男人心一紧,抄起一把搂草的铁耙子,一耙子把大公鸡扑下墙头。待夫妻俩扑上去按住,只看大公鸡翻了两下白眼儿,扑棱了两下翅膀,死了。
夫妻俩大吃一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过了三五分钟,大公鸡蹬了两下腿,翻翻白眼儿,醒了。
男人大喜过望,赶忙抱起大公鸡,说了一句:“哎呀我的祖宗!”
女人赶忙从衣兜里掏出提前备好的布条,把大公鸡两腿绑了,两个翅膀根儿缚了,抓过一个拐筐来,把大公鸡放进去。找一块旧布剪一个透气孔,没缝前又给大公鸡饮了点水,看看确实没问题,便把筐与布缝好。
男人拐起鸡筐,掂了掂,说,总得有八斤往上。这时冷丁想起来,公社所在地今天不是集市。大脑反复搜索,想起邻公社有集,不过离家远点儿,差不多有二十里。
二十里也得去,男人拐起鸡筐,甩开大步就走。走一段路,感觉大公鸡隔三岔五蹬几下筐,心里踏实了。
走了十二三里路,男人觉得好长时间大公鸡也没蹬筐了,便放下筐,撩开封布看一下。一看之下,大公鸡耷拉着头,浑身绵软,这回真呜呼了。
男人心中苦笑。这真是卖面遭风沙,卖盐遇雨雹。但他心里清楚,不能因这点小事儿给家里带来不快,特别是不能再给妻子带来压力,妻子为这个家付出得太多了。
他不但喜欢李凤举,更敬重李凤举。李凤举是他拼死拼活的动力。他家成分高,念过六年私塾。李凤举最爱看他春节时给邻居写对联的毛笔字儿,还有那教孩子练算盘时念叨的加法口诀:一六八七五、一六八七五。结婚十年,李凤举为他生了六个孩子,个个聪慧健壮。但这六张嘴也确实吃穷了他。每当看到屋内里外间炕上一到晚饭后齐刷刷地躺着六个孩子,他便有一丝悲凉涌上心来,他这个做爹的,能给孩子们将来一个什么样的前途呢?
男人站在路边,向过往人兜售刚咽了气的鸡,让人摸鸡的胸腋处:“看,还热乎着呢。”先是要两元钱,见没人买,狠狠心要一元五。心想,够赶个礼的,也算圆了面子。至于新鞋,就不想了。
在路边逢人就打招呼吆喝了半天,看过的倒有几个,全都摇头走开。男人大怒,拐起筐就往家返。他要让妻子好好做顿鸡肉,孩子们还从未吃过囫囵鸡呢。
近晌午,张伯利到了家。李凤举迎岀来,一看鸡筐沉甸甸的,就明白了三分。待张伯利进得堂屋放下筐,李凤举一拨拉盖筐的布,用手摸一下大公鸡,眼泪唰一下溢满眼眶。她知道自己男人的个性,不喜欢眼泪,于是抬起头呆看男人。只听张伯利吐出几个字:“好好做一顿鸡肉,让孩子们吃。”李凤举点点头。
正在这时,队长家四儿子尚佳声走路带风地进了院子,急三火四地说:“叔,你盘的锅灶有台不好烧,倒风,我爸让你去给看看。”
张伯利问是院子东面那台还是西面那台,尚佳声告诉是西面那台。张伯利说:“你五叔呢?我昨天和他一起盘的锅灶,没让他调理调理吗?”尚佳声拍一下厚大的手掌,提高了声音说:“咳!别提了,我五叔摆弄了差不多有半小时,老是倒烟。大师傅急了,嘴里愤愤吵吵地骂着,说再不调理好就得把切好的生肉生菜拌巴拌巴上席了。”
李凤举在一边着了急,低声说:“这种事儿你再不到场,想结冤家呀!”
张伯利一阵小跑,到队长院里看锅灶。他瞅瞅天空风向,把锅灶上插的铁炉筒的拐脚扭了扭,看还有点儿倒烟,于是把锅灶里的柴火扒岀来,把灶台连接炉筒处的一块挡风砖拆下来,往外挪了挪,再把炉筒插上,抓点和好的黄泥抹严,把扒出的柴火重新填进灶膛,再加点柴草点燃,灶膛里就像刚起动的火车,“腾腾腾”地响起来。满院的人都笑了。
这时候新媳妇已经下了马车,进了新房。尚家院子里写人情的桌子边挤满了人。张伯利借机看灶里的火,走也不是,坐也不是。瞅瞅上人情的人稀了,张伯利满面汗水,凑过去,把声音压得极低,说一句:“我上一元钱人情,圈上。”写人情的和收款的不见递钱过来,又跟一句:“多少?”张伯利涨红了脸,刚想重复,只见旁边伸过一只略显粗糙但透着红润的手,往桌上拍了五元人民币,哼了句“写账”。张伯利抬头一看,原来是大队支书。没等大队支书走开,张伯利提高声音,说了一句:“给我写账——两元!”写账的提笔写上,收款的等待张伯利上款。张伯利不动声色。待大队支书走开,只听张伯利从嗓子眼儿里挤出点儿声音:“给我圈上。”
写账人这才明白过来,这是这个贫困山区一个不成文的习俗:赶礼这天要是没钱上人情,可以先报赶礼数目,待三五天后有钱了,再付给事主。这样的情况,记账时要单列,人情账上钱数要画个圆圈,所以称“圈上”。张伯利长这四十五岁,第一次用了“圈上”,羞得坐立不安,也不知道怎样离开了写账桌,选个角落,凑合几个生人一张桌,草草吃了几口饭,溜回了家。
这两块钱,成了张伯利沉重的心思。这种欠账不同于经济借贷,没有搁下的。搁下了将成为人们的谈资和嘲笑的把柄。张伯利回到家和李凤举商议,再卖只老母鸡。李凤举不舍,说现在母鸡正是下蛋和抱窝季节,还指着这几只母鸡生蛋孵小鸡呢,还指望着卖蛋换油盐酱醋和孩子们的学费呢。想到卖点儿粮食,张伯利立即止了这个念头。家中现有的粮食恐怕到早粮下来都不够用。向亲戚和左邻右舍借借,一是原来还有欠债没还,噎死了;二是有些左邻右舍,经济条件和张家也差不多。想来想去,决定找小队会计从自己账上过50个工分——五个劳动日给队长。去年生产队每个劳动日值四毛钱,五个劳动日不就圆上脸了嘛。
队长知道了这件事,说张伯利:“大兄弟,我们老亲古邻至少也有上百年了,为这点儿小钱儿,你何必这样急?等秋收后队里结账再说。”张伯利心里合计,队长是不是担心今年劳动日拉不上四毛钱,怕吃了亏,于是便诚恳地说:“大哥别怕,如果秋天结账,一个劳动日拉不上四毛钱,我再给补上。”队长笑了,说:“你认为大哥我就这样小心眼儿?今年的劳动日说不定五六毛以上呢,你看今年庄稼苗出得多么齐!”然后顿一顿,大方地说:“放下,放下,秋后再说。”
张伯利只好暂时作罢,心中合计待度过春荒再说。但自此之后,见了队长,他多踟蹰不前,上工休息时也不愿跟大伙儿凑在一起,怕有人提到“圈上”。
一日下晚工,清河在前,清溪在后,姊弟俩兴冲冲地进得屋来。清河嚷道:“爸,妈!从今天开始我和我姐是整劳力了!”李凤举不解,接言道:“儿啊,整劳力……什么意思?”
清河说:“从今天开始,我和我姐挣满工分啦!”张伯利诧异地说:“儿,这话从哪儿讲起?”清河说:“今天快收工时,队长尚大大和生产组组长把我和我姐叫到一边,亲自宣布的。”张伯利点点头,说:“你尚大大这个人,还算公平。”
清河又说了:“待生产组组长走开,我尚大大还叮嘱我,好好表现,再有招工可优先考虑我。还说,当兵咱爷们儿也可试试。”张伯利把双手举到额顶,问清溪:“这话可是真的?”
清溪点下头。
张伯利望着屋顶,连说“老天开恩,老天开恩”。见大女儿不怎么高兴,便又问道:“大闺女,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有心思?”
清河插话道:“我姐说尚大大,再有招工和当兵的先考虑考虑我,尚大大听后说大闺女,先尽着你不尽着你弟弟,你爹妈能让吗?你一个大姑娘家,找个好婆家过日子不行吗?我姐听后立刻掉了精神,稍一缓劲儿还是连说谢谢大大。”
张伯利、李凤举俩人均不断点头。他们知道,自已的孩子教养肯定没问题,特别是大闺女,初中读书时就是班里的尖子,可惜赶上全国停课,耽误了。
清河在一边嚷道:“妈,今晚什么饭?还是粥吗?我睡到半夜就饿了。”
李风举说:“好吧,今晚我给你和你姐每人加一个熟鸡蛋。”
端午节刚过,微微的黄海季风吹拂着辽南这片丘陵,暴晒的阳光也变得温润起来。夜间的雷声刚停,布谷鸟紧一声慢一声地叫着,好像在说,再不种地我可就不管啦。小院的几株蔷薇爬上了墙头。院子里除中间留出通道外,两边都砌了小石墙,小石墙内种了些许蔬菜。张家一家老小匆匆吃过早饭,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忽然院子里踱进一个人来,背着手,上身穿着皱皱巴巴的中山服,像个干部。李凤举一端详,连叫:“哎哟,三妹夫来了。”
清溪最讨厌这个三姨父。明明是个庄稼人,一年能上半年班,余下时间,串东屯走西庄,撺掇南家豁挑北户,把事儿挑起来,再当说客,赚酒食,索礼品,人送绰号陈嘞嘞。因为跟张家沾亲,他也隔三岔五到张家来,给点儿酒,睁眼豁鼻地能从中午嘞嘞到半夜。但清溪的三姨是个好人,心里有数,劝不过男人,便暗地里修补亲友,经常隔三岔五地给张家送点米面、鸡鸭蛋或是给外甥们扯块布做件衣服什么的。因此就凭三姨这份心意,清溪对三姨父还算恭敬。
清溪向三姨父寒暄过,就要拉锄头上班,陈嘞嘞发话了:“大闺女稍等,姨父有话商量。”
清溪愣了一下,止住了脚步。张伯利忙把陈嘞嘞让到家里,招呼清溪也回家。
陈嘞嘞开门见山,说是受尚队长之托,来给他的老儿子尚佳声提媒,尚家全家都看中了张清溪。
清溪心想,真是疑神就有鬼在。刚才看陈嘞嘞那个眼神,就感觉他在打她的主意。但她太了解尚佳声了,他们小学六年级时是同班同学,尚佳声比她大两岁,小学升初中连续两年没考上,复课两年,蹲到了他们班,成了她的同班同学。一块儿考上初中,又分到了一个班。
因为大她两岁,初三时尚佳声已长成了一个大小伙子,高挑个子,浓眉大眼。若论相貌,还真的不差,唯独学习,一遇难题就发闷。有时简单的题他也粗枝大叶,毛毛愣愣,常闹笑话。白居易的《卖炭翁》,他一会儿读卖炭翁,一会儿又读成卖灰翁。反正课堂上有他,就像多了个相声演员,肯定没有打瞌睡的。但因为他父亲是生产队队长,他身上六个兄姊工作和家境又相对较好,老儿子的他,吃穿用自然相对宽裕。他经常中午带饭多半份儿,瞅人不注意送给清溪。在那个食品匮乏的年代,因为是同屯人加同学,也是因为饿,清溪一开始也没多想,根本没想到尚佳声是奔着她的俊俏模样来的,所以隔三岔五接受他的馈赠。印象最深的是,他给的食物什么都好吃,特别是包子和馒头,包子里有肉,馒头又白又有嚼头。
清溪有几个女同学挺要好的。有个叫程晓红的,特有心眼儿,她说清溪啊,尚佳声对你“有想法”了,又调皮地说:“就是将来有孩子了能笨当点儿,给十粒豆子,数半小时,能多出两粒。”大家哄的一声笑开了,清溪涨红了脸,以后无论怎么饿,尚佳声一有送东西的动向,她便迅速躲开。
但尚佳声也有长处。当时学校开“农知”课,讲德智体全面发展。班级需要造块试验田,老师选中了操场边上一块沟坎,需从半里地的山上取土。劳动课时,全班近六十个学生,要从自家带土篮子从山上挑土。一般的孩子挑个七八十斤,要歇二三气儿才能回来。尚佳声长得健壮,一担土能挑一百五六十斤,不用歇息便到沟坎。最出彩的是,别的同学得把篮子放下,撅着屁股倒土,而他,扁担依旧在肩上,两手分握土篮子梁,身子一抖,一担土就出去了,篮子里干干净净。为此,老师让他担任劳动委员。要知道,在当时这也是个响当当的班干部,不是谁都能当上的。还有,要是哪个刺头想纠缠张清溪,让尚佳声看见了,抓过来像摔小猪崽儿一样把他摔出老远。
只是,张清溪心里根本没有他。
心底里,清溪对班长向锐有点好感,但那时候,她只能把这份好感按在心底,一门心思奔着考上县高中。
初中快毕业了,准毕业生要体检,为考高中做准备。待她量完身高,体育老师手中掐个压发顶的尺,报出张清溪一米七的身高。向锐在记录填表,一听“呀”了一声,说:“哟,快有我高了。”然后主动说:“咱们背靠背量量个儿。”清溪迟疑了一下,脸有点儿红,但同学有起哄的,连声说“量量,量量”。清溪便掉转背,贴上向锐的背。谁知这一贴,清溪就感到后背一热,像炽阳,像炉火,像电流。体育老师用尺一压清溪头顶,说一声:“矮五厘米。”清溪却好像没听到,懵懂着身子没移开,惹起同学们一片哄笑。清溪连脖子都红了,慌慌张张走开。
初中一毕业,十七岁的向锐就被黑龙江省军区征为小兵。当时征兵的底限年龄是十八周岁,只有小兵可压到十六周岁。眼瞅着向锐前途无量,大队还专门为向锐开了欢送会。清溪虽然也跟着一样拍巴掌,但一句祝福的话都说不出来。
她感到从未有过地失落。
她家和向锐家不是一个屯,却相隔不过半里地,打小在一起玩大,一起上学,印象好肯定是有的。现在向锐走了一年,清溪还是憋不住了。好歹套弄了向锐的邮址,试着给向锐写了一封信,一句相思的话没说,只问部队苦不苦,能否适应。很快,向锐就回了信,也只说部队是个大学校、大熔炉,每天如饥似渴地学习锻炼。
这样互相来往了三四封信,爱情的火苗还是有点上蹿了,但互相的称呼还没改变,信的一开头仍然互称同志,倾慕的话也很含蓄,因为当时农村总有几个粗鄙的人,经常随随便便打开别人的信。
张伯利从向锐来的第一封信始,就明白女儿的心思。但他一直不搭茬,心里默默为女儿祈祷:如果女儿真嫁给向锐,那是积了八辈子的德。
又是你来我往小半年。清溪和向锐都迈进了十九岁这道门槛。清溪从发出的第五封信开始,再也不见向锐回信,一直到第十二封。这件事勾起了张家人的反思:向锐是不是怕张家成分高,影响自己的前途?
这件事也令一直在旁边冷眼瞅着的尚佳声暗暗高兴。
其实尚佳声也想借着父亲的权势去当兵或参工,但尚佳声母亲不让。说她七个孩子六个已成家,三个儿子成家后都分居,三个女儿嫁到外乡甚至是外省,她这个老儿子不能再走了。她身体多病,需要老儿子娶个好媳妇养老。尚佳声开始不同意,母亲破解说:“侍候死了我和你爹,这份家产不就是你的了吗?还用风风雨雨在外折腾吗?咱就不说别的,秋收后别人家搂个草垛,哪家不得个半月二十天的?而我们,噼里啪啦来一些帮工的,加上自家人,一两天就起个大草垛,一年的烧草就够了。”
尚佳声想想也是,但向父母提个条件,留我在家可以,你们得把张清溪办置给我做媳妇。
于是陈嘞嘞来了。
清溪听明白了陈嘞嘞的话意,没等爹妈开口,便抢着说:“三姨父抓紧回复老尚家,我才十九,我还小,现在没想这个问题。”
张伯利看看妻子,妻子审审张伯利眼光,都没有说话。陈嘞嘞有点诧异了,加重语气说:“实话说吧,我这次来,不但是受了尚家之托,也是大队支书安排来的。”
张家人立即意识到,这话不能假。别看陈嘞嘞是个二八月子庄稼人,但上蹿下跳却很有一套。特别令村人畏惧的,是他和大队支书、队长都是酒友。
但清溪不怕,心想现在婚姻自主,我们家虽然成分高点儿,但也不至于被人套上个笼头就牵走了。于是,她朝陈嘞嘞委婉地说:“三姨父,我了解尚佳声,我们是一班同学,我不喜欢尚佳声咋咋呼呼的性格,这是一;二呢,我还小,我还奔着招工或是当个民办教师呢。我自信我这文化底子,不能一辈子没有用场。”
陈嘞嘞没接茬,转而问张伯利夫妻:“当今这形势越来越不好预测,屯里挂牌子进牛棚的可不少哇,你们家就不需要找垛墙倚倚?不想找棵大树避避风雨?尚佳声这小子虽然唬了吧唧的,但你们看没看见,队里的事儿只要他一伸头,谁不得让三分?”
这话绵中藏针。张伯利脸上的肌肉痉挛了一下。他端详了一下女儿的脸色,转向陈嘞嘞,说:“这样吧,等我和你姐跟大闺女商量一下再说。”然后客气地说:“上工的哨子已经吹过了,我和孩子们先上工,你在我家坐着,让你姐给炒俩菜,中午下工时我再去供销社打点儿酒,回来陪你喝两盅。”
见陈嘞嘞点头,清溪气不打一处来,说:“三姨父,既然老尚家什么都好,我看你不如这样掂对,把你家琴子妹妹嫁给老尚家多好。”
陈嘞嘞无奈地笑了一下,说:“你这闺女心眼儿还挺多。你寻思我不想把闺女给老尚家吗?是尚佳声不要。尚佳声要参军招工,他老妈不让走。尚佳声说如若留我在家,你们得把张清溪给我办置来家当媳妇。”
张伯利全家人明白了,为什么张家人被尚家人提高了礼遇,还有动乱闹了这些时间,张伯利没受一点儿触动。
清溪在心里打了一个冷战。为了爹娘,为了身下五个弟妹,看来她此生要做一个义女了……这是一杯多么苦涩的酒!这个屯子周围已经围满了为她架设的网。有冲出去的可能吗?有,只要向锐伸出援手,她就冲岀去了。可是,八封信,已经望穿秋水啦!自古红颜多薄命,难道要算我一个吗?我毁了这副容颜怎么样?那样不是让父母终日以泪洗面吗?不行,我得找尚佳声交涉去,告诉他死了心——我不爱他,我爱向锐!但真若如此,向锐为了提干升官,不搭理我,我不还是一个苦人儿吗?以父亲那刚强的性格,一旦受辱,寻了短见,母亲怎么办?
如此权衡,至少斗争得讲策略,特别是当前,不能一口回绝了尚家。于是清溪变转了态度,对陈嘞嘞说:“既然三姨父看好了尚家,就是给外甥女儿我铺了一条幸福路。告诉尚佳声,处处看吧。”
张伯利夫妻有些诧异,但觉得也只有这样才能打发陈嘞嘞走,余下的事儿当然得从长计议。这个时候处事无远虑,暴风骤雨中是要翻船的。
陈嘞嘞兴冲冲地走了。
板栗开花了,没有向锐的消息。群山披白了,清溪仍然望来的是冬风。
这边不但尚家的兄弟姊妹像走亲戚一样地来,陈嘞嘞也来,大队支书也来。尚佳声更是表现积极。张清溪最小的九岁弟弟和玩伴们打架,被打出鼻血,尚佳声都借此表现,给人家孩子好顿教训,临了还告诉那家孩子的父母:“这是我小舅子,以后告诉你家孩子,放尊重点!
被尊宠到这种程度,首先是李凤举受不了。想起圈上的两元钱被尚家通知豁免,想起尚佳声春来播种拉犁,夏来铲趟,秋来收割,冬来搂草拾柴,不免反思,倘若这门亲事黄了,反转过来,全家特别是当家的,会不会遭祸、挨踩?于是想试探大女儿一下。谁知李凤举刚提个话头儿,清溪眼泪就下来了,说:“妈,我的婚姻无路可走了,也无路可逃了。平心而论,尚佳声对我这么好,恐怕将来也差不了,这其实不就是最好的婚姻吗?向锐是奔进步去了,我们家成分高,别拖累了人家。我们也别痴心说梦了,现实一点儿吧。一旦因为我的付出,能让我爸平安无虞,能保弟妹们一个前途,我这个长女你也算没白养。”
李凤举一把拉过女儿,抱头痛哭。
哭了一会儿,李凤举怕被张伯利看见伤心,又怕被左邻右舍看见惹是非,便对清溪说:“通知你三姨父,把这门亲事先定下来吧。”
陈嘞嘞来了,说:“看家就省了吧,都在一个屯。定亲肯定是要体面的。有我这个三姨父在,他老尚家也休想慢待我们一分一毫!”
定亲那天,尚家五间海青房窗明几净,院子中间通道铺了红砖。尚佳声一身新衣,满脸开心。清溪被请到西屋炕上,尚佳声三对哥嫂先来赠礼,每个嫂子都掏出十元人民币。接着是尚佳声的二姐、三姐,每人用红手绢包了一小沓人民币,当众打开亮相。尚佳声大姐最后出场,是从哈尔滨赶回来的,亮出一沓漂亮的丝绸被面和一床乡下罕见的毛毯——显然十元二十元是买不下来的。最后是媒人陈嘞嘞提过一个红布包裹,跟尚佳声母亲一块儿过来。陈嘞嘞打开包裏,里面有二百元钱、四床被面。
结婚的日子定了:冬月初八。
亲邻正在艳羡之时,乡邮递员来了,递过一封信。清溪一看那专用的军人信封和熟悉的字迹,当着尚佳声的面儿,根本没打开信封,三把两把,攥巴攥巴就把信封扔到地上。清溪二妹站在旁边,一看姐姐没有把信撕碎,立即明白了,姐姐是示意她看个究竟,于是立即拾起攒巴的信,装作扔垃圾,跑到无人的地方抚平信封,趁尚佳声忙着待客,把信偷偷塞给姐姐。
清溪一字一句读着:
张清溪同志你好!
近期中苏边境气氛紧张,我们部队被封闭潜伏在山林,只准进不准岀,更谈不上写信了。近日我奉命带几个人回原营地采购给养,得见你给我的八封信。看后我热血沸腾。我心中只有你。但限于时间,不能畅所欲言。希望你保重、进步。
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此致
敬礼
你的同志向锐
作者简介>>>>
王嗣元,1952年生,大专文化,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庄河记忆》编委。著有小说、散文、诗词、考据等文集三部,计四十余万字。
[责任编辑 陈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