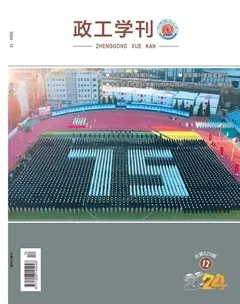读书常“反刍” 记忆勤“打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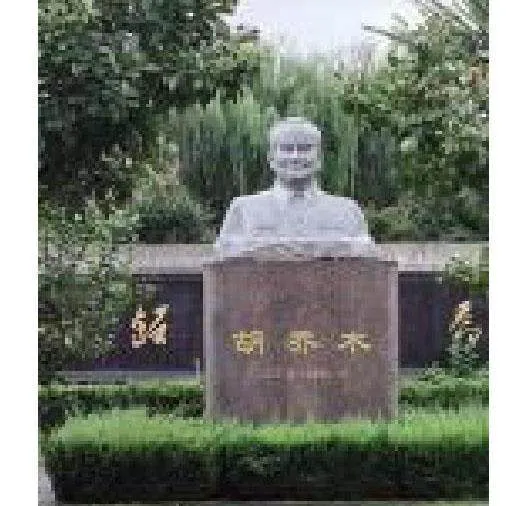
胡乔木之所以被称为“党内第一支笔”,与他科学有效的读书方法不无关系,他常说:“读书不能盲目图快,不能囫囵吞枣,要像牛吃草一样,要反刍。要思考书中的观点是怎么得出来的,有些什么新的材料,这些新材料是从哪里来的,可不可靠,等等。经过这么一番思考,等于给你的记忆打了一个‘结’。思考得越深越细,那个‘结’打得就越大越牢,就不容易丢失了。”
所谓“打结”,本质上是思想的参悟,是书本知识经过思考改造进而内化为记忆的过程。记忆具有由外而内的指向性,“记”包括识记和保持,“忆”包括回忆和再认。只“记”不“忆”得到的往往是“学而不化”的知识,顶多算是“熟知非真知”,缺乏应有的实践指导价值;真正“内化于己”的知识,绝非死记硬背式的“学富五车”,而是深思熟虑后的“才高八斗”,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经过了学思参悟的吸收过程。
胡乔木提倡的“反刍式打结”法,就是主动将学过的知识特别是其中晦涩难懂的部分,返回头脑中进行再咀嚼、再消化、再吸收,以期化“熟知”为“真知”。艾宾浩斯遗忘曲线表明,学习的结束就意味着遗忘的开始,对抗遗忘不能只靠“记”,更有效的办法是“忆”。“反刍”是“记”基础上的“忆”,通过回忆把书本的知识变成自己的、通过厘清把碎片的认识变成贯通的、通过再认把高深的东西变成易懂的,是一个认知内化、深化、固化的再造过程,最终越打越大形成牢固的“记忆之结”,甚至是联“结”成“网”的知识体系。
“反刍”除了具有内化理解的功效外,还是将书本知识与思维创造一体融合的创新过程。如果说发现新知实现了0到1的突破创新,那么“反刍”则是“私人定制”式的重识重塑,实现了“1到N”的发展求新,抑或是“1+1>2”的迭代创新。正如“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相对于固定的知识,“反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化学反应”,打下的“记忆之结”也是千人千面、各不相同;即便是同一人再读同一本书,也能“温故而知新”催生“新结”,毛泽东对《共产党宣言》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每次都有新启发。
知识无止境,认知亦无止境。《资本论》第一版深奥难懂,很多读者是半途而废,对此列宁指出:“想认真考察和独立领会它的人,都必须再三研究,反复探讨,从各方面思考,才能获得明白透彻的了解。”正是获取真知的无限性、艰难性,决定了“打结”的长期性、反复性,而且往往是一番“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思想征程。因此,“书”需要反复读、“理”需要反复“嚼”、“结”需要反复“打”,特别是理论山头更需要反复“攻”,永远不要指望一劳永逸。
“不深思则不能造于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学而不思,不懂得咀嚼和反刍,就会成为“书云亦云”的书呆子;思而不学,缺乏知识内核支撑的“结”,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造于道”是读书的重要旨归,而将学与思紧密结合起来是其必经之路。“反刍式打结”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有效“读书通达”之法,以常“反刍”和勤“打结”,提供了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桥或船”,值得学习和借鉴。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
中部战区政治工作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