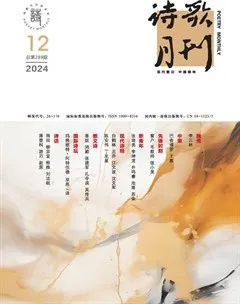《诗歌报》 创刊40周年随感
灰马
巨石般的灰马 和一个
动荡之后的年代 休斯走远了
草原开满野花
云一般的灰马 呼着气
一动也不动 远离马群的
灰马 低垂着头 鬃毛
和后蹄 冒着热气
休斯走远了 灰马
它忍受着 它的沉闷和灰暗
在草原摧开野花
这是我首次在《诗歌报月刊》上发表的一组作品中的一首,也是我平生的第一次发表。时间是1994年7月。时隔三十年再读此诗,其中的比兴、寓意和感受在潮打空城、时移世变后似乎愈见清晰。
我最初接触到《诗歌报》,大概是1989年。那时《诗歌报》还是一张纸质、印刷都较普通的大开的报纸。在此之前,我学诗已有两年。八十年代中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过一套手掌大小的“外国名诗”系列,其中有聂鲁达的《诗与颂歌》、惠特曼的《我在梦里梦见》、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庞德等人的《邻笛集》等等。那一年我十六岁,很偶然地在一位街坊家的旧房子里捡到其中的几本。第一次读到《恶之花》,那种震颤和惊恐的感觉至今难忘。一直把郭小川、贺敬之、郭沫若、何其芳等视为诗歌写作之圭臬的乡村少年,做梦都没有想到过,诗歌还能这样写。在读到那本诗集的那一刻,我已经被彻底改变了,生命中的“另一个我”被唤醒了!
但是最初接触到西方现代派和后现代文学,对我来说,在阅读和理解上还是非常艰难的。如兰波、庞德、布勒东、林赛、金斯伯格、冈恩和艾略特等的一些诗,在很长时间里我都一直理解不了,“达达”“低语派”“深层意象”“表现主义”等,也让我备尝艰辛和苦恼。而我尝试着仿写的那些习作,对于当时一般人所受过的语文教育无疑具有极大的颠覆性,被人斥为“怪作”。直到接触到《诗歌报》,意外地发现,竟然还有很多人像我那样用“胸口碎大石”的方式写诗,不禁惊喜莫名。在苦心孤诣地研读了几期《诗歌报》之后,我的诗歌也迅速产生了变化,很快就跳出了波德莱尔和李金发式的生硬的写作,向先验性和体验性的现代诗写作靠拢。那是个汉语新诗对西方现代诗全面学习、深度高仿和西方诗歌概念被汉语诗学不断进行多层次解析、转注、引用和重命名的时代,年轻一代的诗人趋之若鹜,形成了一股蔚为大观的潮流,《诗歌报》及《诗歌报月刊》在其中所起到的推波助澜和写作技艺示范的功绩,在今天看来怎么评价都不过分。从《诗歌报》到《诗歌报月刊》,在很多诗人的记忆里,那可能是写作生涯中最富有热情和活力、最值得回忆的十多年,一代诗人从这本以开放和探索而著称的刊物登上诗坛,并由此而成就了自己的写作。
毫不夸张地说,那个年代,没有在《诗歌报》或《诗歌报月刊》上发表过作品的诗人,在心理上是很难自洽的。从1994至1998年,我在《诗歌报月刊》的“挑战者第一千零一个”“探索诗之页”“十支铜号”等栏目先后发表过七八次作品,每一次发表,对我的生活和精神,都是极具穿透力的照耀。那时候我在鄂西北的一间乡村工厂上班,先后做过司炉工、技术员、车间主任、劳资科科长、统计科科长、厂办主任等,直到进入新世纪,工厂改制,工人买断工龄,我才选择离开。对于当时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我在1997年6月份《诗歌报月刊》上发表的一首诗中曾有表现:
重现的时光
冬夜美丽 黑暗中的事物
越简单越好 烛光轻曳
另一世界陌生的脸
多么柔和 亲切
雪地上 银色的树
仿佛是大地的馈赠
风在很远的地方
吹裂镜子 孤独的心
被微暗的盆火慰抚
感受着 命运瞬间的宁静和真实。
没有诗歌 没有音乐
乡村的冬夜在一个年代的边缘
熠熠闪光 而从疏朗的杨树林子里
雪使被追忆的生活 和寂暗的北方大地
渐渐开阔 明亮
鄂西北的冬天,干燥,多雪,工厂所处的位置在秦岭与大巴山交界处的二高山地带上,“万山重四塞”,有霜期比江汉平原至少要长一个月,每年的腊月,还常常会因大雪封山而断绝交通。每到下雪的时候,厂里总是显得特别冷,车间里,机器的轰鸣声昼夜不息,千疮百孔的输气管道泄露出的白色蒸汽如大雾垂天。在这里躲避寒冷的蛾子到处乱飞,车间外是厚厚的积雪,一脚踩下去,可以感觉到脚底的冷和脚背上的冷几乎是同时到达的。在这样下雪的晚上,我无处可去,只能守着一盆炭火,读书,写诗,或冥想。“没有诗歌/没有音乐/乡村的冬夜在一个年代的边缘/熠熠闪光”,这种感觉和体味,澄静而使人内心虚弱。我的许多诗作,都是在这样下雪的夜晚写出来的。
我在那里工作了十二年,其中有八年的时间,我一直住在工厂里。我曾经在给一位朋友的书信中,把那八年的生活描述为一种“没有生活的生活”。那是一个孤立、封闭的环境。没有娱乐、没有朋友、没有新闻,甚至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除了食堂里永远缺盐少油的寡淡饭食。在那种土鸡瓦狗似的生活中,我唯一的乐趣就是读书和写诗。我在那里很专注地读过很多书。或者这样说,那八年里,一切稍具书刊外形的印刷物,我都会搜罗到自己的房间里,不分青红皂白地猛啃,包括《资本论》、《医古文》、繁体字号纤细如蚊足的《春秋三传》和李贽的《史纲评要》。直到我得到了一本奥登的《在战争时期》,才猛然意识到阅读要有选择,以及大量的阅读对写作甚至是有害的。在这样的闭塞和贫乏中,苦闷和压抑很难形容,《诗歌报月刊》几乎成了我唯一的精神出路和与外部世界对话的途径。
在自媒体和各种资讯平台空前发达的今天,似乎很难理解一个诗人会对一本诗歌刊物产生不可名状的精神寄托,当然更难以描述贫困的心灵对诗的追求和渴望。整个九十年代,我几乎只给《诗歌报月刊》寄诗稿,因为信息闭塞,我知道的诗歌刊物不多,更重要的是,当时只有《诗歌报月刊》认同我的写作,给予发表和交流的机会。那时候,每到《诗歌报月刊》出刊的日子,无论炎暑或风雪蔽日,我都会骑着自行车狂奔到县城里去购买新刊。1996年第一期《诗歌报月刊》的“挑战者第一千零一个”栏目发表了我的一组诗,但这一期刊物因大雪封山邮路不通,直到临近春节时才送到县城,邮局零售柜台的承包人是我同事的表妹,打电话让我去取。我的自行车坏了,就悄悄把厂里的三轮车开出来,结果因技术太差,开出工厂外的陡坡时,连车带人掉进了农户家的猪圈里,事后不仅要赔猪,还要请泥瓦匠来砌猪圈。很多年后,我回乡偶遇那位农户,他居然还能一眼认出我,攀谈中竟然说我当年赔他猪的钱没赔够时价。我大笑之余,当即拿出一条烟送给他。
《诗歌报月刊》发行量最高时,据说超过了十万份,对于文学类期刊来说,这是个很惊人的数字,由此也可见,那真是个“人人皆怀李杜心,人人争唱饮水词”的诗歌年代。九十年代中后期,《诗歌报月刊》先后两次停刊。前一次停刊前夕,我曾收到主编蒋维扬先生的一封来信,字里行间的无奈和辛酸,尤其让我记忆深刻。后一次停刊时,中国诗坛即将迎来乱云飞渡、泥沙俱下的网络论坛时代。从一定意义上说,《诗歌报月刊》的停办,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到现今的“高级的平庸期”。但是纵观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到新世纪以来二十多年的现代诗的发展形态,可见此种现状的出现,多半是由诗歌艺术的发展规律决定的。一个大潮激岸的时代过后,必将迎来“潮平两岸阔”的庸常期。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是:一方面诗歌在创作上表荣内枯,无论是诗歌写作人群数量、诗歌作品的庞杂浩繁,还是对诗歌创作边界的拓宽延伸,都是前所未有的;另一方面,诗歌在创新和突破上,却处于停滞和为自身所局限,即表象的宽阔明亮,掩盖了中心的幽暗。在中外诗歌史上,这样的时期曾经多次出现过,如浪漫主义盛行的末期,诗歌艺术也是停滞的,一种写作方式和思想潮流走到了极致,几乎没有办法再向前推进和演化,这时候现代派出现了;现代主义诗歌在艾略特之后趋于僵化和泛滥,实验派、自白派、新超现实主义等便应时而生;中国古代四言诗发展到曹魏时期,几乎无路可走了,这个时候五言诗和七言诗出现了,“开窗放入大江来”。诗歌艺术自有其发展之道,这是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的。
1986年,《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至今仍为诗坛所称道,1994年《诗歌报月刊》举办的“‘临工奖’中国当代诗坛跨世纪实力诗人集结”亦可说是对大展的踵事增华。我的诗《斯大林格勒思想曲》在其中获得了金奖。颁奖活动和《诗歌报》创刊10周年纪念会在黄山举行。我收到邀请函,兴奋得难以自已,临近会前又接到蒋维扬先生亲自打来电话确认能不能到会。但当时我刚刚做了车间主任,恰逢冬季前设备大检修,难以脱身,错过了这场盛会。颁奖会举办的当天,我专门跑到县城拍了一封祝贺电报去,也算是聊慰渴怀了。
《斯大林格勒思想曲》获奖对我来说是个意外之喜。以《诗歌报月刊》当时在诗坛的声誉之隆,孤陋如我只有参与的勇气,哪敢稍存获奖之念?但事实证明,“临工奖”确实做到了蒋维扬先生在大赛《侧记》中说的“一次对公正原则的坚守”。我的获奖作品抄录如下:
斯大林格勒思想曲
斯大林格勒的树倒了
在打击到来之前 鸟的双翅
扑动着一个预兆
斯大林格勒的树倒了
金子般的桦林和马群
从大地上消失了
整个俄罗斯的冬天一片寂静 明亮
斧子丢在雪地里 而音乐升起
铁在闪光
铁在斧子深处 灼伤诗歌和灵魂
铁是冷酷的 一片黑沉沉的树
尸体般地倒着。而音乐升起
音乐的曲线 凝重 深沉
远处是无人地带 铁丝网上的刺
像死亡 逼向虚空
斯大林格勒的树倒了
灰色的天空 雪还在下
斧子丢在雪地里
诗人和整个世界 都在等待
或忍耐
三十年后再读此诗,亦让我慨叹无尽。正所谓“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赵原,现居深圳。诗人,中国作协会员,“小说诗”的倡导者。著有诗集《晨曲和叙事诗》《我的灰蛾已盯上了最美的那个》《世上最好的牙都在他嘴里》等,中短篇小说集《我们不得不重新回到大街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