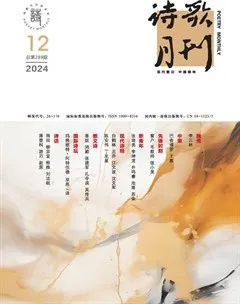新时期以来诗歌新潮的引领者
转眼之间,《诗歌报》就创刊40周年了。无论是对于一个人,还是一份报纸(刊物),四十年都是一个值得回顾、总结、展望的时间节点。四十年来,我一直和这份刊物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关系,有很多值得回忆的过往。
知道《诗歌报》创刊是我大二的时候,虽然是在外语系读书,但恰好遇到吕进老师给我们开设“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课程。这是当年西南师范大学外语系(现在的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的王牌课程,吕进老师讲课娓娓道来,深入浅出,尤其是他对新诗的解读,让我们大开眼界,激活了很多同学对文学的兴趣。我来自偏远的山村,过去读书基本上是以课本为主,对课本之外的作品没有系统的涉猎和积累。但是,一个经历过贫困、自卑、奋斗的学生,很多时候是需要倾诉的,而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用文字把自己的所见所思写下来,因此从小就有了对文字、文学的喜爱。恰好在吕进老师上课期间,我得到了《诗歌报》创刊的消息。那是新时期诗歌最热闹的时期,全社会都对诗人、诗歌充满了敬畏,大学校园更是诗歌生长的沃土。于是我从1985年1月起订阅了刚刚诞生的《诗歌报》。
《诗歌报》是我有生以来自费订阅的第一份报刊。在读中学的时候,吃饭都非常困难,加上学习压力很大,几乎没有余钱订阅报刊。我决定订阅《诗歌报》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当然是因为吕进老师的课,使我对诗歌突然有了兴趣;其次是因为报纸所宣称的“探索性”比较新颖;最后是因为它的价格便宜,每月两期只要三角钱,不会影响到读书期间的生计。
每期收到报纸,我都会认真阅读。红色报头,对开四版,每一版都有值得关注的内容。当时没有网络,没有手机,几乎所有的信息都只能从报刊、图书上获取。《诗歌报》以发表作品为主,尤其是青年诗人的作品,有时还有外国诗人的作品,同时也有评论、诗坛信息等等,几乎每一篇(首)作品都可以给我带来新鲜的感觉,而且知道了诗坛上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我当时对诗歌的了解还不多,理解很肤浅,对很多作品、理论文章并不是都能够读懂。但我坚持读,读不懂也要读,慢慢消化,慢慢积累,逐渐了解了很多诗人和评论家的名字,更了解到当时的诗歌和过去的诗歌有很大的不同。“86诗歌大展”一下子推出那么多流派和诗人,有不少作品是我难以读懂的,也有一些观点惊世骇俗、难以马上消化和接受,但它让我们对当时诗坛的热闹、丰富和人们求新求变的心理有了比较直观的了解,也切实感受到诗坛多元化格局的逐渐形成。不断“突破”与“新变”是那个时代诗歌发展的潮流,虽然有很多所谓的“流派”渐渐销声匿迹,但大胆的尝试为新诗探索打开了创新的大门,有的是提供了新的路径,有的则告诉我们“此路不通”。
那真是一个让人怀念的诗歌时代,而《诗歌报》在新时期以来的诗歌观念、艺术技巧的新变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对于这样一个引领潮流的阵地,每个爱好诗歌的人肯定都希望能够在它的版面留下自己的名字。我也是,而且运气比较好。1987年秋天开始,我有幸开始在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攻读中国各体文学(后来调整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研究方向是“现代诗歌理论与创作”,和诗歌有了更密切的接触。1987年深秋的时候,吕进老师委托我以中国新诗研究所的名义对1987年的诗歌创作、研究、发表、出版等话题开展一次问卷调查。问卷是我起草的,但是当时没有网络、手机、电子邮件,更别说投票软件了。我们遴选了几百位老中青诗人、评论家,以邮寄的方式将油印的问卷寄给他们。收到问卷的诗人、评论家都非常热情,绝大多数都回信了。我记得,除了中国新诗研究所的师生,还有李瑛、纪鹏、杨山、白航、刘湛秋、柯原、袁忠岳、朱先树、杨光治、张新泉及《诗歌报》的蒋维扬等等,以及一些年轻的诗人。他们不但要填写问卷,还要自己贴邮费寄回问卷,我为他们的热情支持深深感动。在认真整理问卷之后,我在年底写出了一份调查综述,寄给了蒋维扬先生,结果他很快就在1988年1月6日的《诗歌报》(总第80期)头版刊发了这篇题为《一九八七年诗坛现状调查综述》的文稿。几个月后,1988年8月出版的台湾《创世纪》诗刊第73、74期合刊全文转载这篇文章。虽然这只是根据问卷整理的综述,但收到报纸的时候,我还是非常开心。能够在《诗歌报》留下自己的名字,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也是对我的极大鼓励。
我统计了一下,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还断断续续在这份刊物发表了另外的五篇文章,分别是发表于《诗歌报》1989年11月21日(总第125期)的《新诗坛:久分必合》;发表于《诗歌报月刊》1992年第3期的《新诗:面对跨世纪的挑战》(后收入邹建军、熊国华主编的《世纪末的沉思》,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发表于《诗歌月刊》2011年第10期的《那高大的身影依然清晰——怀念许世旭先生》;发表于《诗歌月刊》2012年第10期的《诗人玛莎》;发表于《诗歌月刊》2018年第9期的《诗意生活的守望与追寻——傅荣生诗歌散论》(与我的硕士生李云超合作)。这些文章的数量并不算多,而且在职称评审和完成工作任务中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但我个人却非常看重,它们不但记录了我对诗歌的关注和思考,记录了我和《诗歌报》的缘分,而且是我坚持学诗的见证。
在最初和《诗歌报》交往的时候,我还是学生,只是通过信件和蒋维扬先生有过联系。直到现在,我也只是乘坐火车时路过安徽,还没有机会踏上自己一直向往的那片土地,更没有拜访过合肥的宿州路九号。我和《诗歌报》的第一次直接交往是1997年10月。当年9月,我开始在苏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恰好遇到《诗歌报月刊》组织的第四届“金秋诗会”在苏州举行,可能是通过我的老师范培松教授及小海兄的介绍,我应邀参加了那次活动。参加会议的十几位年轻诗人,以前只是听说过他们的名字,读过他们的作品,大多数都是第一次见面。由于时间过去很久,我只记得其中部分诗人的名字。后来在汗漫兄的一篇文章中读到了相关记载,了解到参加活动的大致有韩东、小海、沈苇、汗漫、吴承俊、车前子、雪松、黑陶、庞培、森子、叶辉、叶玉琳、长岛、蒋登科等。汗漫简单记录了当时的一些情况:“瘦高得像一面旗帜的乔延凤主编,引领我们去寒山寺和虎丘游荡,在苏州农业学校招待所谈诗。”这恰好是诗会的几个活动地点。我和车前子、小海比较熟,在活动中又和沈苇、叶玉琳等诗友交流较多,直到现在我们还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我记得当时对沈苇去新疆表示了很大的兴趣和支持,预测他可以写出优秀的作品,因为以江南的细腻打量大漠的苍茫,可以获得不同的体验。我后来也写过关于小海、叶玉琳的诗歌评论。我感觉,《诗歌报》关注年轻诗人的成长是一个正确的抉择,因为年轻诗人感觉敏锐、思维独立,具有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相互之间的碰撞,可以激活潜藏的创造力。
四十年来,《诗歌报》经历过多次风风雨雨,由报纸改为刊物,甚至经历过停刊。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份刊物参与并见证了当代新诗的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诗歌报》的出现,新时期以来诗歌发展肯定不会停止,但或许会是另外一种面貌。当然,历史不能假设,《诗歌报》上的作品、论文、信息已经成为我们回望和打量新时期以来诗歌创作、研究、活动的重要史料。记得在几年前,有人向我打听重庆新诗学会的成立情况。成立于1986年7月18日的重庆新诗学会可能是全国最早成立的此类学会之一,我当时确实在重庆,而且《银河系》诗刊创刊的时候,我乘坐了几个小时的公交车,亲自将吕进先生撰写的《发刊弁言》手稿送给杨山先生。但我当时还是学生,对重庆新诗学会的成立情况确实不太了解。恰好在这个时候,万龙生先生发来了一条消息,这个消息刊发在1986年8月6日的《诗歌报》,题目叫《重庆成立新诗学会》,记录了学会成立的时间、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等信息。虽然只是短短的几句话,而且将副会长“吕进”误植为“吴进”,但它却让我们获得一些准确的历史信息,解决了困扰我们很长时间的问题。即使是误植的名字,也可以成为一个有趣的话题。
几十年来,我和《诗歌报》的联系其实很少,只是在1997年见到过乔延凤先生,在他退休之后又在其他场合见过几次,也见过后来的几任《诗歌月刊》的负责人,我们每次见面,都会谈到《诗歌报》及其在中国当代新诗发展中所做出的贡献。遗憾的是,一直关心、支持我的蒋维扬先生,我却一直没有见过面。对于《诗歌报》来说,我所发表的几篇小小的文字,完全无足轻重。但是换一个角度看,情况就不一样了,从读者到作者,《诗歌报》带给我的激励是很大的。它培养了我对诗歌的爱好,对诗歌研究的长期坚持,对诗歌多元化的思考,对艺术创新的关注。
经过几十年的锤炼、积淀,四十岁的《诗歌报》(《诗歌月刊》)走过了一条坎坷的路,也走出了一条辉煌的路。如今它更加成熟了,或许会少一些年轻时的张狂、锐气,但它已经有了自己的传统和风格,走进了具有底气、尚有梦想和潜力的时期。因此,作为一个诗爱者,在祝贺《诗歌报》不惑之龄的同时,我相信,未来的刊物一定会沿着自己的传统和宗旨,坚守艺术良知、创新理念,为新诗艺术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蒋登科,1965年生,四川巴中人。文学博士,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诗歌学会常务理事等,有新诗论著十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