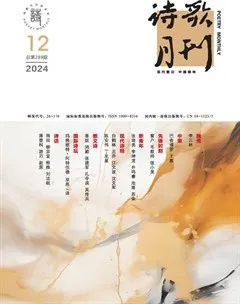与 《诗歌报》 对弈
1987年,我开始定下心,要成为一名诗人,而非一个普通的诗歌爱好者。那时发表作品只有在纸质报刊,发表之难现在难以想象。 1987年我在《小星星》上发表过一首儿童诗;同一年收到《山西文学》的潞潞亲笔写给我的一封采用通知,待发的诗名为《瓶》,这首诗也曾得到当时在湖北黄石教书的诗人程光炜的肯定。虽然这首《瓶》后来没有在《山西文学》刊发,但那封笔迹飘逸的短函对我的信心树立和激情激发还是很有作用的。
而《诗歌报》就是在1986年左右进入我眼帘的。当年我是工科毕业生,与文坛、诗坛不沾边,平时接触到的诗界的信息很有限。我最初读到《诗歌报》来自两个渠道,一个是来自湖北黄石的诗人、中学语文老师何建中;另一个是来自当时在武大的一位中学同学,他寄给我一些《诗歌报》。1988年,我到湖北荆州工作后就是自己订阅来读了。
1986年我开始写诗后,发表的机会不多,我曾拜访过黄石当地的诗人和《散花》编辑部。我还比较向往《黄石日报》副刊,但都没有得到发表的机会。工作调动到湖北的沙市后,平素只是在《沙市报》副刊(主持人赵宗泉)和《沙市工人报》副刊(责编郑泽华)刊发过诗歌。看到变成铅字的分行文字,对保持旺盛的写作热情还是很有作用的。特别是这种报纸,在当地的发行和阅读的密度是非常可观的,我也因此结交到很多当地文朋诗友,还积累了点小名气。
1989年1月,我突然看《诗歌报》某版左上角有我的名字,我难以置信地定睛一看,有《云笺》《隔岸》两首,确实是我的诗,姓名前还有我当时工作的学校名称。那份惊喜自不待言,是从未有过的深深的满足感。那是一个校园专版,栏头是通栏“因诗思飞扬,校园一株株青春树灿烂无比”的栏头语。这次发表,虽然只是两首质地偏软、偏青春抒情的小诗,却有一石激起千层浪的传播效应。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一年内收到全国各地30多封读者来信和明信片,其中有些是有偿征稿,约一半是读者和诗人写来的对诗作的读后感想。这说明当时《诗歌报》的发行量之大和读者深度阅读的情状。当时全国的诗人和诗歌读者交流渠道有限,这种刊发校园诗人通联地址的专版,算是对年轻的校园诗人的福利。那年我刚过24岁。进入九十年代,《诗歌报》改版为杂志,还很贴心地在每页下端安排了“缪斯信箱”,即刊发无名作者的几句诗或几句关于诗的言论及其通联地址。这样,让接近发表水平的爱好者也能“准发表”,刊载地址便于爱好者们相互联系——那个年代,按照地址寻找同好的情况并不罕见,特别是对于居住在同一个地区的诗爱者来说。
那之后几年间我在《青年文学家》《诗神》《星星》《西北军事文学》《飞天》等报刊发了诗作,其中有些是组诗。那时刊物时兴办诗歌大奖赛,可能是为了避免无效稿件太多,或可能为弥补一些比赛活动的费用,参加比赛需要作者随参赛作品邮寄5到8元的费用,我也积极参赛,多有斩获。参赛规则是匿名评选,获奖名单时常有冷门作者出现,感觉那些年评选的公正性有一定的保证,是无名诗人传播作品和提高知名度的一个有效途径。我在那几年陆续获得十几次诗歌奖。其中最为重要的当数1994年获得的《诗歌报月刊》中国当代诗坛跨世纪实力诗人“临工奖”金奖。这是曾经震动诗坛的《诗歌报》首届“探索诗”“爱情诗”大奖赛的延续,那次大赛把大部分写作具有先锋性的民间诗人都吸引过来,使其获得显著的成名和传播效应。这次“临工奖”的终评委我记得是陈超先生领衔,虽然不能与《诗歌报》的首届“双奖”大赛的轰动性相比,但也是令人瞩目的。我在学校门房接到在黄山举办颁奖仪式的通知时正值暑假初期,我展开打印的通知时的狂喜至今还记得,这是得到其他奖时没有过的。据1994年第9期获奖专号披露,那届参加比赛的有效作品有3888件,近两万首,《诗歌报》包括主编在内的六位编辑交换审阅,达到三位编辑同时签名推荐的才进入终评环节。终评稿件邮寄给六位外地评委打分。在这种严格认真的程序下,能够入选,看来也是很有难度的。当然还有运气成分,要知道,那时我与这份诗刊的主编、编辑平素全无私交,估计绝大多数作者也是这样。那次金奖的奖金是500元。
那次黄山颁奖会之行,也有一些有意思的记忆。当时我从安庆转车,中途看到一位书生似的同车男子,心里估摸着他或许也是参加颁奖会的,结果到了报到点,发现他还真是:是安庆诗人、评论家李凯霆(苍耳)。在会上见到了久仰的谢冕先生、蒋维扬(城父)先生和《诗歌报》编辑,以及我的同龄诗人祝凤鸣等,还有大奖赛资助人、诗人临工夫妇。看到蒋先生额头上飘出一缕白发,听说他不久前从阳台上摔下楼来,伤了元气。那次还第一次有幸遇到安徽的老诗人公刘先生,在看黄山脚下的牌坊群时,他略带愤慨地指着牌坊说,这些都是压迫妇女的东西。我们一起爬黄山时,他还亲切地问我,是否父亲曾经是诗人?我有点受宠若惊地说不是。想不到先生还认真看了我的获奖作品。我的获奖诗作是《被遗忘的人》和《为父亲生日所作》,在后一首中我写道:“想到父亲当年的英姿/遥远,非常非常遥远/飘摇和不安/身穿国防绿 唱着歌/他平生的幸福就那样来临……”可见,那时我已经懂得叙述中的虚构了,比起1989年《云笺》时期诗作的意识更有深度和广度,语感也更有张力和弹性。谢冕先生精神矍铄,爬山不在话下,有健步如飞的感觉。那次同去领奖的诗人有金奖获得者叶匡政、余怒、陈朝华,还有曾园、荣荣等。获得这种奖励的意义,对于那个时期写作信心的建立还是很大的。
也还是1994年,第6期《诗歌报月刊》刊发了我的一首34行的诗《路过》,那期只发了这一首诗,还不是重点栏目,责编是城父,也登了作者地址。这首诗我一度有点自我欣赏,但这种诗比较多,是一阵一阵的,所以也不以为意。但这首诗自从刊发以后,30年来陆续有人和我说对其印象深刻。当年,就有陌生诗友因为这首诗到我所在的学校拜访过我。我那时就为《诗歌报月刊》阅读传播效应惊叹。梁小静博士的论文《诗歌的语言激情及主题特征——论析刘洁岷的诗》(《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用了一千多字研析了这首诗:“刘洁岷在《路过》中实现的正是:时间、地理、空间、主体的非线性、可逆性,最后,这个凝视主体‘我’也可逆了,他在循环中成为被凝视的对象。”诗人、小说家宋尾2023年在评论文章《身体周围长出故事而你载它们走到街上》里几度提到此诗:“一共23种景物,还有10个具体人物,以及一些笼统的面目。”还有陈培浩教授2024年的评论文章《与诗神的语言契约——读刘洁岷的诗》里专节探讨了这首诗,并且数出此诗为34行。虽然这首诗诚如培浩所言“尚称不上完美”,但它长达几十年为读者和专业学者所重视,让我对初发在《诗歌报》这首我本不以为意的诗作产生了一种陌生的迷惑感,好像送给别人的儿子在异国他乡被培养为令人瞩目的选手。
再一个值得回顾和感恩的是,我在1997年参加《诗歌报月刊》爱情诗大奖赛并有幸获得特等奖。当时,主持《诗歌报月刊》的已是乔延凤先生。 “特等奖”是在一、二、三等奖之上的一个奖励,名额只有一个,是名副其实的诗赛冠军。诗赛的一等奖获得者是女诗人沈杰和扶桑。我的获奖诗歌是百余行的《从一个句子推算三个关键的词》。那时,“关键词”尚未开始流行,就像后来的“内卷”一样,开始出现时还蛮陌生的。所以在杭州领奖时杭州的爱情诗人董培伦老师还专门问了我这诗歌题目是什么意思。那一届特等奖的奖金是1200元,我在西湖浏览时在旅游纪念品店给每位参会者买了一块丝绸刺绣的手帕,回来后发现数量不够,可能庞余亮等一两个诗人没有送。那时的余亮比较沉默内敛,我们分开后还彼此通了几年信,其间他写出了组诗《底层生活》,我大加夸赞了一番,并收入我和诗人哑君编的民刊《声样》里。同样,那时“底层”还不是个热词。
1997年9月底,湖北诗人哑君个人出资,联合省作协,邀请《诗歌报月刊》乔延凤、祝凤鸣、叶匡政一行,在武汉举办了一个三十人规模的诗歌研讨会,会后组织部分参会诗人到神农架采风。当时除南野、潘能军外,湖北的许多新锐诗人都参加了这次围绕《诗歌报月刊》的聚会,记得有热衷于办民刊的广州诗人江城和邱晴,武汉诗人刘益善、剑男、沉河、张执浩、李建春、阿毛,后来主办民刊《后天》的黄石诗人江雪、向天笑,荆州诗人高柳,刚大学毕业不久的松滋诗人拉家渡等。那时,青年诗人参加这种诗歌研讨会并结识诗歌刊物编辑的机会并不多。我记得对《诗歌报》《诗歌报月刊》的投稿就是寄给编辑部的,一直没有与具体哪个编辑建立私下交往关系。该刊兼职编辑叶匡政是1994年在黄山认识的,虽有信函来往,但好像也没有向他本人投过稿。在那个没有网络的年代,像这种刊物编辑组团深入外省进行诗歌活动,对当地的诗歌作者开阔眼界和激励创作热情还是很有帮助的。去神农架期间,大家吃住待遇都一样,其乐融融。
那些年的前前后后,《诗歌报月刊》陆续发表了我的诗作《站在栅栏后的女人》(1992)、《远大前程》(组诗选二,1993年)、《新词》(1997)、《越战失踪者》(外一首,1997年)。我记得我在《诗歌报月刊》的民刊专号上发表过的《父亲来到我们中间》,这首诗也有一定的生命力。去年张桃洲教授在一篇学术论文集的序言里引用了这首诗,今年陈培浩教授也在引用全诗后进行了深度评论。2021年5月,诗学学者周瓒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查阅剪报资料时看到了我的诗论习作《后90年代诗歌批评:感性》,这篇刊发于《诗歌报月刊》1998年的文章论算是我早期最成型的一篇诗论,也是投寄给编辑部并得以刊发的自由来稿。
在《诗歌月刊》时期,我投寄了作于1997年的近两百行的长诗《乘飞船远行》并被刊发,加之那个时代网络论坛兴起,纸质刊物的影响力被缩小并均分化,所以我是隔几年之后才对该刊投寄几首诗作,有时发表,有时也被拒。《诗歌月刊》在2023年第2期“先锋时刻”栏目头条刊发了我的组诗《我记得我》,这是一个体现刊物悠久的“探索”宗旨的栏目,算是弥补了我当年未能登上令人瞩目的“挑战”“探索”栏目的遗憾吧。
《诗歌报》是当年全国公开出版的诗歌报刊的先锋性“地标”,而我有幸在青年时代习诗的学徒期和诗艺生长期遇到这家诗歌报刊。。它既是我的诗歌棋谱,也是我与之挑战的对弈者,有时能够刊发赢上一小局,那似乎也就荣幸地短暂地成为其他青年诗爱者诗歌棋谱的一部分;更多的是开阔了创作和理论的眼界,被每期“城父”的号角般的编者按、卷首语所感染和激励,使得身处双重边缘(地域和诗界)的自己能够以饱满的热情和较纯正的探索精神在现代诗歌的天地遨游,直至进入不假外力或发表与否也能够持续、自觉地学习和创作的时期。在我与《诗歌报》之间,没有胜率,没有决胜局,只有个人素养的积累和创造力的激发和进化,只有当年的“厚味”“余味”留驻心田,只有一页页报纸(刊物)在读者心中堆叠起来的丰碑——这样的对弈结果才是令人惊喜莫名的诗意人间。
刘洁岷,湖北松滋人,现居武汉。2003年创办《新汉诗》,2004年创设《江汉学术》“现当代诗学研究”著名栏目。主编、执行主编《21世纪现当代诗学鉴藏》系列和《21世纪两岸诗歌鉴藏》系列等。著有诗集《刘洁岷诗选》《词根与舌根》《在蚂蚁的阴影下》《互望》《慢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