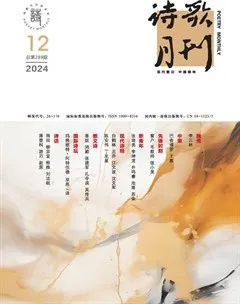写诗与办刊同样是一桩庄严的事
查建英编著的《八十年代访谈录》的封底,标有与八十年代相关的词。比如,激情、贫乏、启蒙、使命感、人文、饥渴、知青等等。我想补上一个词:《诗歌报》。八十年代诞生于合肥市宿州路9号的《诗歌报》影响甚众,刻在那个年代众多写诗者的记忆中,介入了他们的精神生活。当年身边的诗友讲述他们站在绿皮火车密集的人群中专程到那里去拜访。
我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写诗的。那年在县劳动人事局主办的技工学校教书,校门前挂有另一块牌子:职工培训中心。学校面向整个荆州地区招生。在那个早已不在的矩形校园,在有了三室二厅的房子、女儿和讲师职称后,觉得自己没有前途,我试图找一个终有所托的爱好把日子过下去。就是说,27岁决定写诗不仅是残余青春的热情,它也包含着某种来得太晚的人生自我规划。
现在想来,受周边习诗者的影响,我也订了《诗歌报》,两周一张,月末用报夹集中,后装订成册。学校办公室报夹上陈列着各种各样的报纸,只偶尔扫一眼第四版副刊。《诗歌报》则带入书房床头,室内仿佛涌入一股新鲜空气。现在找不见那叠《诗歌报》了。记得主办人是蒋维扬,这个没有什么交往的长者,他将个人诗学修养和对文学的热情投入《诗歌报》的创办与编辑中来,构建了我们心目中的的文学事件或奇迹。
在收藏资料的纸箱内发现仅存的《诗歌报月刊》,1990年一期二期合刊。异形开本,不同于后来《诗歌月刊》的16开本;刊名保持了《诗歌报》字体。年代转换之际,《诗歌报》由报纸转型为月刊。
之后,中国新诗研究有这样一个专用名词:九十年代诗歌。本人理解诗学研究者们的意思。确实,线性时间下的诗歌写作全然不同于八十年代,不同年代产生的新诗文本集体地呈现了迥异的美学形态。三十年后,我给文学院的学生讲中国新诗研究课程,视点就落在这个转型期,细致地从时代语境和写作者的身份转换、后现代文化思潮的涌入,以及诗文呈现其断裂式的变异来加以描述。本人开始于九十年代的诗歌写作,受到那个年代的新诗潮的淘洗,在练习期的草稿式诗作留下抹不去的诗潮印迹。
与九十年代相关的词:现实、城市、新空间、个人、身体、书斋、多元、可能性。这是一个个带着我们个人体悟的词语。相较于八十年代,时代空气变了,当代诗写作在寻求新可能,从一个个字词的替换到情感的拿捏、结构的重建来更新诗的面貌。我的写作开始了全方位的运行:从生活到阅读到写作,开始个人的计划拓展,教书之余的旅行和交友都是围绕写作一事展开。
近日想到在《诗歌报》第二版读到于坚的《避雨之树》。印象太深了。九十年代初,我开始和于坚通信,他的几封谈诗的回信至今依旧保存着。几十年后,我在写作评论他的长文时,曾提及早年的信件往来,书写了几十年来在不同时段阅读他的诗歌的情景,此为我们纯粹诗歌友谊的纪念。那些年国内文学刊物时兴办函授班,1989年《诗歌报》也办了函授,函授老师中有韩东做。那年正我读他的诗集《白色石头》,为了结识他,特别挑了他作为辅导老师;他曾向《诗歌报》推荐过我的处女诗作《宾馆104》。《诗歌报》很大程度上激励着我的写作。今年,早年的学生从广东来看我,他车开到我山房院外,下车的一句话是:只有我们的语文老师选择山居。他说我是他的启蒙老师,提及我在课堂上讲新诗,在酒桌上背诵了那首《宾馆104》。
1996年的某个黄昏,一个年轻小伙子找到我家,自我介绍他是读到了《诗歌报月刊》上我的诗特意来寻访我。他是县人民医院分配来的外科医生,叫管兴平。后来他离职到武汉考博,常给我写信,请我参加武汉的诗歌活动。认识他之后,又与当年在武大哲学系读博的夏可君相识,每次去见他,他都对我说,柳哥,你每次来可要带些新作给我。再后来又见到张典博士,他从南京来会可君。我们有过在黑夜中长谈诗和哲学的经历。现在想来,他们三人先后到过那个矩形校园教工宿舍楼我的书房。他们或隐或现地参与了我的写作生活,和《诗歌报》一样,环绕着我,传入新鲜空气,让一个写诗的时空变得多重多维。
在经历了必要的阅读写作期,1999年,我背着电脑闯荡北京,在中国青年出版社下属的《青年文学》杂志做诗歌编辑多年,2009年离职举家南迁,回武汉某高校文学院工作。在武汉地铁诗歌公共空间的朗读会上,我见到了韩东和于坚。朗诵会完后,和韩东走在一起,忆及“他们”文学社的内部交流资料第四期,封面人物是于小韦。其中他的《三个世俗角色之后》,对于迟到写诗的我有着某种开启之效用。那是让我难忘的阅读期,我在《诗歌报》和民间刊物读到了全新的诗歌作品。肖开愚与孙文波主编的《九十年代诗歌》,在私下流传的民刊《倾向》,曾一度让我惊喜。《诗歌报》可以说响应或推动了民刊诗歌的涌现。前面提及的《诗歌报月刊》1990年一期二期合刊就是“中国诗坛1989实验诗集团显示”,其中展示的诗歌流派基本来自民间。。在徐敬亚、孟浪等编辑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一书,收辑《诗歌报》现代诗群体大展的内容。早年《诗歌报》还举办“探索诗”大赛,后来大赛作品结集出版,可谓推出当代诗的全新文本。
新诗创作就是实验,就是无路可走时的探索性开拓。办刊除了对诗的爱,还要有专业的知识。新诗学是一个特殊的知识,编者即一个类似的诗学专家。《诗歌月刊》在跨入新世代后变得稳重大气,又不失早年的探索风格。刊物的“先锋时刻”“评论”等栏目延续了《诗歌报》时期的栏目。那年的“现代诗导读角”让人留意。在北京工作时期,到扬州出差,诗友带我去看望过叶橹先生,他刚退休,和他聊及他在《诗歌报》开设的专栏。在《青年文学》杂志编辑部,某日偶然发现沈天鸿先生的信件,主动与之联系,谈及他在《诗歌报》的专栏稿《现代诗歌技巧十二讲》。《诗歌报》保持了让我心动的记忆,可以说是我们共同记忆的凝结。
近日翻看保存在书房的《诗歌报月刊》和《诗歌月刊》,在不同的年代断续展示我三十年来曲折的写作路径和留下的或稚拙的或成熟的作品,它参与或见证了我的个人写作,映照出一个写作者在时光隧道中走向某种时间塑形的圆满——这似乎又与《诗歌月刊》有着某种隐秘共通的相似。回忆让人感怀。忽置于写作的晚境,觉得个人写作要用余下的光阴来完成一本类似于惠特曼的《草叶集》。我们的写作即为修得一首首让自己得以通过的文本,此为一个写作者的责任。语言与生命形式的互动生成,语言塑造的同时限制了作者的命运。确实,写诗是一件庄严的事。《诗歌月刊》诞生40周年,经过几拨人的经营,刊物由报到刊,变中有不变,岁月对它的雕塑令人感叹。
柳宗宣,曾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著有诗集3部、散文集《漂泊的旅行箱》《语词地理》、诗学专著《叙事诗学》、随笔集《语词居住的山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