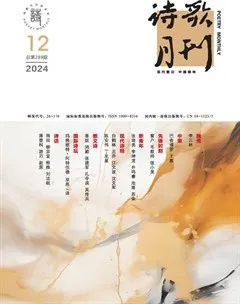诗话三则(随笔)
诗的本体
诗是什么?谈及这样的话题非常难。记忆犹新的是一部关于太空探索的电影——在人类对浩瀚宇宙无限向往的驱动之下,加上科技力量的赋能,电影里的主角出人意料地穿越了虫洞,抵达了宇宙某个深邃之处。这显然是剧情的高潮所在,主角面对超出经验的奇幻太空,震惊之时脱口说出了至关重要的一句台词:“也许只有诗人能用语言描绘出我眼前的景象。”
每个对诗发表观点的人都是一个潜在的诗的本体论者,他们内心迫切想知道“诗是什么”,并且希望能够将具有确定性的答案揭晓给他人。不过,企图以“一言以蔽之”、接近雄辩的方式回答本体论问题,并非易事。可以类比的是,哲人柏拉图在《大希庇阿斯篇》的结尾,也不得不借用古谚“美是难的”,来形容“美”的不可捉摸性。而有关“什么是美”的问题长久以来一直陷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境地。
不妨换个话题,从认识论角度谈一下“诗的发生”。某些经典且通俗的解释很大程度上令人信服,比如《毛诗序》中所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此处指向诗的源起。接下来,言及“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则是将人类情感意志的表现形式作了一个递进式排序。按此说法,诗,准确说是古典时期的诗歌合一的形式,是介于狂呼小叫的嗓音嗟叹和四肢并用的手舞足蹈之间的情志表达,其情绪演绎强度只略低于舞蹈。
那么,诗是什么?回到前面说到的电影的高潮部分,可以略微作出一个论断:当人类萌发了一种必须使用语言来表达自我情志,并希望将这一情志传递给他者时,所选择的最优方式是用诗的形式来完成这一目标,这几乎是人类心智的自然选择。诗的本体,从人类的心智模式角度来阐释,它应该是人类心智模式中的一个细分结构,一种以声音的、文字的语言为“输入/输出”媒介的情智结合体。当然,以上也仅是那些纠缠于实在与唯名的万千“似是O8VkYdR5Dwvdxyz56p2cIg==”说法中的一种。
怎么写诗
怎么写诗,一个方法论问题,细说起来并非一个十分有趣的话题,我大致可以讲讲自己的一些体验。写诗,于我而言是一件苦中作乐的事。早年写诗,写得很快,那是受感觉驱动。之后写得很慢,或许是到了知觉的层面。前年下半年,我与自己订立了一个契约,主题是坚持每天写一首诗。
既然如此,不敢懈怠。为了完成这一目标,时常枯坐或干躺沙发上,冥思苦想诗的第一行、诗的主题、诗的结构、诗的语调、诗的结尾,甚至是每一句的停顿、连接处,以及标点、断行和分段。一旦有一个闪念,就立马行动,给诗稿注入新的元素。有些诗修修改改几十遍,不知疲倦,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为什么在写诗上如此不计成本、投入精力?现在总结起来无非有几点。其一,设定一个颇有挑战性的工作,为了抵抗长期居家的焦虑。写诗,成为了一项能够自我疗愈的行动计划。其二,写诗是进行文学创作,它需要一个合适的、受自我认知框架搭建的场景。竞争性原则正好处在这个框架场景的顶端。换句话说,是个人将创作当做了一个竞技项目。在竞技场景中,至少面临两类竞争者,一是自我,与过去之我竞争;二是他者,与前人和同时代的创作者竞争。其三,出于好奇,想着检阅自己的心智系统是否强大。如果说诗是人类在个性化的心智模型中产生的一种情智结合体——情感与智识的结合体,我们则可以将创作视为一项造物工程。作者便是造物者的主体。作者通过写作来测试心智系统连续创作的稳定性和成长性。
关于这次写诗的契约,最终是履行了。不过,作为一个道德评价的洁癖者,我不认为自己每天写出的那些诗让人称心如意。两种创作者值得观察,一是过度自我怜悯乃至走向自恋情结的作者,他们会满足于自己的造物,并坚信其作品的完美和卓尔不凡;二是那些有相反品格与洁癖的人,对其作品的缺陷深信不疑。
怎么写诗,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甚至有一个非理性的想法是,教授或指导他者如何写诗,对我而言是一项极其无趣的举动。
怎么读诗
自己甚少在公众场合读诗,是出于一种对公开阅读的逃避。有那么一次读诗的经历,倒是让我难忘。不过,不是我自己读诗。那是前年的某个夜晚,我攒了一个非常小的酒局,就在我寓所楼下的餐馆。结束后,趁着酒兴未减,我提议当中一位女士读一首我写的诗。我给了她一首比较长的诗,她很顺畅地读了下来。她读完后,怔在那儿,好长时间一言不发。等她缓过神来,开口说道:“刚才陷进了一种说不清楚的、忘我的情绪当中。”
我并非在意我的那首诗是否属于好的诗。我感兴趣的是,一首诗在被人读出时,包括读者与听众在内,触发的是哪些情绪反应机制。作为诗的基本元素的“语言情绪”的传递方式,是映射、折射还是投射?这似乎又是一个弗雷泽式的触染律的论题。
至于怎么读诗,这里面有必要设立一个前提,那就是选择一些相对的“好诗”来读。什么样的诗是好诗?又是一个富有争议性的话题,长期存在于普遍主义者和相对主义者的争论之间。一些基本共识也许会存在,一首好的诗需要有一种倾向于节奏性的语调,一种适度的能引人共鸣的音乐性,它不同于一般性的散文。
我偶尔也会兴之所至,或说煞有介事地拿某一首诗来朗读,并且沉浸在它的语言洪流中。我指的是有声的朗读。而阅读,需要一个特定的相对沉默的氛围,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感受它的语调和节奏,想象出它所描绘的一帧帧画面,并捕捉弥漫在诗行里的情绪,以及情绪之外的语言智识。
艺术作品至少会提供人们一些情绪和认知上的价值。诗也不例外。阅读它,通过理解这个情智结合体,这一种语言造物,获得疗愈和教育。就像杰克·吉尔伯特的读者所反馈的那样,吉尔伯特的诗让他们“改变了对生活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