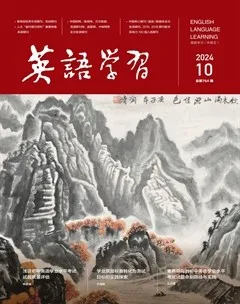在对话中认识女性的处境及其根源
尽管如今社会总体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无论是体力还是脑力劳动者,又或者是各个年龄段的学生,都在各自所处的复杂系统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社会日趋老龄化,生育率持续下降,日新月异的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对传统教育和职业发展构成极大挑战,还迫使我们追问人类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为什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生命的健康和延续反似遇到了更大的危机?停下来思考自己当下的处境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因为它可能会占据我们已经排满的时间,也因为它可能是特定条件下才能获得的一种奢侈。不过,这种对自身处境的思考往往源于某个契机。而激发笔者最近一次思考的契机,就是阅读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的作品《第二性》(The Second Sex)。
通过《第二性》,波伏瓦试图展示这样一种可能:只有认清自己的处境,并且了解这种处境的根源,才有可能生发出自觉自愿的意志和行动去超越这种处境;而因为处境是在变化的,坚持不懈地认识与超越它,才可能获得存在主义意义上的自由。但是,带着当下的视角阅读,我们也可能更多地在书中看到这种“自由”的艰难和有限性:波伏瓦以纵贯历史、横跨多个学科的视野,细致梳理了女性在父权社会中“第二性”处境的形成过程,并揭示了这样的处境如何极大地限制了女性的选择。而看清这样的处境是能为个体指明超越它的道路,还是会带来个体更大的绝望,这是一个艰难的问题,但这也是推动我们持续阅读、思考并作出行动选择的问题。《第二性》对于处境和行动的思考还有另一种启示:我们在了解自身处境时,需要尽可能地扩大视野,去认识他人的处境。过分关注自我或者只把他人当作自我对立面的认识,只会造成更加闭锁的自我认知。对他人及其处境的探查,积极与他人进行对话,会让我们自身的处境以及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变得更加清晰,对于我们的选择和行动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第二性》讨论的是女性的处境问题,而波伏瓦提出这一问题所面临的困难及其意义,可以先从《第二性》英译本的遭遇说起。1949年,《第二性》在法国出版时引发了轩然大波,一边热卖,一边被批判为粗俗下流、缺少科学价值,并被梵蒂冈列为禁书(柯克帕特里克,2021:266,269,274)。当时,在巴黎感受到该书热度的美国出版商艾尔弗雷德·克诺夫(Alfred A. Knopf)的妻子布兰奇·克诺夫(Blanche Knopf)认为这是一本“知识分子的性手册”。克诺夫夫妇请了一位没有哲学和法国文学背景的65岁男性动物学教授帕什利(H. M. Parshley)将此书删减并翻译成英语。波伏瓦看到这个既不完整也不忠实的译本时,曾致信帕什利说:“在我看来很多重要的东西都被删掉了”,并请他在前言中说明实际情况,但后者却在译者序中妄称删减得到了作者的同意。这个最早的英译本在美国一上市也立即成为畅销书(柯克帕特里克,2021: 294—295),却大大减损了波伏瓦原作的哲学深度与女性主义内核1。直到2009年,英国才出版了第一个完整的英译本,译者是两位研究哲学的女性学者博德(Constance Borde)和马洛瓦尼-谢瓦利尔(Sheila Malovany-Chevallier)。一年之后,这个更为忠实原著的全译本才在美国出版。这样一部由女性哲学家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挖掘和揭示女性经验与历史的开拓性著作,却从一开始就以充满偏见和曲解的形式与众多读者见面,这不由得让人想起那些被男性历史抹掉的女性声音。伍尔夫夫妇自己出版的《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1929)里,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用虚构和真实混杂的叙事讲述道,一个女作家带着“女人为何贫穷?”的疑问(伍尔夫,2019:46),在大英博物馆里翻阅书籍寻找解答,却看到关于女性的书大都是男人们写的——“你们知道吗,自己很可能是全宇宙被(男)人谈论最多的生物”(45)。最终,除了愤怒,伍尔夫并没有收获任何有价值的答案。直到20世纪中叶,波伏瓦在写作《第二性》时在卷帙浩繁的文史哲社科经典中看到的,仍然是诸多男性“权威”对女人的本质与命运的“锤锤定音”:“我们应该把女人的特性看作要忍受天生的不完善”(亚里士多德)(波伏瓦,2011,I:8);女人是“有缺失的人”、“意外的”存在(阿奎那)(I:8);“没有男人,女人不能独立思想”(邦达)(I:9);“成为女人是某种非常古怪、非常混杂、非常复杂的东西”(克尔恺郭尔)(I:204);“女人是生病的孩子,十二倍的不纯”(维尼)(I:213);“在女人身上令人恼火的是她们想有理智”(蒙泰朗)(I:278)。而当时的社会现实对于刚刚开始在教育、职业和政治上谋求基本权利的女性而言,也是非常艰难的:男人们从二战战场回家了,因为战争需求而暂时获得就业机会和经济来源的女人们被要求“不要抢走男人的饭碗”,回归家庭生儿育女,毕竟她们“从小就被教导要做母亲”,那是她们的“人生目标”(亚龙,2016:373—374)。在这样的社会期待和文化意识中,波伏瓦要从思想传统的最底层究根溯源、抽丝剥茧,揭示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性塑造,可以想见需要多大的勇气。
尽管困难重重,但每个时代总有女性声音突破重围,因为关注自身性别的处境而提出问题并尝试回答。波伏瓦的《第二性》尽管以不同的面貌被批判,却依然成为“女性主义的圣经”(柯克帕特里克,2021:1)。2009年的英译本前言对上述称谓做了辨析:虽然这个宗教性类比可能吓退那些以为这是狂热信徒的圣书而心生警惕的读者,而且波伏瓦写作时已经从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女孩变成坚定的无神论者,但《第二性》的开拓性(the first of its kind)及其两卷本的叙事框架使其堪称“非选民受奴役历史的新旧约(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of an unchosen people with a history of enslavement)”(de Beauvoir,2011:13)。也就是说,《第二性》不是一部女性成长史,不是在讲述女性主体如何历经困难自我成长的故事,而是记录了在历史长河中,男性主导的社会与文化力量对女性的命名、限定、规训与惩罚。
《第二性》中最有名、被后世讨论最多的一句话是:“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波伏瓦,2011,II:9)。这是该书第二卷《实际体验》(Lived Experience)第一部第一章的第一句话。为什么第二卷在极为简短的导论之后,以此句开篇?因为这句话是两卷本中承上启下的关键句。《第二性》第一卷是男性在历史、科学和文学中对女性的定义和解释,探讨了女性为何被视为“第二性”;第二卷则从现代女性的成长历程出发,讲述女性自身的经验和对自己处境的理解。“女人不是天生的”承接了第一卷对父权社会将女性界定为弱者并归因于天生如此的驳斥,“后天形成”则开启了第二卷由女性自己讲述的社会“变形记”。那么,这句话为什么能成为后来的学者和读者广泛讨论的名言呢?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它看似与“常识”相矛盾。我们习惯于用生理特征来界定男女性别,因为这是“自然”的、天生的。就如《第二性》第一卷导言所提到的,有人认为有子宫的就是女人(波伏瓦,2011,I:5)。进而,第一卷第一部第一章“生物学论据”列举了古往今来很多男性科学家、哲学家依据女性的生理特点去界定女性本质的观点:由卵子在受精过程中表面的“被动”引申出女性是“被动的本原”(I:32—33);女人因为身体和大脑的平均重量比男人轻,所以大脑能够“分泌”出的知识更少(I:56)。这些观点如今看来很荒谬,但是它们的基本逻辑——将某个生理特征赋以特定价值,使“女人”因其“生来”就有的某些特征成为社会评价体系中的弱者——在各个时代依然回响不绝。在把生理特征与价值标准相关联来圈定一部分人时,也必定会排除一部分人。比如《第二性》第一卷导言还提到有“行家”断言某些女人虽然有子宫,但却“不是女人”,而他们此时的评价标准是以柔弱为标志的“女性气质”(I:5—6)。由此可见,父权社会对“女人”这个社会范畴的界定背后的逻辑是:先由特定的生理特征指向某种价值标准,再用这种评价标准反向划定该性别的群体。自此,这种人为的标准就变成了“天然”的桎梏。用生理特征来界定内含价值标准的社会范畴,在当代还引发了另一场争议:《哈利·波特》系列的作者罗琳(J. K. Rowling)因其关于女性生理定义的言论引发了争议,她认为生物性别是不可忽视的,这引起了许多人的反对和批评。但她本人和支持者坚持认为,这一限定是为了不抹去“全球女性的生活现实(lived reality of women globally)”。因此,性别的问题看似是生理的划分,实际关系到政治、经济、伦理等一系列价值与利益之争。
回到《第二性》所讨论的女性定义,要了解与之相关的价值标准是什么,只需分析一下它的标题“第二性”。相对于男性/第一性,女性始终处于第二性的从属地位,这是波伏瓦对父权社会中女性处境一针见血的概括。波伏瓦在两卷本中从父权话语和女性经验两个维度对“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成为第二性的”做了详细论证。父权社会对女人的定义和对女性的期待是一整套价值体系,第二性是其基本内核。“第二性”的法语原文是Le Deuxième Sexe。与英文中分别强调生理属性和社会属性的sex和gender不同,法语一般都用sexe2表示性别。波伏瓦以“第二性”为一部女性论著的标题,意在揭示社会常规与流行观念中隐藏的性别不平等结构。她将女性在父权社会中“二等公民”的现实提到前台,并将其作为全书要挑战的中心标靶。《第二性》第一卷的导言这样概括“第二性”的内涵:“两性的关系不是正负电流、两极的关系:男人同时代表阳性和中性,在法文中,‘les hommes’用来指人,即‘vir’这个词(拉丁文,男人)的特殊含义吸取了‘homo’(拉丁语,人)这个词的一般含义。女人是作为负极出现的,凡是限定词对女人来说都是限制,没有互逆性”(I:7—8)。也就是说,“女人相较男人而言, 而不是男人相较女人而言确定下来并且区别开来;女人面对本质是非本质。男人是主体,是绝对,而女人是他者”(I:9)。在追溯女人“他者(other)”的地位时,波伏瓦使用了“他性(alterity)”思维的概念作为过渡。她认为,“他性是人类思维的一个基本范畴。任何群体都绝不会不直接面对自身提出他者而将自身确定为一个群体”(I:10)。他性思维源于主体通过区分自我与他者(非我)来认识和确立自我。由此建立的他性关系不是绝对的,因为自我与他者的交往会带来相对性的认识,即在我眼中他是他者,在他眼中我是他者。在这里,他性思维与女性的第二性处境有微妙的区分。第二性意味着他者始终处于次要的附属的地位,他者和自我的这种不平等关系是绝对的;他性思维则只是强调任何主体在认识非我的存在时所采用的一种二元思维方式,并不一定会成为限制自我和他人的压迫性结构,反而是认识自我之外的世界并建立与其关系的必要途径。波伏瓦在第一卷导言也针对关于男女两性孰优孰劣的争吵重申了这一点:“‘妇女问题’的争论之所以如此被人视为废话连篇,是因为男性出于狂妄,把它变成一场‘争吵’;争吵时是不再讲理的。人们坚持不懈地力求证明的是,女人究竟高于、低于男人,还是与男人一样……每个论据立即招来反驳的意见,往往两种论据都失之偏颇。如果试图明察秋毫,那就必须摆脱这些尺矱;必须拒绝高等、低等、相等这些模糊的概念,这些概念搅乱了所有的讨论,必须重新开始探讨”(I:21—22)。所以在波伏瓦看来,他性思维本身并不存在孰高孰低的压迫性二元对立,承认异于自我的存在,是人类思考自身和世界的基本方式。这一点显示出她在与他者的关系中认识自我与世界的本质的存在主义哲学立场。
既然他性思维本身不存在压迫性,那么为什么长久以来女人会被界定为绝对的、纯粹的他者,并屈从于她作为第二性的处境呢?波伏瓦提出这个问题时将被压迫的女性与其他被压迫的群体做对照。她指出,在很多不平等的二元关系中,他者会通过斗争挑战和颠覆原来的压迫关系,比如海地黑人的反殖民斗争和无产者在俄国的革命。波伏瓦问:为什么女人并非少数群体(从有人类历史以来就几乎构成人群的一半),却在漫长的父权社会历史当中没有试图确立自己的主体性,改变从属于男人的地位(I:11)?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第二性》整本书实际上都是在回答这个问题,同时驳斥这是因为女人天生就该如此的本质主义观念。不过,她在导言里给了一个比较宽泛的解释,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波伏瓦在女性主义问题上的前瞻性。她指出了两个关键点:其一,女人因为历史和社会的原因高度依附于自己的压迫者,且没有形成整体性的认同——“资产阶级妇女与资产者而不是无产阶级妇女联结起来;白种女人同白种男人而不是同黑种女人联结起来”(I:12—13);其二,女人不能以反抗全体男人为目标——“即使在梦中女人也不会消灭男人”(I:13)。第一点表明,波伏瓦不仅意识到女性群体内部的分裂,还关注到其他群体所遭受的压迫和不公。在争取女性权利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女性问题与其他政治问题(包括但不限于阶级、种族、宗教、文化等)的相互交叉,也就是当下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中最重要的交叠性(intersectionality)问题意识。尽管后来许多女性主义者批评波伏瓦站在欧洲白人中产阶级非婚非育女性的立场而产生的诸多偏见,但这并不能抹杀她在《第二性》中时时流露的对“我们”中“他人”的伦理关注。第二点其实很好理解,毕竟,压迫女人的不是男人这个生理性别,而是支撑父权社会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这一点也极具现实意义,它反驳了那些认为倡导女权和女性主义就是挑起性别对立的观点:与女人和男人为敌的不是另一个性别,而是将二者形塑为男上女下的压迫性权力;真正的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思想是对平等关系的诉求,是将男男女女都从不平等的关系中解放出来。
除了在导言中这段精辟的概括,波伏瓦针对“女人为什么长久以来屈从于第二性的处境”这一问题,在厚厚的两卷本中运用自身丰富的学识和精微的洞察,呈现了一种哲学的探究,且是融合了多种声音的探讨,而非给出一个简单的定论。政治学学者马尔索(Lori Marso)指出,《第二性》采取了一种对话的形式,“波伏瓦将几位不同的人物置于对话之中,他们的身份和处境在彼此之间以及与世界之间都是相互渗透的。波伏瓦描述的人物都受到本体论、情感、经济和历史条件的影响。这部文本在跨学科和跨领域方面进行实验,将生物学、生理学、哲学、文学、定性社会学记录、历史、经济学、心理学和政治学等各学科都纳入对话,共同探讨性别差异的意义和层次”(Marso,2024)。马尔索注意到,《第二性》纳入了不同个体的经验和多个学科的观点,而这种形式的探讨并不指向 “某个确定未来的预见或是解决方案”(Marso,2024)。也许可以说,波伏瓦写作《第二性》和我们阅读《第二性》的意义在于理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以及这个问题是如何形成的。有了问题意识,我们才会去思考自己的处境,进而找到适合自己的答案,选择自己的行动。这与存在主义哲学强调主体自主选择的理念一脉相承。
以这样的方式阅读《第二性》,我们可以更好地结合当下的视角和具体的地方性观点,参与到问题的对话中。例如,第一卷第一部第一章从生物学角度讨论女性如何被“科学”地定性为弱小和被动。波伏瓦在其中所批驳的很多观点如今已经过时,但是她捕捉到的某些趋势却颇具预见性,其论述的基本逻辑在今天仍然有效。她指出,动物世界中的雌雄只是依据生殖功能划分的不同生物形态,而且不是绝对的存在形态(28—29);物种的存在因为生殖活动而延续下去,但存在本身并不规定必须有性的差异(31,34—36);可以想象单性生殖、无性繁殖和雌雄同体的社会,实验也证明激素调节可以产生雌雄间性(31—32,39)。由此可见,生理性别本身就不是必然和应然的,对它的限定只能是社会的建构,并与其他目的相关。波伏瓦还认为,总体而言,女性在机体力量等方面处于弱势,这是事实。但“弱小”只是相对于环境和物种延续功能的要求而言的。“生理学论据(肌肉不够发达)具有的意义从属于整个环境;只有根据人给自身提出的目的、人所掌握的工具和人制定的法则,‘弱点’才显现为弱点。……在风俗禁止暴力的地方,肌肉的力量不会建立统治地位,必须有存在、经济和道德的参照,弱的概念才能具体地界定”(57—58)。她一再强调,“生理学并不能建立价值,更确切地说,生物学论据具有生存者赋予它的价值”(59)。由此逻辑推演,当环境和物种的延续条件改变时,比如医学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引发人体机能和生殖功能的改变时,人的生理特性与功能或也将被重新界定、塑造和评价。当生理性别可以被后天改变,生殖功能可以在体外实现,身体与技术进一步糅合,我们关于人的概念与价值都会经历持续的拷问。
《第二性》的对话性还体现在波伏瓦让抽象的理论与真实的经验一同参与到对同一个具体议题的讨论中。比如,第一卷第一部第二章“精神分析观点”可以和第二卷第一部第一章“童年”进行对照阅读。在分析男性视角的精神分析理论时,波伏瓦指出,“弗洛伊德不太关注女人的命运;很明显,他根据对男人命运的描绘来描绘女人的命运,只修改了其中某些特点”(62);“在精神分析学家那里,只有男人被定义为人,而女人被定义为女性,每当女人作为人行动时,就被说成她模仿男性”(75)。她认为,弗洛伊德以男性的性欲和性感受为基准,仿照自己创造的男童“俄狄浦斯恋母情结”,制造其女性形式“厄勒克特拉情结”(恋父情结),其核心是阴茎崇拜(63—64)。但波伏瓦并非全然否定精神分析理论,她在“童年”一章中充分展示了如何辩证地利用精神分析理论来阐述女童自我意识发展的真实体验。她用细腻的笔触描述了婴幼儿时期男孩和女孩对母亲共同的依恋和源自身体接触的安全感,结合拉康的镜像理论说明幼儿断奶期意识到的自我是一种“异化”的孤独的形象,因此无论男女都试图通过“诱惑和炫耀”来“竭力延长断奶以前的幸福状态”(II:11)。波伏瓦指出,正是在这个阶段,家庭和社会对男孩和女孩开始了显著的区别对待,注重培养男孩独立、勇敢的个性和作为男性的自豪感,而宽容女孩的依恋和撒娇(12)。她认为,那些在弗洛伊德之后假设仅仅发现了男女生理构造不同就足以产生心灵创伤的精神分析学家,“极大地误解了儿童的心理”;与其说女孩因为发现男孩有自己没有的东西而自卑,不如说是“父母和周围人做出的评价,给予男孩的威望”才是女孩自卑产生的原因(19—20)。小男孩在小便游戏的自由中发现“一个可以认出自己的他我,可以大胆地承受他的主体性”,生殖器作为“与之相异的客体本身,变成一个自主、超越性和力量的象征”。与此同时,人们把一个代表整个身体的被动的布娃娃放在女孩手中,“小姑娘喜爱她的布娃娃,打扮它,就像她梦想自己被打扮和被喜爱那样……她强烈地感到要被人赞赏,要为他人而存在”(21)。由此,男孩在控制身体的过程中习得主动性和掌控力,而女孩在打扮自己和布娃娃的过程中习得被动和乖巧的“女性气质”,并在成长的过程中进一步熟悉以男性为主导的性别等级。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权运动的发展,女性地位显著提高,女性的声音和形象也变得越来越丰富而有力,女童乃至儿童整体的养育和教育思想与实践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第二性》深刻描绘并剖析了女性第二性地位背后的社会塑形力量,揭示了女性处境根源的隐蔽性和长期性,警醒和启迪了世界各地的女性读者。也正因如此,我们在当下依然阅读它,思考它提出问题的意义与方式。
最后,在阅读《第二性》时,还可以结合波伏瓦对自我的讲述和他人对她生平的讲述,也就是在波伏瓦的女性论著、回忆录,以及关于她的传记中寻求一种对话性。在这场对话中,笔者找到的是自我与他人的伦理,即对自我的关注和与他人的联结之间的关系。波伏瓦在一系列回忆录中讲述了她成为自己的历程。而在波伏瓦的部分日记和书信被公开后,由学者写就的传记《成为波伏瓦》(Becoming Beauvoir:A Life)指出了她的回忆录与她的日记和书信中的不相符之处,并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波伏瓦要在回忆录中抹掉其他的男人,给萨特一个最重要却与事实不符的位置?”(柯克帕特里克,2021:109)为什么波伏瓦没有忠实地记录自己在哲学上独立于萨特,甚至先于萨特的创见(比如存在主义的道德观),而“要在自传当中抹掉自己如此重要的哲学贡献”呢(211)?笔者认为,波伏瓦的回忆录与她的日记和书信中展现出的自我之间的差异和取舍,反映出女性自我书写的普遍困境:一方面,她们有强烈的自我表达的需要和渴望,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她们在家庭私人领域和社会公共领域中的声音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抑制;另一方面,自我表达总是伴随着自我审视,而女性的自我审视中总是带有社会道德审判的意识投射。这种渴望和审视都受到父权社会的抑制和刺激。正如波伏瓦在1927年的日记里提到的“从内向外对自我的审视”和“从外向内对自我的观察”(柯克帕特里克,2021:198)。对比她在日记中的自我记录与在公开出版的回忆录中的自我塑造,可以看出,不同的写作目的决定了其中隐含的审视力度和角度的差异。考虑到自己早先出版的自传体哲学小说《女宾》(She Came to Stay)被当作八卦谈资和人身批评的经历,波伏瓦对人们从她的回忆录中获得一个怎样的波伏瓦形象,必定是有着复杂的考量。波伏瓦在很多场合强调萨特才是他们俩中的哲学家,又轻描淡写她对萨特之外情人们的感情。柯克帕特里克对其中原因做了比较细致的分析,概括而言,是“敏感的波伏瓦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察觉到了不安全感,因而选择低调行事”(99)。我们可以把波伏瓦这些不同性质的文本看作她对自己的多维塑造。在这个将她的性别界定为“第二性”的世界中,她反复探索成为自我与联结他人的伦理问题。在哲学小说中,波伏瓦“提供了两种与他者联系的方式:第一种是承认他者和自我意愿都是有意识的存在,都有丰富和脆弱的内在生活。第二种是拒绝看到前者,拒绝互相回馈的可能,理所当然地认为他者要么是对我们有用的物,要么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阻碍”(柯克帕特里克,2021:196—197)。在日记里,波伏瓦写道:“在我看来,我有一部分生来就是要奉献他人的,有另一部分生来就是要保持自我的。第二部分能够独自成立,而且它保证了第一部分的价值” (柯克帕特里克,2021:62)。在回忆录中,她反思自己和萨特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认为无产阶级的斗争不是他们的斗争,“他们的斗争是哲学层面的”,并对当时的自己和萨特“给出了‘精神上骄傲自大,政治上盲目无知’这样的评价” (柯克帕特里克,2021:133)。对于和萨特的关系的表述,不可否认,波伏瓦在回忆录里的记录有塑造某种公众形象的成分。后世对于波伏瓦和萨特的关系、他们与其他情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某些哲学观点中究竟她和萨特谁的贡献更多等问题,常常争论不休。但笔者更认同柯克帕特里克所说的,他们之间“是一种‘永不间断的对话’”(柯克帕特里克,2021:198),就像波伏瓦在日记、回忆录和小说中也在不断地与不同时刻的自己对话一样。通过这些对话,自我在与他人的关系中不断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同时这些对话也是对自我和他人的持续塑造。
波伏瓦的《第二性》开启了西方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揭示社会意识和文化基因中女性的不平等处境,其关切至今仍不过时。女性地位在政治和经济稳定的时期看似总在进步甚至激进,但是一旦遇到突发事件时,首当其冲的常常还是女性。例如,2022年6月《柳叶刀》发表的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2019年3月至2020年9月间的数据表明,女性更有可能报告失业,女性和女孩因非学校关闭原因辍学的可能性更高,女性报告性别暴力增加的可能性也比男性高。该研究据此认为,在新冠疫情期间,女性和男性之间原有的不平等现象有所加剧(Flor et al.,2022)。《第二性》早早地看到了女性处境的历史性、现实性、持续性、隐蔽性,并开创性地论证女人之所以成为第二性,并非天生如此,更不是她们自觉和自由的选择。我们需要像波伏瓦一样,不断尝试与自我对话,与他人对话,在自我与他人的联结中认识我们的处境,并作出我们的选择。
参考文献
de Beauvoir, S. 2011. The Second Sex [M]. New York, NY: Vintage.
Flor, L.S., Friedman, J., Spencer, C.N., et al. 2022. Quantifying the effects of the COVID-19 w9aAHCBttTymv88+UA+yFA==pandemic on gender equality on health, social, and economic indicator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data from March, 2020, to September, 2021 [J]. The Lancet, 399(10344): 2381—2397.
Marso, L. 2024. Simone d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A]. In J. T. Levy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lassics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 [C]. Oxford Handbooks Online. https://doi.org/10.1093/oxfordhb/9780198717133.013.31.
Moi, T. 2002. While we wait: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Second Sex [J].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27(4): 1005—1035.
Simons, M. A. 1983. The silencing of Simone de Beauvoir: Guess what’s missing from The Second Sex [J].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6(5): 559—564.
波伏瓦. 2011. 第二性(两卷本)[M]. 郑克鲁,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柯克帕特里克. 2021. 成为波伏瓦[M]. 刘海平,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伍尔夫. 2019. 一间自己的房间[M]. 于是,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亚龙. 2016. 太太的历史[M]. 何颖怡, 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1 1983年,美国哲学家西蒙兹(Margaret Simons)就对第一个英译本的错漏和负面影响做了细致的分析;1993年,美国学者皮拉迪(Jo-Ann Pilardi)梳理了《第二性》在西方的接受史,并指出该英译本对此还是有积极影响的;2001年,著名女性主义文论家莫伊(Toril Moi)呼吁是时候该出版《第二性》的新英译本了。与此同时,《第二性》在非英语世界的翻译与传播也与第一个英译本有着复杂的关系,可参见2023年出版的《翻译〈第二性〉》(Translating Simone de Beauvoir’s The Second Sex: Transnational Framing, Interpretation, and Impact)中多国学者对这个问题的分析。
2 近年来,受到英美性别理论的影响,法语在强调社会性别(gender)这一含义时,常常借用原指“类别和语法性别”的genre一词,比如L’identité de genre(性别认同)和L’expression de genre(性别表达)。此外,在阅读《第二性》时,笔者曾向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法语教授车琳求教。车老师指出,在法语中长期存在把女性叫作Le sexe faible(the weaker sex)、男性叫作Le sexe fort(the stronger sex)的用法。
作者简介
牟芳芳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