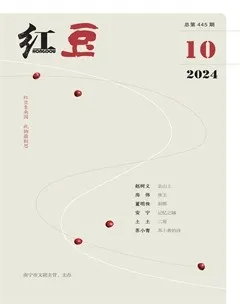天稻之城
一
有可能是新月,也有可能是残月,还有几缕月光从云缝里掉落下来,前前后后,三三两两,铺洒在这楼顶天台的稀泥之上。来自遥远的海上的风,不管是早到一天,还是迟到一天,只要能将这层浮着灰尘的水幔子轻轻荡开,第一粒种子就会迫不及待地顶破黄金般的稻壳,然后一激灵,抖落满身的泥水,冒出一个针尖大小的白芽儿来。
这是夜与昼交替的黎明。三爹知道,更壮阔更盛大的景象马上就要到来了。他清了清嗓子,扯了扯衣襟,很想把有些佝偻的腰板也扯直了。可在这三十三层还建楼的楼顶,没有人能看见他庄严肃穆的样子。三爹却执拗地认为,他能看见他的样子,水稻也能看见他的样子。
最先的一粒种子,是潜伏在泥底的水稻种子兵团派出的侦察兵。它刚一露头,三爹就以久违的神情注视了它,迎接了它。而现时有着近十万人口的左岭新城,已经没多少人还在意谷雨这个古老的时节。这个时节唯有三爹与一粒种子秘密接头,窃窃私语。种子得到三爹友好的暗示,于是朝稀泥里点了点头。刹那,成千上万粒种子像是接到集体冲锋的号令,纷纷拼出全身的力气,挣脱裹身的铠甲,以一种向死而生的决绝和绝境重生的勇气,从泥底发起了冲锋。那一刻,东方的一抹鱼肚白将现未现,不知是云还是雾,贴地弥散。准确地说,是贴着厚实的水泥隔热层弥散。白云或湿雾所到之处,抻开了一张浩大的朦胧的水幔子。白云或湿雾消退,“蚁军”显现,密密麻麻的白芽儿钻出稀泥,占领了楼顶一角。
三爹会心地笑了。吸饱了水分的白色“蚁虫”,身体渐渐膨胀。三爹抬头一看,东方的鱼肚白已经扩大到了天际,天光泄露。这一瞬间,有如接受神谕,数不胜数的白色“蚁虫”预备起,齐刷刷地往上一蹿,抽身长成了一株秧苗。再预备起,往上一蹿,除了保留身秆子的那部分嫩白,头顶统一地、齐刷刷地开始分叉,分成了两瓣浅黄的叶片儿。
观察一垄秧苗的生长,让三爹找回了底气。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稻农,而不是住在左岭新城的新市民。挺一挺胸脯,朝曾经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村庄耿家畈望去,树荫下的粉墙黛瓦早已消失殆尽,一马平川的尽头,日头刚刚冒出。三爹迟疑了一下,还没有来得及确认那个方位是不是耿家畈,只见日头往上一跳,跳出了地平线,跳进了他的眼窝子。好大一个太阳,比磨盘还大。立刻,天幕开启,白昼的强光让三爹睁不开眼睛,他不得不背过身去,逆光而立。等他再一回头时,蓦然发现天台上那些嫩白的浅黄的,竟在转身之间换上了一身新绿的新装。
这身新绿在三爹面前砌起了一道墙,将他挡在了另外一个世界,却又在墙内制造出了一些气息,故意去迷惑他、引诱他。三爹就地打坐,闭上眼睛,大口大口地吸气,并且一直憋住气,尽量不那么快吐出来。他把植物的清新、泥土的腐臭,还有禽畜的膻臊……总之是把一些有的或没有的气味统统憋在鼻腔里。过了很久,他才缓缓地舒出了一口长气。这气里只有气而没有味了,那些混合了村庄的味道,全部被他吸进肺里,沁进心里,渗进骨髓里。
三爹似乎满足而又不满足地从地上爬起来,朝天台门洞走去。他刚才扶地撑起的一双手上,沾满了灰尘。他拍拍手,要把灰尘继续留在天台上,等待一场雨,化尘为泥,好为将来水稻分蘖时再追加一次底肥。
大半辈子的劳作,让三爹的双手比一般人要粗糙、颀长,都快垂手过膝了。这样不成比例的上肢,不仅有碍观瞻,而且行动起来也似乎多了一截,平添不少麻烦。三爹干脆将双手朝后背一甩,左手右手很配合地交叉起来。如此这般,弯曲的后背既能驮起超长的双臂,双臂的重力又能压平脊椎的弯曲,真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爹,你又一宿没睡?”不知什么时候,儿子铁蛋蛋已经站在了天台门洞处,本是关切的一句问候,却把三爹吓了一跳。三爹不搭理铁蛋蛋,侧身挤进门洞。本来他可以乘坐电梯回到自己家,但他更愿意走楼梯。从前村前的古牳山和这还建楼差不多一样高,自己一天能上山下山好几趟。三爹下楼约等于下山下到一半,累了停下来歇口气。婊子养的,到底是老了,爬不动了。婊子养的,还好意思问我睡没睡。三爹在心里骂个不停,他连自己都骂,骂儿子铁蛋蛋那是小菜一碟。不是吗?这个不着调不靠谱的狗东西,哪里知道老子睡不着觉的原因?
左岭新城竣工,农民准备回迁那阵子,三爹想着就要住进和城里人一样的高楼,也是整宿整宿地睡不着。他的祖传宅基地在耿家畈,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土坯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砖瓦房,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两层楼。如今拆迁了,就要住进摩天大楼了。三爹回想他这辈子,人生如住房,越住越高,越住越好。
没承想,住进新城的新鲜劲儿刚过,各种烦心的事儿接踵而来。新城的高楼长得都一个样,刚开始三爹记不住自家的楼栋,好不容易找到自家的楼栋,又担心人潮汹涌挤不进电梯。铁蛋蛋这个狗东西把好端端的一个新家搞得不伦不类,他是住舒服了,可老子一进屋就犯起愁了。比如客厅的电视机,那基本上就是一个摆设,三爹想看个新闻、听个老戏什么的,都不知道是要从机顶盒遥控器里找,还是要从电视机遥控器里找。家里的空调、冰箱、电风扇、洗衣机、扫地机器人……各种电器,各种按键,各种模式,三爹记住了这个,忘记了那个。铁蛋蛋却用无线网络连接了他的华为手机,人不落屋,十里百里,隔空操控。最气人的是,他还搞了一个智能马桶,坐上去冬暖夏凉不说,屙完了还不用手纸,用温水冲洗,热风烘干。这叫蹲了大半辈子茅厕的三爹情以何堪?又如何屙得出来享受得了?最最恨人的是,自从铁蛋蛋的母亲去世后,这个家就剩下爷儿俩老少两条光棍了,铁蛋蛋都三十好几了,连个媳妇都不肯找。有一天竟抱回家一个黑盒子,说这个就是他的媳妇,叫“小爱同学”。她能听懂铁蛋蛋的普通话,比如点歌、讲故事、回答问题、控制家用电器等,只要铁蛋蛋一句话,她都能乖乖搞定。但她听不懂三爹的左岭方言,无论三爹怎么吩咐,她总是娇声娇气地回答:“哎呀,你这个问题把我问住了,看来我要加强学习了。”搞得三爹常常生闷气,气得睡不着觉。
“婊子养的,这是造的哪门子孽啊?怎么搞回来这样一个媳妇啊!”多少次,三爹生完闷气,一个人爬上楼顶,仰天长啸。有时在深夜里,不管是冬天的冰冷,还是夏天的灼热,他索性瘫倒在水泥隔热层上,对着星星吹胡子瞪眼睛。那些星星还嘲笑他,也对他吹胡子瞪眼睛。后来三爹的心境慢慢地平和下来,他不再生儿子铁蛋蛋的气,不再生儿媳“小爱同学”的气,也不再生左岭新城的气。为了表示自己想得很开,他躺在天台上哼小曲,还伸出两只大手掌,就地打拍子,左拍一下,右拍一下,感觉这硬邦邦的天台,就像从前耿家畈的稻田一样柔软、亲切。
二
三爹是在前年的夏天,在这摩天高楼的天台上,发现长有一株水稻的。那是一只麻雀偷了别处的稻田里的种子,在飞越左岭新城的途中,将一粒良种遗落在了天台隔热层的缝隙里。雨水和灰尘成就了一粒种子,种子诞生了一株水稻,水稻邂逅了三爹。三爹一眼就认出这是一株杂交的猫牙香稻。两年以后,由一只麻雀带来的一粒种子,孕育了成千上万粒种子。三爹很想感谢那只麻雀,但在左岭新城,已经很难见到麻雀。有一天,三爹站在三十三层楼顶,朝耿家畈的方向眺望。他总是这样,朝那个方向眺望,那里曾有大片的田地和时而轰然飞起、时而骤然落下的麻雀群。只是现在田地被机械推平,立起了钢结构塔吊,围起了建筑围挡,麻雀和闲杂人等被禁止入内。三爹隐约感到,又有什么项目就要开工了。
建厂是迟早的事情。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三爹还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时,村里就盛传要建化纤厂。在三爹的印象中,确有一批专家搬动大小箱子,在耿家畈周围勘察过地形。三爹好奇地问村里大人那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大人告诉他,箱子里装有铁砣子,专家拿它来测量地壳的厚度。一般的地方只能承受两三个铁砣子,再往上加,铁砣子就会摇摆不定,说明此地地壳较薄。但耿家畈能承受五个铁砣子,表明地壳较厚,适宜建厂。小小年纪的三爹觉得大人扯淡,几个铁砣子都能压得地壳抖动,那仪器箱子岂不是会把地压塌了?大人们一脸窘相,朝三爹的小脑袋拍了一巴掌。“问那么多干吗?你好好读书,将来进厂了,不就晓得了?”读书对三爹来说,就像要他的命,让他难受得很。不过那个学期,班里突然来了好多大龄女生,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和七八岁的三爹一起读书,很搞笑的。三爹后来才明白,这些女孩子都是来补习文化的,准备将来进厂当工人。那时农村女孩不读书或中途辍学的居多,建厂燃起了家长和她们的新希望。没想到一年后,专家撤走了,建厂的计划泡汤了。
工人没有当成,三爹却收获了爱情。三爹小学没毕业,家里就给他定了一门“娃娃亲”,对象就是那个重新辍学了的插班女生。成年后两人依照农村的规矩交往着,直到适龄结婚。后来儿子出生,越长越大,越来越调皮。三爹联想到从前村民口中的“铁砣子”,干脆唤儿小名“铁蛋蛋”。这会儿,三爹心想,那么老实忠厚的一个女人,怎么生下了这么一个不靠谱的儿子?他的眼睛直勾勾地望着耿家畈的方向,好久才回过神来,铁蛋蛋母亲的坟被推平了,骨灰迁去了八叠山。四十多年以后,说建未建的工厂终于落地成真,可铁蛋蛋的母亲就那样走了,不再属于耿家畈的人口了,当一个留守的孤魂都不够格。
三爹多少有些伤感。一挪步,楼顶的秧苗摩挲了他的足踝。他又有了走在耿家畈田塍和地埂上的感觉,那是一份关于植物疗法的日常使用清单。这个季节,就有垂序商陆、酸模叶蓼、一年蓬、草木樨、打碗花、野豌豆、插田泡、辽藁本、苣荬菜、灰菜、川芎……它们有的是能治病疗伤的药材,有的是能充饥饱肚子的野菜,有的是能解馋解渴的野果子,更多的还是能治愈眼睛的风景。
一只麻雀从天空俯冲下来,在三爹的眼前划了一道黑色的闪电。它紧接着闪电般掠过蓊郁的秧苗,检阅完大半个天台后,再侧身飞回天空。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提醒了三爹,真有一只麻雀在惦记着他,惦记着他的稻子。
三爹打望天空,想看清这只麻雀是打哪里飞来的,又要飞到哪里去。只见麻雀在天空旋绕一圈后,停驻在楼下道路指示灯的灯杆上。那里有一根横向的空心钢管,上面挂满了信号灯和摄像头,钢管的截面没有封口,留下了一个圆形的小孔。麻雀稳稳地站住,四处张望了一番,发现路上的行人以及楼顶的三爹并无敌意,于是放松警惕,一头钻进空心钢管里。三爹心想,时代变了,连麻雀都住进了密不透风的铁房子,能不憋得慌吗?又想千变万变,“麻雀落田要吃谷,人要吃饭”这个道理不会变。三爹俯下身去,认真查看秧苗的长势。秧苗像睡醒了似的,日夜不停地生长,快有一个拳头高了,再过几天就能移栽了。三爹扒开苗距,发现分蔸出苗旺盛,只是水深不够,泥层出现了裂缝。三爹抬头看天,天气晴朗。他苦笑着,感叹自己不是神仙,不能呼风唤雨。三爹准备晚些时候回家挑水。自从天台上有了秧田,他就时不时地回家挑水,给秧田抗旱。三爹不敢坐电梯,怕被人发现,只能趁天黑走楼梯,上上下下,来来回回,像翻越古牳山一样,将种田的水挑到山的那边,山的高处。
“爹,你能不能不整这些没用的?实在憋得慌,整个老伴儿回家陪陪你,也比你种几棵稻子强。”不知什么时候,儿子铁蛋蛋又站在了天台门洞处,一双眼睛骨碌碌地转——除了喜悦和害怕,不屑与疑惑、厌恶与悲哀、乞求与难过,各种表情像川剧变脸一样,在他的脸上一一翻遍。
“婊子养的,你还说我?年纪轻轻的,不讨个老婆也就算了,工作都不要了?老子种稻子玩,也比你耍手机打游戏强。”
三爹想侧身挤进天台门洞,继续回家挑水,无奈铁蛋蛋气鼓鼓的,依然堵在那里,丝毫没有让道的意思。“耍手机打游戏咋了?手机耍得好,人生差不了;游戏打得精,生活才得劲。”
这个铁蛋蛋,和年轻时的三爹一模一样,读书不行,贪玩样样都行。他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一直在外地电子厂打工。后来,工厂降薪裁员的浪潮又把他打回了原形。最近,他宅在家里,主要任务就是吃饭、睡觉、打游戏。
三爹不跟铁蛋蛋怄气,转身侍弄他的秧苗去了。
三
它们比肩站在天台上,身高一拃多长。一拃多长就意味着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稻种从稻壳中分娩而出,已由稚嫩的婴儿长成了青涩的少年。三爹准备好了,他找来了很多白色泡沫箱,帮助它们去完成一段从野草到水稻的神奇生存史和进化史。
白色泡沫箱是从农贸市场捡来的,箱中的黑泥是趁着夜色从耿家畈“偷”来的。三爹做事很谨慎。直接在天台上大面积种植水稻,容易造成渗漏,引发邻里矛盾。将水稻移栽在泡沫箱里,便于挪动,便于管理。只是那些黑泥,在耿家畈的田地上取土也算“偷”,因为那里现在是一家芯片工厂的建筑工地。
新城新生活让三爹发现了一个新的生活常识。社区在广场空地上开辟了晒衣场,一般的居民不会到三十三层楼顶上来。即使是发现了他在天台上种水稻,那也没什么好奇怪好指责的。他的泡沫箱栽培技术,既能节约土地,又能美化环境,还能净化空气。别说种水稻,即使是建个空中花园,造个空中游泳池,那都不算个事儿。
三爹花了两天时间移栽秧苗。泡沫箱铺满了天台,那便是广阔的稻田。他想象一个泡沫箱就是一块稻田,他在稻田里插秧,是每年的四月和七月。
不插“五一”秧、不插“八一”秧,既是那个年代的农业口号,又是提高农作物产量的有效手段。三爹是生产队的种田能手,一年种两季稻,只有赶在“五一”和“八一”前完成插秧,才能跟上趟。农事急不得也拖不得,守住了农时,才能干事成事。哪像现在的铁蛋蛋之流,趁着大好年华睡懒觉、打游戏?猫牙香米饭是张口就来的吗?
提起猫牙香稻,三爹不会忘记自己的父亲——铁蛋蛋的爷爷。在铁蛋蛋的爷爷手里,耿家畈实现了一年三季稻,三爹继承衣钵,成了“水稻世家”传人。一九七一年,在耿家畈建厂的计划流产后,农民还得回到种植水稻的老路上来。那时地少人多,口粮不够吃。报纸上说,海南岛水稻产量高,是闻名全国的种子库。于是公社一位副书记带队去海南岛选种育种,希望背回属于自己的米袋子。
三爹的父亲是去海南岛的人选之一。去时八个,一年以后,回来只剩七个,副书记没有回来。回来的人个个衣衫褴褛,面色晦暗,惊恐,对副书记的下落只字不提。庆幸的是,三爹的父亲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稻种,并亲手培育出了第一批秧苗,于那年的“五一”前抢种到水田里。七月底,收完头季水稻,三爹的父亲叫人不要犁掉稻桩,他给稻田补充水分,施以氮肥。不久,被收割过的稻桩上长出了新苗。又不久,新苗长成稻禾,稻禾抽穗、扬花,结出了饱满的稻粒。虽然产量比母本要低,颗粒较细偏长,但形似猫牙,煮出来的米饭洁白油亮,还自带一股清香。再生稻一种两收,节省了人力,增加了总产量,一时声名鹊起,县里组织学习推广。可是除了耿家畈,在别的地方种植都不成功。
有一个诀窍,三爹的父亲不告诉外乡人,更不告诉县里的领导。那诀窍便是风水。耿家畈属山前丘陵,气候湿润、温和,土层疏松、肥沃,一条谷米河贯穿全村。神奇的是,这条谷米河是三爹的祖先一锄头挖出来的。很久以前,耿家畈不像现在这般光景,那时十年有九年旱,四季水荒。有一天,三爹的先人在劳作的间隙躺在古牳山北坡上休息。他突然听到了一阵流水声。有时像小鸟啁啾鸣啭,甜美悦耳;有时像绸缎鼓风,喜悦明快;有时像浪击石穿,惊心动魄。三爹的先人惊恐坐起,又错愕趴下,反反复复,最后确认这流水的声音来自脚下,于是他抡起锄头,使劲挖了下去。一股清泉汩汩溢出,泉眼如钱眼,逶迤于大地,便成了日后的谷米河。谷米河水源自地下河,出水口常年恒温18℃,适合稻种发芽。到了夏季分蘖期和抽穗期,随着气温的升高,河水可以达到30℃左右,是再生稻最适宜生长的水温。更为重要的是,谷米河水质清纯、甘甜可口,滋润出来的猫牙香稻水灵灵的,像仙女,像神童。别的地方哪有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呢?
三爹不可能将谷米河水引上三十三层高楼楼顶。再说了,开发区建设,早已将谷米河的源头——那个被后人用铁管接驳的泉眼堵死了,在上面建了一条园区互通的主干道。谷米河改道,两岸修建了水泥驳岸和大理石栏杆,河水也不再是泉水,而是雨污合流。枯水季节,大部分河段断流,裸露的河床上堆积着生活垃圾,并点缀着一些顽强生长的蒲草、菹草、旱伞草等水生植物。
三爹灌溉水稻,一靠天公作美,二靠自家的自来水。他像照料婴儿那样,给秧苗浇水施肥、防治病虫害。可以想见,在三爹的侍弄下,那些水稻碧波荡漾、意气风发的样子。三爹还经常搬动泡沫箱子,让墙角的水稻都能晒到太阳。搬着搬着,时间一长,他就搬出了花样,搬出了名堂。三爹将泡沫箱子摆出了富于变化的几何图案。有时是飞机或蝴蝶,有时是房子或花朵。三爹很满意自己的作品。他觉得自己编排得不错,水稻们的表演也不错。
有一天,天台上来了一个小女孩,六七岁的样子。她被眼前的景色震惊到了,大面积的植物拼图,是她看到的最大的儿童画。小女孩问三爹:“爷爷,这是什么植物呀?”三爹说:“孩子,这是水稻。”她又问三爹:“水稻是什么呀?”三爹说:“水稻就是我们吃的大米。”小女孩露出天真的神色,一本正经地说:“爷爷骗人,大米是在超市里长出来的,不是在楼顶上种出来的。”三爹哈哈大笑,笑过之后,脸色凝重。
他从一大箱水稻中,移出一蔸水稻,重新栽在一个很小的白色泡沫盒里。三爹对小女孩说:“你拿回家放在阳台上,两个月之后,就知道大米是怎么长出来的!”三爹以为,他送给了小女孩一个袖珍农场,一个夏收在望的广袤农村。
小女孩兴高采烈地回家了。她把泡沫盒放在窗台外面,又怕被妈妈发现,就将窗帘拉上小半幅,刚好遮住了水稻。按照三爹的吩咐,她经常给泡沫盒里偷偷浇水。一天,妈妈在家打扫卫生,拉开了窗帘,只见一丛水稻头顶墙壁,顶得不能再顶了,才肯低下头去,将劲儿往下使,直叫根系穿透泡沫盒,牢牢地吸附在高楼的外墙上。根须的长度明显超过了稻秆的长度,估计有好几米,仿佛是一幅贴在墙上的稻根艺术浮雕。它的根茎粗壮,显现出被时间和水浸染的锈红色,并由深锈向浅锈过渡,直至渐变为乳白色。像毛细血管一样的根须向墙壁的四周进发,但在总体趋势上,又保持着向下生长的力量。那个狠劲儿、钻劲儿,是一定要抓住大地、钻进泥土里的。
“天哪,这是什么节奏?”妈妈惊呼。
四
三爹的七月,山河、信念、万物都格外昂扬。他在磨刀,一把从耿家畈带来左岭新城的镰刀,被他挂在客厅的墙上,生出了经年的锈斑。那是他的父亲留下来的唯一遗物。现在它被七月的热风吹醒,被七月的烈日锻打,只等三爹的猫牙香稻第一镰开割。
昨天傍晚,三爹与水稻子说完最后告别的话,坐在天台上,沉默了好久。他就那么直勾勾地看着它们,看它们轻摇身姿,看它们齐刷刷地弯下腰去,向他行集体鞠躬之礼。他知道它们也有千言万语,只是开不了口,说不出话来。三爹朝它们挥了挥手,它们弯腰致意的心情更为迫切,将身子贴在地上,像波浪一样起伏。
飞机俯冲的旋风,将三爹和水稻推搡在一起,拥抱在一起。三爹记得小时候,也有飞机从耿家畈的上空飞过。不过那是小飞机,飞得也不高。国家还在古牳山顶架设了一座一人多高的红白相间的航标塔,为过往飞机指引航向。那时只要听到空中传来轰鸣声,三爹就会不顾一切地跑出教室,仰着脑袋,看飞机在天上吐出一条白线。后来村民炸山采石,将古牳山顶削去大半,航标塔也不知去向,但飞机照样飞行。再后来,都是大飞机了。从东边飞来的大飞机在左岭新城开始下降,飞出一道弯后,去天河机场降落。等飞机飞走,风力衰减,呼啸声渐渐消失,三爹扶正了离他最近的一蔸稻禾。他双脚并拢,挺胸昂头,严肃地说:“孩子们,都站好了!”话音刚落,挂在高楼一角的夕阳,咣当一声,重重地沉落下去。它把最后一抹金色留给了稻子,所有的稻粒都穿上了黄金的铠甲,而稻叶混合了金黄色和碧绿色。这时候只见稻叶拽住稻秆,稻秆顶着稻穗,稻穗将稻粒紧紧地抱在一起。它们头顶青天、威风凛凛,组成了整齐划一的空中方阵。那一刻,在一株水稻面前,三爹平生第一次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平淡无光。
他黯然退下,回到家中开始磨镰刀。镰刀在磨刀石上刺啦刺啦地喘息,三爹啪嗒啪嗒地掉着眼泪,眼泪一连串地滴落在磨刀石上,溅起了星星点点的石泥,石泥越来越黏稠,也越来越稀薄。他这个磨刀的阵仗,是要把一把镰刀按进一块磨刀石里,从此世上没有了割稻子的镰刀。没料到,他磨了一夜的镰刀,在灯光下依然闪着坚定的冷傲的蓝光。此时的镰刀已不再是镰刀了,而是收割灵魂的法器。三爹跪在父亲的遗像前,将镰刀举过头顶,拜过三拜,然后用舌头舔舐刀锋,刀锋滴血,冒出热气。他想,这祭过祖先的镰刀,用血淬过火的镰刀,应该配得上长在天上的那些稻子。
天刚刚放亮,三爹就提着镰刀上楼了。这次他选择了电梯,直达三十三楼,再到天台只需几步。他选择电梯的理由,是从昨晚到今晨,他心里总有一种莫名的忐忑,愈逼愈近的紧张与焦灼。他想在最短的时间内,抓紧抢收,确保颗粒归仓。
三爹步出电梯,一股稻草与泥土的气息和他撞了一个满怀。太浓郁了,有些反常。他三步并作两步,朝门洞奔去,铁蛋蛋黑着脸站在那里,用身体堵住了他。三爹扒开铁蛋蛋,眼前的一切,一目了然。天台上光秃秃的,散落着几束稻穗和几坨淤泥。一夜之间,三爹的箱栽猫牙香稻不见了踪影。
三爹气得浑身发抖,他掏出手机,想要报警。那部老年机像个铁砣子,攒在手里,明显承接不住,就像当年地质专家的测量仪器,让三爹的大地震颤不已。报警?给谁报警?他自知在天台上种水稻,并不是公安机关支持的一桩美事,于是拿眼神逼视铁蛋蛋,用手机指向铁蛋蛋,问:“是你搞的?”“爹……”铁蛋蛋刚一张嘴,三爹迎面就给了他一巴掌。铁蛋蛋下意识地抬手一挡,三爹的手机掉在地上,三爹吼道:“婊子养的,是老子碍着你了,还是稻子碍着你了?老子把你养大,你有本事来和老子作对了?婊子养的……”
铁蛋蛋下楼,一头钻进电梯。一不小心,电梯门还是夹住了一句“汉骂”的尾巴。“婊子养的”对三爹来说,也许是一句口头禅,一种愤怒情绪的习惯性表达。但对铁蛋蛋来说,就是血淋淋的亲情撕裂,是代际鸿沟的进一步扩大。如今的左岭,只有三爹那一代人还一口一个“婊子养的”,像铁蛋蛋这样的年轻人,早就换了另外一种说法。愤怒也好、惊叹也罢,轻蔑也好、赞赏也罢,时不时地蹦出一句“卧槽”。脏话不带脏字,个中滋味自己体会。愤怒的铁蛋蛋快速走出电梯,他没有回家。
这以后,有人看见铁蛋蛋白天开出租车,夜晚在网吧打游戏。三爹由他去。铁蛋蛋喜欢的一款游戏叫《地平线5》,他在电脑上飙车,就像三爹在天台上种水稻一样着迷。
十多天过去了,铁蛋蛋一次也没回家。三爹试着打他的电话,总是占线。三爹听老伙计说,出现这种情况,要么是被对方屏蔽了,要么是对方连人带机掉进了传销组织的黑窝。铁蛋蛋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三爹开始紧张起来。他想起几十年前失踪的公社副书记,不禁打了一个寒战。三爹的父亲临死之前,断断续续地说他们八个人在海岛丛林里选种育种,历尽了千辛万苦。副书记在一次寻找野生稻的途中误入沼泽,眼见被草丛伪装的泥淖漫过他的头顶,而另外七个人却束手无策,不能施救。
三爹的父亲让三爹好好种水稻。他哪里知道,如今的左岭新城连一块稻田都没有了,自己在天台上种稻,还被铁蛋蛋硬生生地搞掉了。
如果说副书记当年是误入了沼泽,那今天的铁蛋蛋就是掉进了陷阱。
五
三爹开始了寻子之路。
他寻遍了左岭新城的网吧,又去最繁华的路段蹲守,看看哪辆出租车驾驶座上坐着他的儿子铁蛋蛋,他要把儿子揪下来问问:“婊子养的,汉堡是不是比米饭好吃一些?外面是不是比家里舒服一些?”可是三爹连铁蛋蛋的影子都没看到。
三爹心里说,狗日的铁蛋蛋,从小就在外面野惯了,怎么可能待在左岭这个小地方?肯定是去了大城市。这样一来,三爹就有了去武汉主城区,去深圳、北京、上海的想法。
在去大城市之前,三爹回了一趟耿家畈。他走在高新大道的人行道上,恍若置身科幻世界里。不说沿途平地而起、风格迥异、造型吸睛的高楼和厂房,单说这路,过去农村的羊肠小道变成了现在的双向十四车道,都赶上飞机跑道了。道路两侧,安装有近千盏白玉兰造型的5G智慧路灯。夜幕降临,三爹走在路上,眼前直至头顶,两条盘踞在半空的巨龙,次第发出了耀眼的光芒,壮观无比。三爹无心观景,只想尽快回到老家耿家畈。他像麻雀一样,飞过建筑工地的围挡,飞进曾经的村落。虽说六十多岁了,但长期的体力劳动,练就了一副好身手,类似田径运动中的走、跑、跳跃等动作,他一气呵成地做下来,轻飘得很。
三爹明显感到耿家畈的地形地貌又发生了改变。千万年以前,冰川、山洪冲积形成的低凹田畈,被大型运土车运来渣土抬高了好几米。黄海高程都能修改,这世上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发生?一座村庄沉入地下与一座新城拔地而起是一样的道理。三爹想起搬迁那阵子,除了人民币和随身衣物之外,人们把拿不走的东西、不想拿走的东西统统留在了耿家畈。父亲的那把镰刀,就是他走在半道上突然想起了,折转回去从废物堆里找出来的。
三爹突发奇想:若干年以后,会不会有一支考古队前来发掘耿家畈的遗址?他们怎能考证那些被风挟持的石磙和石磨,碾碎了多少稻菽多少梦?被泥土封存的木犁和铁耙,翻动了多少大地之书多少人间回忆?被改写的田畴和河床,又隐匿了多少炊烟多少鱼迹?
夜已深沉,三爹在一台大型履带推土机前坐下。虽说是建筑工地,但还处于“三通一平”的准备阶段,大批的工人还没有进场,推土机司机已经下班。这个时候,三爹给自己下了一个赌注,他要夜宿耿家畈,再过一次露天纳凉的生活。如果明早他能正常起来,那他第一站就去武汉,继续寻找他的儿子。如果起不来,一定是被蚊虫抽干了血液,再被推土机碾入地下,他回到久别的村庄,被印进了考古画册里。
从来没有像今晚这样踏实、安逸过,三爹只要把头贴近这片土地,就有一股强烈的睡意袭来,在左岭新城患上的焦虑症、失眠症都不治而愈了。耿家畈还是自己的故乡吗?这故乡的土地,覆盖了厚厚一层从他乡异地运来的渣土,但三爹俯下身子,就能与地下的村庄气息相通,安然入睡。
也许是凌晨,也许是半夜,反正是三爹与铁蛋蛋的母亲正在梦里亲密幽会的时候,突然有了一阵嘈杂声。随后一道手电光直通通地杵进了他的眼睛里。他的耳边有呼唤的声音在回响:“爹——爹——”三爹听出了是铁蛋蛋的声音,还像儿时一样亲切。他强行睁开眼睛,眼前的景象把他吓住了。除了儿子铁蛋蛋,还有派出所民警、社区女书记、工地项目负责人。
铁蛋蛋问:“爹,深更半夜的,你咋一个人跑到这里来了?”三爹反问:“儿啊,深更半夜的,你咋知道爹一个人在这里?”铁蛋蛋指了指民警说:“公安机关的天眼系统既可以抓捕坏人,也可以帮助好人。你以为你翻进建筑工地,人家就不知道了?”三爹说:“我又没干偷鸡摸狗的坏事,怕什么?快说,这些天你去哪儿了?可把老子急死了。”
铁蛋蛋把自己最近的经历一一道来。他说:“我给‘萝卜快跑’当测试员,不过呢,目前又失业了。”“‘萝卜快跑’是个啥东西?”三爹不懂,但仍不失时机地要教训铁蛋蛋一顿,“又失业了?儿啊,你就这桩不好,除了打游戏,啥事都干不长。”
三爹哪里知道“萝卜快跑”其实是一项无人驾驶出租车业务。作为测试员,铁蛋蛋只用坐在驾驶室里测试各项数据,必要时处理道路紧急情况。目前,武汉街头已经投放了很多这样的出租车,正式为市民提供出行服务。测试任务完成了,铁蛋蛋也就理所当然地失业了。
“我不能老坐在车里测试啊。”铁蛋蛋还特别提醒三爹,“就像你,不能老当农民啊!”
三爹想起寻找铁蛋蛋的情景。的确,高新大道、左岭大道宽敞开阔,前段时间真有不少车顶上架着摄像头的小车跑来跑去。有时车里有人但不是铁蛋蛋,有时车里没人但车子自己会跑。三爹当时还挺纳闷,没人驾驶的汽车,也能自己跑?经铁蛋蛋今天这么一说,原来“萝卜快跑”就像滚萝卜下坡,不要人推,自己会跑,一直往前跑。
三爹还想对铁蛋蛋说点什么,站在一旁的社区女书记拉住了他的手:“老同志,是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到位,事先找不到水稻的主人,没法同您商量,就把‘天空稻田’清理了。我们向您道歉!”
三爹惊讶地看着铁蛋蛋说:“不是你搞的?”铁蛋蛋笑了笑说:“爹,你当时那么激动,还打了我,我都来不及解释。我一个人哪有那么大的力气?是城管中队的无人机巡查小分队发现了你的秘密,才联合社区连夜处理了你的水稻。人家可是事先投放了宣传单和整改通知书的哦,也许是天黑,你没有发现。你要是不服,还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嘛。”三爹说:“算了,天台本来就是公共区域,我不该在高层楼顶种水稻。”
铁蛋蛋掏出一部新购的智能手机,犹犹豫豫,想递给三爹。社区女书记接过手机,将铁蛋蛋和三爹的手拉在一起,说:“老同志,您想当农民就当农民吧,手机上也能种水稻。”
铁蛋蛋想得周到,他在新手机上下载了一款游戏软件——《天稻之城》。这是一款以种田和养殖为主要玩法的动作RPG游戏,玩家通过线上种田和养殖提升等级,建设自己的梦想家园。
三爹抓住手机,像抓住了一个能定天定地定乾坤的铁砣子。
从此后,他像一个对游戏着迷的小孩子,每天在自家的阳台上玩手机。他最后的等级是丰穰之神,司掌播种、收成、牧养和繁殖。玩着玩着,三爹乏味了,竟在自家的阳台上又开始了种植,那是一株白菜、一棵辣椒、一丛香葱,当然还有一兜水稻。清一色的德化袖珍白瓷花盆,美得很。
三爹坐在阳台上,美美地睡着了。他梦见社区女书记邀请他去农场体验生活。他说不必了,现在躺在家中就能用手机“种植”,播种、插秧、收割一键搞定。三爹笑醒了。睁眼一看,东方既白,太阳更新,大地更新,自己又是一个快乐的庄稼人,左岭新城是一捧刚刚冒尖儿的种子。
【作者简介】杨中标,湖北武汉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水利作家协会理事。作品散见于《诗刊》《解放军文艺》《小说月报·原创版》《长江文艺》《中篇小说选刊》《诗选刊》等刊物。出版长篇小说《你竟敢如此年轻》《去天堂使坏》《青春是一条地下狗》等三部,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光纤之路》一部。部分中短篇小说、诗歌被《中篇小说选刊》《诗选刊》及各种文学选本选载;中篇小说《石头是石头的纪念碑》获评《小说月报·原创版》二〇二二年度佳作;长篇小说《去天堂使坏》入选甘肃省“农家书屋”重点图书推荐目录。
责任编辑 梁乐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