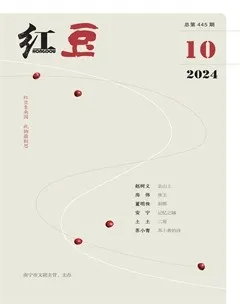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叶子突然说:“你不是本地人吧?”安娜说:“你怎么知道的?”叶子说:“你说话的声音特别好听,和本地人不一样。”安娜说她是常德人。“是嫁到这里的吗?”“被骗来的。”叶子摇摇头,表示不相信。安娜说:“是真的,我是恋爱脑,傻,人家一忽悠,我就跟着来了。”“因为爱情?”安娜说:“我以为那是爱。”安娜不愿回首往事。叶子关心地问:“怎么啦?”安娜说:“没什么,我离婚了。”这是开始交换秘密的节奏。好吧,安娜想,索性吐槽一下前夫。
安娜说:“他很帅,关键是爱得热烈,他说他可以为我做任何事,他强调任何事,包括杀人,只要我说一声。我哪会让他杀人?他说我让他跳河他也跳。我开玩笑地问不会是骗我的吧,他二话不说,就跳进湘江,差点淹死。他不会游泳,是一个路人把他救上来的……我以为那是爱,后来才知道不是。”
叶子说:“他太极端了,你不觉得可怕吗?”安娜说:“鬼迷心窍。嫁给他后,然后就来到了黄姚。”“黄姚挺美的。”安娜与叶子碰杯。“瞧,他走了,我留了下来。”叶子问:“他家暴吗?”安娜不说话,停顿,她在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叶子按住她的手,给她安慰。安娜摇摇头,讽刺地说:“那不是家暴,是爱!这是他说的,他说他爱我,所以……”“不说了,不说了,我晓得。”
叶子与安娜碰杯。这时候,安娜胸中翻涌着愤懑,如同涨潮,停不下来,必须朝禁锢的堤岸扑去,哪怕撞得粉身碎骨。
安娜继续往下说:“他下手很重,我快被他打死了,女儿吓得浑身发抖,说不出话……很奇怪,我竟然活下来了……他跪下认错,写保证,说他多么多么爱我,多么多么爱我……狗屁!之后,又重复这个过程,打,认错,打,认错,打,认错……最后,我们就离了。”
“他同意离?”“他不同意,他有个情人,情人逼着他和我离,他才离的。”“他又结婚了?”“结了,和那个情人。”“真是个浑蛋。”
安娜说:“其实他挺可怜,从小没有母亲,他父亲老揍他,他才变成这样。”安娜不是为他开脱,她是在鄙视他。瞧,他就是个心理残疾的人。只有鄙视他,她心里才能好受点。
叶子说:“也不能把什么都归咎于原生家庭。”她晓得这样归因大都不会错。原生家庭,这个熊熊燃烧的炉子怎能不制造炉渣呢?“不过,自己的责任呢?你没一点成长吗?”
安娜说:“你呢?你一定很幸福吧?从容颜上就看得出来。”她心里说,该你了,如果你把我当朋友,就也说点秘密出来。
叶子冰雪聪明,马上领会,喝口啤酒后缓缓说道:“我,还可以,他有情人,我也有,我们相安无事。”“开放式婚姻?”“算是吧。”
她们相视一笑,莫逆于心。尽管叶子说得笼统,不过不像假话。现在她们亲近多了。碰杯。有人在谈论涂鸦的事。涂鸦出现在安娜店铺墙上——《小女孩与红气球》。叶子说:“你真不知道是谁画的吗?”“真不知道。”“班克斯。”叶子说。
班克斯并非只在英国涂鸦,他在全世界涂鸦,他来中国涂鸦也不奇怪。为什么选黄姚?黄姚美啊,根据毛姆的小说《面纱》改编的同名电影曾在这里取景。她看过那部电影。男女主角都是大明星。黄姚的美景在电影里如梦如幻,美若仙境。班克斯大概也看过《面纱》。他喜欢这里,所以就来了。来了,涂鸦,就这么简单。完全说得通,合情合理。
安娜去看那幅涂鸦。涂鸦还是那幅涂鸦。不,对她来说,涂鸦不再只是涂鸦。涂鸦是个宝。她从不相信天上掉馅饼的事,但这一次,似乎不一样。
回到店里。
胖妞说一个陌生男人说要买她的店。
不卖。她没想过卖店。她的生活全靠这家店,怎么会卖呢?最初苦苦支撑时她都没卖,现在收入稳定了她更不会卖。
胖妞说:“我告诉他你不会卖,他不走,说要见你,和你谈,喏——”
“你要买我的店?”
“你开个价。”
安娜看着男子。他是哪根筋搭错了?后来她知道这个男子名叫柏林。这是什么名,他怎么不叫巴黎呢?
柏林说:“实话实说吧,我看中的是涂鸦,不是你的店。我要你的店干什么?”他愿出二十万元买她墙上的涂鸦。
二十万元!她没听错,是二十万元,千真万确。
她有些飘飘然。“瞧,你这个俗人,一幅涂鸦就弄得你心猿意马。”“可恶。”“你的自我哪去了?”“这时候说什么自我?说说涂鸦吧。”“你是关心涂鸦还是关心钱?”“我关心钱好吧,我就是个俗人,你想让我有多高尚?”她身体里有两个“我”,这两个“我”一个高雅,一个庸俗,总是争吵不断。
和胖妞相处时,庸俗的“我”主导着她,她和胖妞能聊半天八卦,快乐得不得了。和常靖在一起时,高雅的“我”主导着她,他们谈读书,谈文学艺术,谈不着边际的话题,也很快乐。当两个“我”都不占主导地位时,她就有些恍惚。
安娜和常靖是在读书会上认识的。那时他们都有家庭。他们没讨论过婚姻。相爱就要结婚,那太俗套了。他们不考虑。他们看重自由。自由?好吧,看看自由会带来什么。突然有一天,安娜的丈夫看到她与常靖的聊天记录,认定她已出轨,打了她。她没告诉常靖。这是她自己的事,她自己承担。之后,她疏远常靖,不再与他联系。她不再参加读书会,常靖发信息她也不回。她还想维持婚姻,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这没问题,丈夫没提离婚。丈夫还经常在微信朋友圈秀恩爱。一边秀恩爱,一边家暴。一次又一次。每次家暴后,丈夫都会低声下气求她原谅。丈夫说他爱她。正因为爱她,才打她。他妈的,这是什么狗屁逻辑?她已不爱丈夫。同时,她发现丈夫有情人。好了,这下扯平了。她原谅丈夫,希望丈夫也原谅她。丈夫冷笑一声,说:“这能一样吗?”他照旧家暴。她在家里毫无尊严。丈夫不光打她,也打女儿。他怀疑女儿不是他的种。他要做亲子鉴定。她不阻止,想做就做去吧。丈夫却又不做了。她和女儿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中。还维持婚姻吗?别天真了。她提出离婚,丈夫不同意。“想离开我,没门儿。”丈夫威胁要杀了她和女儿,“你知道我干得出来。”她知道他是一个极端的人。她被吓住了。她循规蹈矩,许可丈夫拥有情人。如此退让,换来的是什么?家暴,变本加厉的家暴。最终,拜丈夫的情人所赐,丈夫同意离婚。她担心丈夫与她争夺女儿,可丈夫为了另组新家,根本就没要女儿。
要给常靖说这件事吗?
二十万元啊,二十万元!谁会和钱过不去呢?她从不鄙夷金钱。有钱可以任性。这是真的吗?她上网一查,班克斯的涂鸦值一点六亿元人民币。噢,天哪!一点六亿元!一点六亿元,一点六亿元,一点六亿元!这个数字在她头脑中轰隆隆炸响,如同滚雷。
不要说一点六亿元,也不要说几千万元,给她几百万元就行。柏林出到二十万元,要是美元,她就卖了。她会卖吗?要不,拍卖吧,价高者得。公开,公平,公正,童叟无欺。
老宋要清理涂鸦,安娜不让。这哪是涂鸦,这是钱啊,钱!一点六亿元!怎么能清理呢!老宋说他得听管委会的。安娜强调是她的墙!她的权利!她的决心!看那气势,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店主不让清理,他能怎么办?他只是一个小小的临时工,他敢和谁硬来?好吧。好吧,好吧……老宋夹着尾巴逃走了。那萎靡的背影,像一条被打断脊梁的狗。
“那家伙会不会是个骗子?”“他骗什么?”“我哪知道?我又不是骗子。”胖妞说,“小心驶得万年船。”
“我还能骗你不成?”柏林说。安娜将信将疑。
“我们是朋友吗?”她说。叶子说是,又说她没遇到过这种情况,遇到也不知道该咋办。
安娜走,叶子跟着。“你不去采访了?”她问。“我正在采访。”叶子说,“标题我想好了,叫……”
景区又有两家店铺的墙上出现涂鸦,还是班克斯风格。安娜让叶子去采访另外两家,叶子说已经采访过了。“他们和你一样,知道涂鸦值钱,开心得不得了。”
安娜哼一声。开心什么?她现在只有烦恼,除了烦恼,还是烦恼。
“谁没有烦恼呢?”叶子说。她羡慕安娜,自由自在。她说自己哪儿哪儿都不自由不自在。安娜说:“开放式婚姻,你还不满足,那你想要什么?”叶子说:“我也不知道,看上去我没有理由再要求别的,可是鞋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安娜猜测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叶子说:“他从来没夸过我。”“这算什么事?不叫事。”叶子不这样看,她说:“我们很久没有那个了。”“哪个?”“你知道的,坏。”安娜问:“你想吗?”叶子说不想。“假话。”“和他不想。”“这就对了,你还是个正常人。”叶子说:“我们同时在一个屋子里我感觉不自在,哪儿都不舒服。”“是啊,谁也不干涉谁,听上去不错,彼此尊重,都保持自我。可是,我们像两个陌生人,冷漠的陌生人。我在家里感觉不到温度,冷冰冰的,那个家,如果还能叫家的话。”安娜说她理解这种感受。
这个下午,她们在不知不觉间成了闺密。叶子说她晚上不回去了。安娜问:“你要去哪儿?”叶子说约会。安娜拍一下叶子说好好享受吧。叶子走后,安娜便也蠢蠢欲动。真是奇怪,暧昧也会传染。她给常靖发微信,约见面。常靖秒回:“恭候大驾。”
常靖调到黄姚来工作。他在黄姚没房子,每天都回贺州住。车程一小时,不算远,也不算近。常靖来黄姚之后,他们还没有约会过。
常靖在宾馆开房,把房号发给安娜。安娜直接上去。她清楚,他们大概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常靖要回市里。她也要回家。她自嘲,这就是一次快餐。
安娜想了解管委会对涂鸦的态度。她如果不能很快卖掉,涂鸦会被清理吗?常靖没有直接回答,他让安娜猜。猜个屁,安娜说她猜不着。常靖点燃一支烟,满足地吸一口。她也拿过来抽一口。平时她不抽烟。这时候抽,是共犯。她把柏林要买涂鸦的事说了。常靖笑而不语。“你笑什么?”“我笑你在做白日梦。”“我靠,你怀疑我?”“不是怀疑你,是怀疑柏林。他脑子进水了,让门板挤了,还是叫驴踢了?”安娜问:“什么意思?”常靖说:“他像傻瓜吗?他逗你玩的。”安娜说:“对他有什么好处?”常靖说:“这你得问他。”安娜弄不明白常靖的话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玩笑的。她看着常靖。常靖怡然自得地抽着烟。他向空中吐出一串烟圈。她不会吐烟圈。她学过,但没学会。还是回到涂鸦的话题上。“管委会会清理吗?”“会。”常靖说。她猜也是。规章制度中有一条,不能乱涂乱画。那可是二十万元钱!她昨天就应该做出决断,二十万元卖掉,一了百了。
他并没做错什么,你何必给他甩脸子?突然想到叶子,她诡谲地一笑,也不知这家伙在和哪个男人鬼混。她头脑中出现一些不宜描述的画面。叶子的婚姻,唉!
“……人们真有想象力啊。”安娜说。
“那班什么斯的怎么不来我的墙上画?”胖妞说。她有些愤愤不平,“这太不公平了,真是的。”镇上出现那么多涂鸦,多得数都数不清,唯独她的墙上没有。她的墙不平吗,不光滑吗?
“说不定明天早上起来,你的墙上就会出现一幅涂鸦。”
“借你吉言……给我来个价值二十万元的涂鸦,让我也高兴一下……那些涂鸦的家伙躲在哪里?别让我看见,让我看见有你好看的……老鹰拎小鸡也要把你拎过来。画,画,画,画出二十万元,否则别想走……”胖妞陶醉在对财富的狂想中。
“那个人呢?”“哪个人?”“就是要买画的那个。”“柏林啊,鬼知道钻哪儿去了。”“胖妞说他可能在和别人谈。”“让他谈去吧。”
叶子又来了。安娜见到叶子特别开心。她们掏心掏肺,赤诚坦率。现代人都穿着层层铠甲,刀枪不入。她们俩是例外。安娜意味深长地说:“满面春光啊。”叶子说:“你不也一样嘛。”她们相视一笑。
叶子采访过常靖。她和安娜没有秘密。安娜说出常靖的名字后,她就去采访了。她很好奇。她想看看常靖是个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人?”安娜问。“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叶子说,“想法多,敢冒险,不服输。”“看上去不像。”安娜说。“你是被他的温柔迷住了。”叶子说。“他很懦弱。”安娜说。“那是假象,他有另一面,你肯定看到了。”叶子说。“只停留在思想层面,他不会付诸行动。”安娜说。她了解他。
安娜已经多日没见常靖了。他说忙。她信。他从来不会拒绝她。原来也有忙的时候,他会解释,取得她的理解。现在,他只说忙,就没下文了。看来是真忙。不只是忙,还有压力。但愿只是工作方面,不是家庭方面。
她私下问叶子:“你会喜欢常靖吗?”叶子说:“喜欢又怎样,不喜欢又怎样?喜欢你也不会让给我,不喜欢你该说我没眼光,我怎么回答能让你满意?”“如实回答。”“不,这个问题我拒绝回答。”“我知道了。”“你知道什么?”“你脸红什么?”“我哪儿脸红了?胡说。”
安娜给常靖发微信:“听说你有压力了,要不要放松一下,见个面如何?”
过了一会儿,常靖回三条:“忙。”“宾馆爆满。”“我联系你。”
他们在常靖的车里见面,车里安全。他们没有玩车震。会被人看到的,那样多尴尬啊。亲昵的动作是有的。安娜想帮助他缓解压力,这不是亲吻和小动作能解决的,她想和他聊聊。都是工作方面的事,他不愿聊。“好吧。最近降温。”“是的。可是不觉得冷。忙起来就忘了冷。”“是这样。”古镇反常的热闹,让他们误会了天气。“人气与天气,哈哈。人气影响天气,天气没有影响人气。”他说有人告他破坏古镇风貌,还有人说他胡闹,这些都是因为景区火了。“噢,这都是你的功劳。这怎么行?必须给你找点毛病。”他不知不觉吐槽起来。说过不聊工作,他自己倒聊起来了。他说,好在有主任支持,主任是个有开拓精神的人,他很佩服。每年的作家采风活动都是主任组织策划的。看着花了不少钱,其实赚了。每个作家都写了文章。古镇,在他们笔下,有说不尽的好。安娜不关心那些。文章都上墙了,她读过。很美。是的。可她更关心当下。班克斯,她又想起班克斯:“这么说,涂鸦不是班克斯的。”怎么可能呢?安娜心里也这么想,可她不愿承认。万一就是班克斯的呢?常靖说:“全世界范围内,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在城市公共场所墙体或街头墙壁上乱涂乱画都是违法的,都会被清理,班克斯的涂鸦也不例外。你上网搜一下,班克斯的涂鸦有几幅保留下来了?班克斯自己拍照,立此存照为证,你看到的都是照片。班克斯的涂鸦之所以值钱,就因为少。物以稀为贵,多了就不值钱了。像古镇这么多,全世界都罕见。我猜……”安娜说:“你也不要压力太大。”常靖说:“还有别的压力。”“什么压力?”“不说了,说好不聊工作的。你的生意怎么样?我猜猜,肯定没少赚吧。”安娜说:“拜你所赐,游客这么多,想不赚钱都难。”“哈哈,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以后每年一届,搞成一个涂鸦界的盛典。这是流量时代,有流量就有生意。得感谢班克斯。班克斯如果来黄姚,我们会给他颁发荣誉市民称号。要搞得隆重。”
“来了很多外国人。”“假如一个叫若泽的站出来说他就是班克斯,人们会信吗?““没人信。”“这里有个逻辑陷阱。说自己是班克斯的,一定不是班克斯。说自己不是班克斯的,倒有可能是班克斯。问题是全球八十亿人都说自己不是班克斯,你如何从中找出班克斯?瞧,这可不是一般的难。”想到这里,安娜自己笑了。看来班克斯是指望不上了。
“柏林图什么呢,是寻开心吗?”安娜不再相信柏林。
安娜与前夫已经形同陌路,如果不是女儿,他们一辈子都不会再联系。前夫让她害怕。前夫极端的爱——狗屁的爱——让她恐惧。他的暴力总是以爱的名义进行。“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然后揍你揍你揍你……”她想起他就战栗,心是疼的,像插着一把刀。至于常靖,温柔、宽容、有趣,时不时还会给她惊喜,可要爱他就是飞蛾扑火,她不敢爱他。
一夜之间,小镇所有涂鸦都被清理了。《小女孩和红气球》消失了。安娜的生活又归于平静。二十万元,还是别提了吧,安娜当然没有得到。别说安娜,整个小镇的许许多多的涂鸦,有谁卖掉过一幅吗?那个曾经说要买安娜涂鸦的柏林,鬼晓得去哪里了。
她们见面已经不再谈论班克斯和涂鸦了。
安娜问:“离了吗?”叶子说:“没有,不急。其实离和不离一样。”“你会和常靖结婚吗?”“不会。”
【作者简介】赵大河,一九六六年生,河南内乡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品见于《人民文学》《十月》《中国作家》《花城》《山花》《美文》等刊。作品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转载及收入年选和其他选本。出版有《隐蔽手记》、《北风呼啸的下午》、《我的野兽我的国》、《侏儒与国王》、《燃烧的城堡》、《时间与疆域》(六卷本)、《你可以飞翔》等多部。曾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杜甫文学奖、曹禺杯戏剧奖、《中国作家》短篇小说奖、河南省优秀文艺成果奖、《莽原》文学奖、金盾文学奖、蔡文姬文学奖、师陀文学奖、《广西文学》优秀作品奖等。二〇二一年荣膺中原文化名家。
责任编辑 梁乐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