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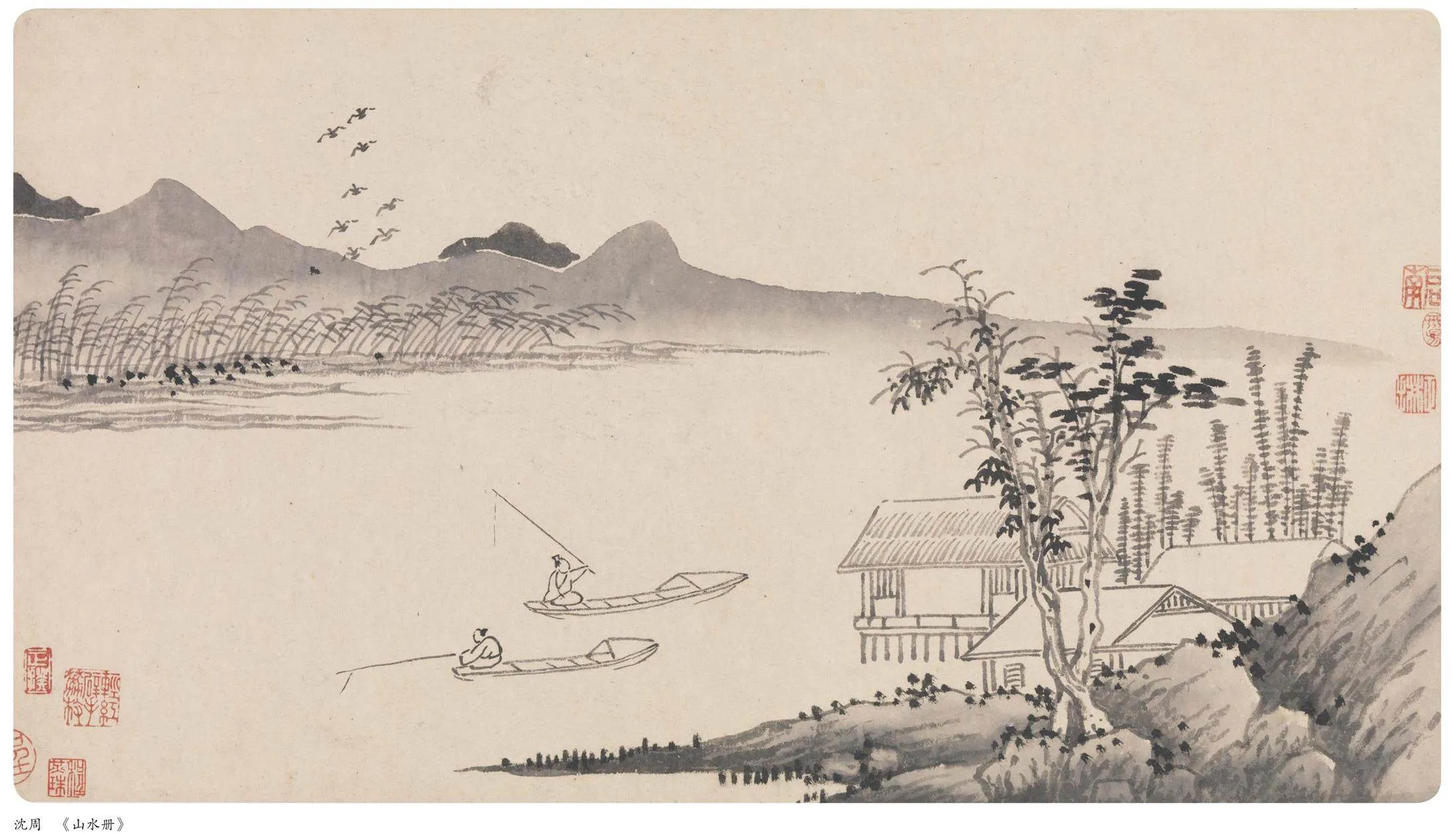

前 言
《论语》一书,由《学而》开始,首先讲述孔门为学问的精神和宗旨。跟着便讲《为政》,点出学问的致用,再以《八佾》为孔门维护文化的目的,《里仁》则为孔门学问的极致。我们都知道代表儒家传统精神的孔子和孟子,是以仁义为学问的中心。孔子特别注重于仁,孟子特别发扬于义。什么叫作仁呢?几千年来的大儒,各种解释,纷纭莫定,至今犹难确定其界说。举其荦荦大者来说,依汉儒训诂释义的意思,仁字从人、从二,大意是指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学问。所以到了唐代,出了一个古文文章的宗师韩愈,他自谓继孔孟的绝学,作了一篇《原道》的大文章,说出“博爱之谓仁”。于是后世言仁,大多宗奉他的意思来解释了。
宋代苏东坡赞叹韩愈说:“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简直把韩愈的道德文章,比拟为孔子了。其实,韩昌黎的学问,究竟是否纯儒,大是一个问题,我们姑且不去讨论他。至于他的成功且享大名,除了他的文章写得好,当时极力提倡恢复古文,以革新六朝以来的文运以外,他能特别享有千古盛名的,就是上书《谏迎佛骨表》的一件事。但他也因此而遭贬,因遭贬而享更大的名望。等于现代人写文章、闹运动、大骂打倒孔家店而成名的,都是同一幸运。这种是非得失,我们也不去管他,至于他说的“博爱之谓仁”,却与孔门相传的学问心法有所出入了。
我们都知道孔门的弟子中,孔子独许颜渊以知仁,他在《论语·述而》篇中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那岂是博爱的作用?如果是“博爱之谓仁”,那就等于说,苟欲仁时,博爱就来了吗?而且孔子为什么又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呢?他为什么又告诉颜渊仁的纲目,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呢?由此可见仁的境界,孔子已经明明白白地指出来了。所以他说颜渊“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了。当然仁发为作用的时候,自然也就会爱人以德,《易传》曰:“安土敦乎仁,故能爱。”可是却不能硬说爱人便是仁的极致,否则,和孔门的传习就有许多梗隔不通了。
到了宋代的儒家,有理学家们的兴起。他们也说,为了继孔孟以后的心法,对于仁的解释,又是另外做注解的。有的是拿中国古代医书上的话来做反证,说麻木谓之不仁,所以仁便是心性灵明不昧的境界。又说,如果核之有仁,所以仁便是心性的中心,中心就是中和,也就是中庸之为德。如果我们根据上面简述的两种解释来说,果核之仁,都是两瓣相合,中心是空洞无物的,两瓣如阴阳的二合,所以人能效法天地间阴阳的和易调顺,中心空荡荡的,寂然不动,灵明不昧,那便是仁的境界了。这些道理,的确很高明,也有相当的理由,其实这种说法,由于已经融合了佛家、道家,才能画出仁的一个面目。所以理学家们专长此道而发展之,就成为心性玄奥的微言了。
我们说了许多,既然知道孔门学问中心的极致的确是一个“仁”字,那仁又究竟是如何的境界呢?这就要好好研究《里仁》一篇了。所以我说此篇是由《学而》第一层层剖出的中心。仁是有体有用的,心性的静相是仁的体,所谓“寂然不动”,必须于静中养出端倪的便是。而思想言行是仁的用,所谓“感而遂通”,必须于行事之间,具有一片孝悌忠诚仁爱之心的便是。
那么,你就可以看出如汉、唐诸大儒的讲仁,大体是偏重致用于行为之间;宋、明诸大儒的讲仁,大体是偏重于心性修养之道,殊途同归,是非一致。以后能明体而达用,建大功,立大业,己立而立人,己达而达人,措天下于衽席之安者,只有以极大的愿望,寄予后起之秀了。
什么是仁
《里仁》的“里”字,但从文字的解释,里就是道理、村里的意思。历来儒者们的解释,里便是居处的地方。
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有的解说是,选择居住的地方,一定要选择一个仁里而住,否则,就是无智慧的人。如果的确只是这个意思,那么,孔子也只是一个专拣好环境住的人了,何以他在感叹世道人心之余,就要去居九夷,又要乘桴浮于海呢?九夷岂是仁里?海外便是仁乡吗?那就难怪当国家遭遇衰微危难之时,只有出国的一途了。
里当然是居的意义,换言之,那是说,长住在仁的境界里,才是学问的真善和至美啊!所谓学问,就是先要择善固执而从,要达到仁的极致才对。因此他说,你如不能择善固执,达不到仁的境界,那便是不智,也就是没有真智慧。
所以这一则话当中的“里”与“处”两个字,就有士君子立身出处的意思存在。里仁,便是立身要随时随地在仁的境界中;处仁,便是出处和处世,也要随时随地在仁的境界中才对。如果做学问修养的功夫,不能择善固执,达不到至善至美的仁的境界,那对学问,就可以说没有真知灼见了,所以下面跟着便提出: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这就是指出,唯有学问修养到达常在仁的境界,才能长久自处在约、乐、安、利的情况里,才可以做到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地步。学养没有到仁的境界的话,是绝不可能做到的。“约”,是穷困的环境,外面处处受约束,内在也要随事俭约,包括孟子所谓贫贱不能移的贫贱之意。“乐”,是春风得意的通顺环境,包括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的富贵之意。所以只有达到仁的境界的人,才能随时随地安于其仁,也可以随时随地利用仁道而安身立命。这样,才是人生境界的真安乐、真利益,名利富贵只是身外余事耳,何足论哉!何足论哉!
例如范蠡批评越王勾践,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就是不仁的明证。宋代名臣文天祥,当他没有起义勤王以前,出任庐陵太守的时候,沉醉在声伎歌舞之中,一旦为国勤王而起事,立刻摒除嗜好,备尝艰苦危难而不变节,这就是求仁得仁的证明。明末清初的大儒李中孚,隐居讲学于山西五台附近,贫病交迫,康熙虽然御驾亲幸山西,屡次召请,他也不肯变节出山投向,这也是求仁得仁的证明。所以说学养已到达于仁的境界,便可安住于仁而不变;如果学养没有到达仁的境界,只要知道了仁道的精神,也可以用以安身,卓然特立独行而不拔了。同时又说: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这里的“好”,读作爱好的好;“恶”,读作厌恶的恶。到此才说出学养达到仁的境界的人,才真能推己及人,而有知人之明的智慧。所以只有仁人的待人处世,在好恶之间才能够做到真实的爱人以德,并且厌恶其所以不能为德,否则,都是由于一己的私心利害,来权衡评判他人,根本没有中心的标准。然而,仁者的用心,固有好恶是非的存心,但他斤斤计较好恶于胸中吗?那所谓的仁,也就不过如此而已,何必要赞叹什么君子之仁呢?到此,便必须点出下文孔子的一则话,方才显见圣人境界的伟大处。
仁者的行径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这句话,因为一个“恶”字可以读作名词的善恶之恶,或动词的厌恶之恶来解,所以包含两个意义。第一,是说如果一个人真能学养到了仁的境界,而且长久养志于仁道之中,对于恶人,也只有以仁而化之,根本就不会有厌恶恶人的心情。第二,为什么会做到不厌恶他人呢?因为仁人的用心,根本就无恶意,只有一片祥和之气,哪里会以他人之恶而厌恶之呢?这恰恰点出仁者待人接物的一团祥和的风格;如果只做善善恶恶的一面来看,未免会埋没圣贤的用心了。
例如宋代名儒司马光,虽恶王安石之为人,而于大节处,却不深恶痛绝之。神宗欲用王安石为相,问之司马光,他就说:“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他又写信给王安石说:“谄谀之士,于公今日,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将必卖公自售矣。”虽王安石很不高兴,但司马光还是一味地爱护怜惜他,这也是大儒仁者用心的楷模。
由于从上文所说仁者不厌恶人的第一观念和衔接下文一则来看,再扩而充之,就可见孔子所说的仁的境界非常地渊深。那就是说,学而达成仁的境界者的用心,不但不厌恶人,而且也不厌恶现实生命过程中的生活。他说,富与贵,是人人所要求的目的,大家都想争取,但从一个仁者的用心来看,如果不合正道而取得富贵,他是绝不肯要这个富贵的。贫与贱,是人人所厌恶的,大家都想逃避,但从仁者的用心来看,如果不合正当的方法脱离,他是绝不肯轻易走出贫贱的环境的。总之,君子的儒者,即使穿衣吃饭之间,也不肯片刻违背仁的境界;即使建功立业,也是在仁的境界中完成的;纵然颠沛流离,也会安贫乐道在仁的境界中的。所以提出: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造次”,是忙忙碌碌、有所作为的状态;“颠沛”,是艰难困苦的状态。到此,需将仁者待人接物之间,不立涯岸,不固执好恶,但把养得仁心为学问第一要义的道理,作一结论。所以五代大儒陈图南虽然有心用世,但他感觉事不可为之时,便作诗明志,他说:
十年踪迹走红尘,
回首青山入梦频。
紫绶纵荣争及睡,
朱门虽富不如贫。
愁闻剑戟扶危主,
闷听笙歌聒醉人。
携取旧书归旧隐,
野花啼鸟一般春。
从此他就高卧华山去了。等到宋太祖平定以后,再来召请他,他又再三恳辞,谢表自称:
数行丹诏 空劳凤使衔来
一片闲心 已被白云留住
因此他的学问三传而到邵康节,又是一个死守善道、不肯随便出山求富贵的人。
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这是说,我没有看到一个真正好仁的人会厌恶一个不仁的人。你能够做到好仁,当然是了不起,好到无以复加了,可是你如果厌恶别人的不仁,那怎么能算是仁呢?倘使你会厌恶他人的不仁,那是把不仁的态度,加到别人身上去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这当然是不可以的。于是孔子又似感叹地说,世上哪有人真肯努力追求仁的境界呢?也许有吧,可是我并没有见到过啊!由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对仁道的难得,是如何地沉痛了。就以他的弟子们而论,他也仅得一个颜回,可以传他仁道的衣钵。其余的,对学问各有所长,各自成就了一面,但对于仁道,都还谈不上,不幸颜回又短命而亡,所以孔子就更伤心了。
如何修养到仁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这是说,如果能去掉尘俗的观念,而志心于仁道的学问,就是早晨听到这个道理,晚上就算死了,也可算是不虚此生了。这句话,从文字的表面看来,未免过于强调,如从身入其境的人看来,就会明白这句话真有无比的仁心厚德!因它同时在说明仁的道理,就是反身而诚,并且明得心地灵明体用的学问。如能心志不纷,常住在仁的境界中,又有什么生死可畏惧呢?生之与死,有如旦暮,“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死生如朝暮的变化,仍然不离于仁心,又有何可畏?如果只从死生的现象上看,似乎有生灭的过程。若能从得仁心之体用来观生死,那些现象的生死往来,万变不离其宗,方知此心之体,自有其不变者存焉。它既不落在生死之中,也就不必了什么生死啦!所以《易传》说,“通乎昼夜之道而知”,知个什么呢?就是知道生死变化犹如旦暮,始终不离于仁的境界而已。
上面说了许多勉励学以致仁的话,那么,哪一种人才能从事仁道的学养呢?而且如何才算是实行仁道呢?于是就提出: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他说,讲到志心于仁道的人,有一个很好的考验,如果他要志心于仁道时,连生死都无所惧,哪里还会贪图生活的舒适和享受,讲究好的吃、好的穿呢?如果不能领略到菜根香、布衣暖的人,根本就无法和他谈什么仁的学问了。所以下文便说,凡是君子之儒,处身于天地之间,心里根本就没有坚持哪种事物舒适,哪样事物不好。仁人的用心,在可与不可之间,并不是以个人的贪欲为标准,只以义理的相宜不相宜做比较。如果是义之所在,就是火坑苦海,也要去跳,还有什么选择好衣食的余地呢?故在此就说: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那么,义之与比,大体上又比较些什么呢?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他说,如果是君子的人,他的胸襟怀抱,随时随地,只有一个如何建立德业的念头;倘是一个小人呢,他的胸臆之间,只是一个为财产利益打算的田舍翁,日夜都在计划谋求田舍。再说,君子的人,随时随地怀惧天刑;一个小人呢,他就只顾到目前利益,贪图小惠,得点好处就算了,哪管后果如何!所以:
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如果只从利益打算来做人处世,结果多招怨尤,就是自己的内心也会多生怨悔的。再说,社会上到底君子少而小人多,如果不爱人以德,只是以惠来结交,那就如俗话说的“善门难开”,结果反会多招怨尤。
所以宋代名臣王曾在朝廷进止有常,平居寡言笑,一般人都不敢向他求私事,所以对于人的升迁进退,谁也不得而知。范仲淹尝向他说:“明扬士类,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独少此尔!”王曾便说:“恩欲归己,怨将谁归耶?”范仲淹听了,就深深佩服他的德行和器识。到此话头又需一转,再说志心于学养仁道的人,假使有机会,要他担任为国家天下的事,他绝不会高兴得忘穿鞋子,马上就驾车去上任的。他必定衡量礼义的轻重得失,然后还要推让其他贤能的人去做,否则,还谈什么礼乐的教化呢?所以: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这里所谓的礼,就是文化教养的精神,也是孔门学问的目的,所以在这一段结论中,仍然引用如《学而》篇中的话说。
仁的体和用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他说,学养真能到达仁的境界的人,不怕在社会上没有位置,应当怕自己没有建立可以贡献人群的学问。当然更不要怕没有人知道你,了解你,只要你真为学问,自然会求仁得仁,何必一定要人知道!况且你真有了学问,自然会有可知之处和可能知你的人了。
全篇到此,对于仁的体用,已经说了一个大概,画了一个轮廓,但是仁的宗旨究竟如何?还是没有说出来。其实,如果纯用文字言语来说,能够讲得出来的仁,也只是人生立身处世行为上的至真至善的美德,可以说只是仁的致用,实在没有办法把仁的道体显现出来。
那么,所谓仁的道体,也就是宋儒理学家们所讲的心性微妙之体了。说心、说性、曰仁、曰理,无非只是名词表达的不同。如果我们综合汉儒的训诂释义和宋儒的专讲义理来说,仁,从人,从二,便是人与人之间、心身性命的中心,犹如果核之有仁,灵明不昧,不是麻木不仁的。当其寂然之时,它是寂然不动的;当其致用之时,它是感而遂通的。
所以颜回三月不违仁,居于陋巷之中,只有一箪食、一瓢饮,而犹不改其乐,正是他心身住在仁的静态里,处于寂然不动之中而别有乐趣存焉,这也就是宋儒所说的孔颜之乐了。所以孔子就大为赞赏颜回,认为孔门弟子中,只有他才得到孔门传心的道体。我们如果学以致仁,事实也并不太难,孔子已经说过:“我欲仁,斯仁至矣。”只要你在动心忍性之间起心求仁的时候,便可立刻到达仁的境界了。如果要勉强去体会的话,便要学孔子告诉颜回的求仁的纲目,先能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等。先当正其心身,从外面强自打进心来,把欲望的念头去尽,就可以识它的端倪了。
曾子悟道
自从颜回死后,仁道几乎失传,幸好在孔门的弟子中有曾参其人,还可以担当起这个传承的责任。我们都知道,孔门的弟子中,颜子是最聪明的天才,他对孔子的教学是闻一而知十的人。但曾子却是一个诚笃而鲁拙的人,与颜子来比较,恰恰是一个最上乘的智慧和一个最诚笃最鲁拙的对照。求其达到仁的道体境界,唯有上智与鲁拙才能不变。如果是中人之资,听了仁道,只能若存若亡,或者下学而上达,渐渐地进修,才可以到达。因为曾子是个宁可守拙而诚恳讲求仁的道体的人,所以他用志不纷,渐渐就成熟了。
有一天,孔子看到曾参涵养纯熟了,便当他经过时,突然叫他一声,曾子回头一看,心里的疑念涣然冰消云散,活泼泼地现出一个灵明寂然的仁体来。他明白了!孔子也认为他是真明白了!便告诉他说,我这个心法的仁道啊,一以贯之;只要用志不纷,一直下去,就可以到达的。既然到达了仁的境界,以后也只要保持这个境界,就可以贯彻一切,能通天下之事了。所以曾子在明白了孔子的指示后,便答应一声说:唯。“唯”,只是一句答应的表示语,等于我们现在说的“喔”!
这一段事,当时只有孔子和曾参彼此心心相印,明明白白,不达到这种境界,谁也无法领会的。所以等到孔子离开后,其他的弟子们便争着向曾子问,刚才你和夫子的一番做作,讲的是什么道理啊?何以是“一以贯之”啊?曾子明知他们的学养还没有到达这种境界,说了也是白费,所以就以仁的致用来告诉他们说,老师所传的道理,很简单,只要你立身处世,随时随地,做到尽心为别人的忠心;待人接物,随时随地,做到宽厚待人的恕道,那就是一贯的学问了。
这一节书,看来真是笑话,明明一个忠、一个恕是一回事的两面,哪里贯得起来呢?如果在忠和恕上加个一贯,就有了三贯了,那还叫什么一以贯之呢?而且孔子告诉曾参的只是“一以贯之”的一句话,他当时哪里说过忠和恕呢?如果有,那便是曾子临机应变,硬把忠和恕贯起来了。所以就可知道孔子当时传曾参的、许可他的,正是仁的道体境界,也因此,他就成为孔门传道的唯一传人了。曾子告诉别人的,却是仁的致用,其实,并非曾子要瞒人,实在是学养能到仁的道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于不得已中,只好如此传布,只能在行为上面画出一个轮廓罢了。
孔学的宗旨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这节书最难读,但又是《里仁》全篇的中心所在,也是孔门传心学问的宗旨所在。如果只抓住一贯当作孔学,实在有许多地方是贯不起来的。孔子也曾经把“一以贯之”这句话告诉过子贡,子贡便缺少曾子回答的“唯”,所以便无下文。你必须要下过一番功夫,身体力行,身入其境来体会,等于实地演习一番,才能稍有领会之处。如果不如此看,我就不知道仁是何事了。因此,这一节话,一定要插入《里仁》的中心,才不会误会它突兀可怪。再说,我们如果要把仁的道理和一以贯之联接起来说个明白,最好和最妥当的解法,还是多读书、多研究,追寻孔子传承儒家道统以来的理论,才比较信而可征,而且不落在后儒的窠臼里,那样就更接近、更可靠了。
这种治学的办法,就叫作以经注经。我们试读《易经》的系传,首先可以了解孔子所讲一以贯之的道与仁是个什么情形。他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至于所引用本节的内义究竟如何,只要静心研究,自然会通其理的,因为这不属于本题范围,只好留在讲《易经》的时候再说了。
为什么我肯定地说本篇是孔门传道的中心,是孔子学问的宗旨呢?只要静心读书,你就会发现它的脉络。《论语》一书,从《学而》一篇开始,许多地方都插入孔门师弟之间研究学问的对话,互相辩难。一到了本篇,统篇都是“子曰”开始,一路到底都是记载孔子的自说。虽然末后一句加入一节子游的话,只算是余波荡漾而已。只有在曾参的一节,好像是记载故事那样,忽然插入这一段机锋妙用,而且对曾参则称为曾子。可见编记的大半是曾参的门人,所以他们对这一段传心法要就特别地重视,更要尊称曾参老师为“子”了。
根据《汉学师承记》,凡嫡传的称为弟子,再传的便称门人。到这里,既然点出曾参承受孔门心法的仁道,已经指明传仁道的宗旨了,以后就无事了吗?不然!不然!须知在未见道以前,戒慎恐惧,唯恐不及;既见道以后,还是戒慎恐惧,唯恐不及。如果明体而不能达用,但见到一个寂然不动的境界,还只是为学的半途。必须要由此知,由此见,起而发于立身处世的行事之间,才是仁的大机大用。因此以后半篇,跟着而来的,就是孔子谆谆告诫的平常日用之间的言行了,虽然人人都懂得,唯恐不能踏实做到,所以便一再提醒。
重义的人 重利的人
你看他在曾子见道以后的传述,统篇都是义利之辨,敬己敬人,尽孝修德,自立立人之道。如说: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但他告诫我们,在行为上,切实明辨一个义利以外,为什么又要加入一个“喻”字呢?这也就是说,凡是君子之儒,处处以义为前提;倘是小人呢?便会时时以利益做标准。除此以外,另有一层意思,还是在讲仁的作用,这个仁的境界啊,它是含育天地、弥纶万类的。君子见仁,便如曾子一样,就拿忠恕之道,或以其他的礼义来做比;小人呢,就只知道学养做到了仁的境界,对于自己的心身和一切,是有无穷利益的,这种动机,其目的还是为一己的功利出发。所以在这里,就可以看出君子之儒和小人之儒,同样都是为学问而学问,可是其中却有了一个极大的分野。跟着一节是: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这是说,儒有君子之儒和小人之儒,只要你明白了其中的不同,当你见到真正贤者的君子之儒,就应当想做到和他一样,可以并驾齐驱于仁义之道。倘使你见到一个不贤的人,就应当以看到他的缺点和过错之心,当下反省自己的学养是否也同样犯了他的错误。这样,你就可以做到上不骄,也下不谄了;不会拿着一点知识当学问,或是写成文字,而且看不起别人,或羡慕别人了。
其次,讲到仁的致用,万变不离其宗,圣人是以孝道治天下,纵然你已经到达了仁的境界,还是要切切实实从孝道做起。这与《学而》一篇劈头便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是首尾相照的,所以便引用:
如何奉侍父母
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这是说我们孝敬父母是当然的事,但如果发现父母的事情有错,你不去劝谏他,也就是不仁。所以应当好好地、婉转地、不断地劝谏他。父母实在不肯听从的话,就只好尊敬他,不违背他的意思,虽然自己受劳受苦,也只好受之而无怨,宁可任冤到底。如果事先不劝谏,或者任劳而有怨恨之意,那就要不得,也就是不仁了。
还有一层,“几谏”的“几”字,又通“机”字。机者,机会也,机微也。换言之,在发现父母有可能做错的动机时,就要找机会来劝谏他才对。讲到仁者对于孝道的用心,便说: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如果父母还在世,自己绝不敢远游不归。万一非远游而不可,也要有一个方向和目的,而且还要对父母有所安排,绝不可为了享受而到外国,丢下父母不管了,那是鬼道社会的习惯,绝对自私和唯利是图的风俗,万万做不得的。如果那样做了,你到临死的时候也会后悔莫及的。
清代诗人黄景仁旅居北地,在途中患病颇剧,便怆然作诗说:
去家已过三千里
堕地今将二十年
事有难言天似海
魂如化去月如烟
更有“今日方知慈母忧,天涯涕泪自交流”之诗句,可见人到穷途末路时,都会想到父母。为什么不想想,你在富贵中,父母也会想念你呢?这是说对父母生前孝道的一环,倘使遇事非远出外方不可时,也要像在父母面前时一样,没有口是心非,或当面唯唯、背面否否的事。乃至父母过世三年之久,还是和父母生前一样,始终不变,这才够得上是孝了,才显出真性情的伟大。
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古人向来对这一则的解释是说,父母死后,你在三年当中也不改父母的做法路线,这才是孝。如果真作如此说,孔子这句话的确是有问题的。我在《学而》篇中已经说过了,所以不必再讨论。
但因此而说到仁者的用心孝道,不但应注重父母生前的孝养,而且更要注重父母的健康,要随时注意照应他们的衣服、饮食和医药,无论相处一起,或出门在外,都须知道。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这是说一个为人子女的人,对于父母的年龄,不能不知道。一方面知道父母年高有寿,而且还很健康,这是一件最可喜的事;一面又惧怕父母年寿高了,一旦健康有损,医药无效,就有抱恨终天的遗憾。孝道出于至情,大凡人在青年和中年,对于男女夫妇和下对儿女,自然有至性流露的爱。至于上对父母的孝顺,凡是根基不厚的人,如不经过教育的提示,或许要到中年以后,人生阅历增加了,才会反省体会得到。倘是至情充沛的人,则能自少便领略到孝的重要。但人到中年,大多父母都已过世,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那时才会追悔和痛恨。
我在数十年的交游中,默默观察,凡是没有丰富的至情至性的人,大多都是天性凉薄刻毒的小人。我也亲自看见几位老一辈的朋友,对父母的孝行和孝思,的确值得肃然起敬,将来我很想把他们的事特别写出来,传与后代子孙做榜样。至于现代的青年人啊!一切倾慕西方文化,连这一点基本仅有的孝道也不存在了。有些人责备怨恨父母的心,比怨恨他的佣人还要厉害,如果能够拿出爱子女心情的一半来孝养父母,或者还报父母对子女情爱的一半,已经属于凤毛麟角了。
以上几节,由义利之辨开始,一直到重提孝道的重要,到此为止,还是告诉我们学养达到仁道以后,仍然需从人生本位最基本的真性情中,老老实实、平平易易地做去。
其次,才说到见道以后的立身处世,与社会人群相处时敬业乐群的要点,尤其要谨谨慎慎、小心翼翼地做人。
你会做人吗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这是孔子举出古人的谨言慎行的好榜样,用它来告诫弟子们。他说,古人不轻易、不随便地说出一句话,因为他怕话说出去了,自己行为上有做不到的地方,那是很可耻的事。“不逮”,就是不及的意思。这是他教人言行合一的重要,但跟着又引用孔子的话说:
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
只要随时约束自己的心身,谨言谨行,就会很少有失言失信的过失了。这里的“约”字,是简少、管束的意思,不作俭约的约字用。所以下文便有: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这是反证上面两节和本节的连贯处,也就是说,凡学君子的儒者,宁可做到木木讷讷的,不肯轻易发言、不宣传、不说空话、不吹牛,只有敏捷地去做到,以行为来替代言论才对。这句话,也有先做后说的意思,认为行在言先的重要。
自这里以后,下面列了两节话作为本篇的结论,也作为仁者平时力学和用心的格言。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这是说,只要你自己内在学养到达仁的境界,在处世致用的行为,随时随地,以培养自己的德性以俟天命,那就不惧怕世途上的孤单和寂寞,久而久之,一定会有向德慕化、千里趋风的知音来同类相聚的。这与《学而》篇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恰恰是一对照。
本来到此已是全篇的结论,但忽又加入弟子子游的一节话,似乎是不伦不类。其实不然,子游的一则话,加在这里,正在说明行仁之道的向上一着,说明仁者爱人必须约之以礼。否则,仁则仁矣,还怕会有过犹不及的毛病了。须知仁道的学问,重在做到,不在空言。要求自己可以极其严格,对待别人不必希望太过,更不可要求别人个个都做得到,所以说:
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
例如一个人臣,对君主希望或要求太多了,又要屡次请说,结果只有招来自取其辱的份儿。对朋友也一样,只要你要求得太多,或者过于希望他好,结果反而疏远了。大抵人情,过于亲密则反疏,疏淡则反亲。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能够永远和易相处得其中和之用的,实在太不容易。
由此可见,得仁道固然很难,行其仁道,尤其不易。这是人生处世的艺术,艺术的意境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仁哉!仁哉!不易言矣。这一节的结论,和开头的一节“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恰恰又遥相呼应。也就是明明白白告诉你处世的艺术和经验,运用之妙,存乎其心,全仗自知智慧的抉择,不然,哪里会识得学问德业之为美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