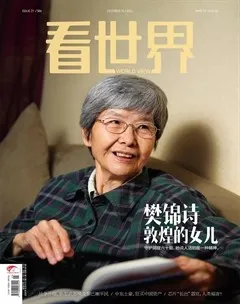纯爱退场,“渣男渣女”集合

国产爱情剧正在抛弃爱情。或者说,正在剖解“爱情”这个词。
近期开播、宣称“向所有纯爱战士致歉”的都市爱情剧《半熟男女》里,没有任何一个角色在感情里绝对忠诚。熙熙攘攘的城市迷宫里,他们互相躲藏、试探和拉扯,各怀鬼胎。看似自由的男欢女爱,背后都藏着各取所需的心机,或是一念之间的背叛,几乎“全员恶人”。
以剧中男性角色瞿一芃为例,他与几个月前另一部国产剧《玫瑰的故事》里的方协文一起,成为了年度“渣男”代表。二者人设也类似:自卑且自负,敏感多疑,在感情里极端且不真诚。
这部剧将一个终极论点抛在了台面上:如果削弱道德占比,仅随心所欲地去爱,爱情的模样还可能是美好的吗?道德是维系一段感情的必要因素,还是阻碍?
“渣男”“渣女”的炼成
作家金宇澄曾在接受《十三邀》访谈时,对“渣男”这种词汇表达了不解和批评:“人本身是非常复杂的东西。这么复杂的人性变化,用这么低能的一句话去涵盖它,真的是太幼稚,太可怜了。”
节目播出后,金宇澄毫无意外地招致了讨伐。甚至有一种批评声是:没准金宇澄自己就是或曾是“渣男”,才会为这种“道德败坏”的身份“洗白”。


其实只需关注语句的表面意思本身即可。这位年过七旬的作家之所以认为此类概括让人显得“可怜”,是因为在本可以具有充分缓冲地带的道德情感境遇里,一个人主动选择了单一的受害者立场。
若概括《半熟男女》里几位主角的行为,几乎人人都是“渣男”“渣女”:脚踏两只船、互相出轨、移情别恋、为攀富贵玩弄感情者……从道德角度论,人人都是加害者,同时也是受害者。
而“渣男”“渣女”“海王”“海后”这样的词汇,自其发明初期到大面积传播,其承载的功能更多是便于概括和情绪发泄。在亲密关系里,当人们感觉自己受到了伤害,自我保护和反击是一种本能,其中就包括情绪发泄与道德审判。
看不见的台面之下,人人都在提防遇到“渣男渣女”,但我们自身是否也可能在某个瞬间变得“渣”?我们是否也会“本能”地用人性的复杂性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剧中,“脚踏两只船”的何知南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不妥。她内心的另一个人格在试图唤醒她:“被两个人喜欢没有错,但你享受就渣了。”但世俗里的何知南也会对自己承认:“被两个人争夺,让我感觉被在乎了。”
人很容易用“渴望被爱”来解释自己背德的行为,这似乎是用一种心理或情感的脆弱来做掩饰。剧中千方百计想要攀上富家女的小镇青年瞿一芃,从他的视角,自己出轨、撒谎,都是因为自己在这个名利场社会里不被尊重。他渴望被人“看得起”,渴望被爱—难道,也是一种错吗?
一些行为的初衷也许并不是伤害他人,但又的的确确给他人带去了伤害,在这种两难情境下,人真的可以毫不犹豫地作出利于他人的选择吗?如果对我们自己的心诚实,是否必然会在感情里滑向道德低谷?
也许需要承认的是,当人们遇到爱—无论那是假象还是真实,被激发出来的也许不是勇气和力量之类的东西,反而是内心深处的脆弱面和攻击性,还有贪婪、欲望和趋利避害的本能。
例如“普通女孩”何知南渴望被爱,渴望在多多益善的爱里享受独特性;已婚男人周斌渴望年轻女孩的肉体,渴望掌控弱者的权力感,为此谎言遍天飞;职业女性韩苏也渴望一段忠诚和稳定的感情,可当发现自己被背叛后,她也会产生报复的欲望。
人们因独特性而具有吸引力,也因独特性互相伤害。正如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缪塞说:“男人会欺骗、背叛、泄密、伪善和傲慢无礼;女人都很做作虚伪、不诚实……但是这不完美的两者结合起来却是人世间一件神圣而庄严的事。”
爱情,它是一个神话。我们可以去演绎,可以去欣赏,但别想着活在神的世界里。
爱情神话
《半熟男女》不是近几年第一部戳破爱情神话的国产影视剧。
去年,出自同一作者之手的电视剧《装腔启示录》(豆瓣8.2分),同样将叙事焦点对准都市里互相拉扯、试探的男男女女。他们没有纯爱的幻想,但他们会诚实面对自己的私心和欲望。同时,他们对爱情没有不切实际的期待,能在混沌现实里互相提供支撑和某种力量,就已足够让两个人走到一起。
诱惑、欲望、寂寞等让“背德”趁虚而入的情绪,在或许原本就不够坚定的心理堡垒里横冲直撞,最终指向供我们所有人躲躲藏藏的道德暧昧性。
如果对我们自己的心诚实,是否必然会在感情里滑向道德低谷?
这种“道德暧昧”,与浪漫主义文学史上的道德边缘化完全站在对立面。前者是由于现实掣肘和世俗心思过多,后者,如《泰坦尼克号》或《廊桥遗梦》里那种超脱世俗的浪漫邂逅,反而是摒除世俗限制、听从内心激情的感召。
不过,多年后,人们才恍然大悟,《泰坦尼克号》里男女主角的爱情,其实也是背德的婚外情。由是,又一轮逆时代的道德价值批评涌入。
一个有些“反现代性”的事实是—在今天,道德在爱情里的地位似乎更高了。
于是,对人性的其中一个面向做出道德评判变成一件容易的事。网络平台上,铺天盖地的“劝分”大军。节日不送礼、回复信息不及时,就足以被审判“该分手”,仿佛亲密关系里的人只是商品,可以随时退换。
但似乎的确,越来越多人默认,只有乐而毫无“喜怒哀”的亲密关系才值得自己走进。结婚率整体下降的社会背景为这种道德洁癖做出了呼应:如果不是足够纯粹的、毫无瑕疵的爱情,宁肯不要。
然而,忠诚的命题之下,同样埋藏着令人失望的可能。近几年知名度较大的国外家庭题材电影《婚姻故事》和《意外坠楼的审判》,都呈现了“承诺”之下更长远的隐患。有情人终成眷属之后,还可能面对更棘手、更难以脱身的人生命题。
爱情只需要发生,它属于两个人相望的一瞬间。长期的感情、婚姻,则需要经营,需要用心和用脑,也需要物质支撑。
从这个角度看,爱情并不是难事。两难的是人们对它的定义和期待。这并不是要求我们放低自己的道德标准,恰恰相反,我们的道德准则,不应该被爱情“污染”。
在古希腊哲学家们对爱情的思考与解说中,爱天然包含欲望、嫉妒等“人性阴暗面”,现代社会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更外因性的虚荣、势利等因素,于是诞生了“凤凰男”“捞女”等词汇。


信息时代,在种种“不美”的爱情故事的冲击下,人们一面歌颂绝对纯净的爱情,因为它越来越显得稀缺;一面对掺杂半点瑕疵的感情难以容忍,要求关系里的绝对公平与透明。
当人们对爱情不切实际的信仰和期望一点点破灭,紧随而至的是对爱情的唾弃与嗤之以鼻。如今,轻视爱情甚至反对爱情成为某种时代主流。爱他人的分量远远让位给“爱自己”,一个将爱情看得太重的人,被放置在了鄙视链底端,为了追求爱情付出的心力更是可耻的。
时代情绪在提倡“自爱”,并认为充分地爱自己是爱他人的前提。可爱情的本质,就是一种人格深处缺失的弥补,是一种“忘我”。人们沉迷其中是因为忘我,但经历伤害和痛苦,也是因为短暂的忘我。
一个有些“反现代性”的事实是—在今天,道德在爱情里的地位似乎更高了。
抽丝剥茧之后
爱情的魅力之一,在于排他性与唯一性。在这个拥挤的世界里,我唯独看到了你,你也独独看到了我。爱情发生的瞬间,个人价值得到最大程度地满足,对大部分普通人而言,甚至是前所未有的满足。而那些三心二意的、朝三暮四的暧昧和试探,在审美上就与爱情背道而驰了。
但真正的爱是依附于日常和世俗发生的,我们没办法忽略复杂的现实,反而去发明一些更复杂的理论和公式来提纯爱情,这实际上是在拒绝真实的感情。
《半熟男女》的原著作者柳翠虎在接受采访时形容:“都市里的爱情其实很像绿化带里的花,它很鲜艳,但是它也有城市应该有的汽车尾气和灰尘。”
利益和算计、防备和试探,不公平的付出,以及永远辨不出来的“输赢”,这些东西看起来很狼狈和污糟,但它们是在这个环境里生长并活下去的必要痕迹。
“互相劈腿”的何知南和瞿一芃,也会在与前任分手的时候真情实感地流泪,他们真切地感受到痛。只要一个人还有心,哪怕已经被大面积污染,他依然可能被刺痛,可能发生感情的波动。
但毋庸置疑的是,如果我们选择去爱,就要接受受伤的可能性。因为它极大概率是理性控制之外的、防不胜防的,也可能是短暂且充满危险性的。
爱情是《花样年华》里周慕云与苏丽珍在深夜她拾阶而上之前的刹那对望,是《两小无猜》里还不懂爱的两人互相说“敢”的一瞬间,是《安娜·卡列尼娜》里有夫之妇和年轻军官在火车上偶然发生的刹那对望和震颤。
有时,爱情的发生,短到还不够进入道德审判的维度。可有时,它与世俗道德的相斥性,又恰恰证明了它的纯净性。
对大部分亲密关系而言,百分百的、纯粹的公平是个伪命题,总有人付出多一点,在意多一些。同理,不假思索地接受对方的全部也是伪命题。在一次次体验、质疑的过程中,我们渐渐靠近真实的自己,也渐渐攒聚起生命的多维度和厚度。
特约编辑吴擎 姜雯 jw@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