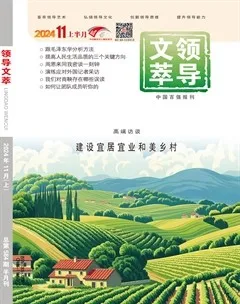如何利用好东南亚机遇
东南亚国家充满活力,尤其越南、印尼等这些起点较低、过去10年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国家。从经济总量看,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东盟10国合计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且经济增速处于全球前列,比世界年均水平高出2个百分点。从发展序列看,东南亚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同样引人注目,印尼人均GDP不到5000美元;马来西亚人均大约1.2万美元,属于中高等收入国家;而新加坡是典型的发达国家,人均GDP超过8万美元。
重视东南亚不仅是因为东南亚经济蓬勃发展,市场潜力大,也因为中国面临着来自美国的围堵、遏制和打压,因而也需要在全球寻找能够替代美国市场的地方。面对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中国企业必须做好深耕东南亚的全方位准备。
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之后,东南亚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中转站”。中国大量产能在向东南亚转移,中间品贸易即基于价值链的增加值贸易尤其发达,形成了更精细化的三角贸易模式。中国目前在东南亚的投资和经贸合作是全方位的,不仅有基础设施、农业、水资源领域的投资,还有各种发展水平的产业合作,包括工业园区等特色内容等。
如今,不少东南亚国家的贸易情况是,同时向中美两头推动进出口,因而需要新的理论来理解东南亚的贸易模式。
东南亚地位更加突出
中美贸易摩擦仍在持续且战略博弈加剧的背景下,东南亚的地位比以往更加突出了。以贸易为例,在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之后,东南亚地区很快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23年,中国—东盟贸易额占中国外贸总额的15.4%,为第一大贸易伙伴,比2018年上升2.7个百分点。在动荡不安的世界里,这是中国外贸方面难得的好消息。
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十分深远。在此背景下,对美、对欧贸易增速出现下滑,中国企业主动加大了对东南亚的投入。过去5年,中国—东盟贸易额净增加约2.5万亿元人民币,而美欧合计仅增加了不到1.5万亿元人民币的贸易额,特别是美国的增量不足5000亿元人民币。
中美贸易额占中国外贸总额的比重,已从贸易摩擦爆发之初的13.7%下跌至目前的11.2%,跌幅2.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迅速上涨,占比甚至超过亚洲增量的一半。一定程度而言,中国在美国市场的损失,通过东盟市场弥补回来了。
考察东南亚主要经济体的进出口结构后,可以发现一个显著的特点,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行业的比例是很类似的,即进口的产品和出口的产品都属于同一个类型,两者在进出口中的占比极为接近。
在典型的南北贸易模式中,发展中国家通常出口的是原材料,进口的是制成品,两者分属于不同的货物范畴,因而进出口结构是很不同的。在增加值贸易主导的时期,越南乃至东南亚的地位有点像加工“中转站”,xxKAYSLnGKdhXpaOLd6TOw==对中美都能出口一些适合的产品,因而这些国家难以选边站,而是两头谋求利益。
零部件贸易实际上更有利于中小国家参与产业链,因为在一个工业体系不完整的国家,很难在本国完成一个产品的所有生产环节,很少有国家会追求大而全,各国均可以利用各自的特色谋求生产链中的位置。
冷战结束以来,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大量进口原材料、出口制造业产品,机械、ICT和电气产品出口成为价值链贸易的核心产业部门。信息技术加速发展,大大降低了沟通协调的成本,使得分工链条进一步细化和加强,不同国家可以根据自身在成本上的不同优势,积极参与到价值链生产中。
由于强大的金融能力,美国在经济规律的驱使下,大幅度压低了本土的制造能力,而将其转移到其他国家进行加工,本国则坐收金融之利。在美国霸权鼎盛时期,没有国家挑战这种分工秩序。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不再像以往那样能提供足够庞大的市场,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必须自谋出路,通过联合自强,加强区域合作制度建设,将彼此作为部分损失了的美国市场的替代。
机遇与挑战
东南亚人口将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结束之际超过7亿。曾有机构预测,到2030年,东盟7亿人口中的65%将成为中产阶级,即大约4.5亿人口。其中,每人每天的支出范围在10美元至100美元之间,这会形成一个十分可观的消费市场。对于那些注重消费市场的企业来说,这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庞大群体。
审视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存在感时,总的来说要看到,中国增量快但存量还弱于美国及其盟友。东盟给出的数据显示,美国仍是东盟最大的外资来源地,2022年为369亿美元,占东盟当年吸收外资的16.4%。日本列第二位占12.1%,2022年为270多亿美元。中国列第四位占6.9%,约为155亿美元。
从国别来看,新加坡吸收的外资最多,占到东南亚吸收总量的近68%;其次是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三国合计约占东南亚吸收外资总量的28%;最后是中南半岛的较贫穷国家。在新加坡、印尼和马来西亚,美国的投资额领先其他国家,中国仅在柬埔寨和缅甸的投资额占据首位,而日本在泰国的投资额占总量的30%以上。
不过,从行业领域看,美国在新加坡的投资很多集中在金融领域,这与中国、日本在东南亚的投资有很大的不同。目前与中国企业竞争最为激烈的主要是日资企业,因而日资企业的经验和教训值得优先考虑。
日本企业在东南亚布局较早,形成了一套在当地经营的方法,其中包括通过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事先进行详尽的调查。该机构在马来西亚、泰国的分支机构均设立于1950年代末,在印尼的办事处设立于1960年代。相较于服务日本企业对外投资的这些辅助性机构,中国在这方面的准备和投入是远远不够的。
日韩企业在东南亚的投资比中国早了一至两代人,它们下沉的程度比中国企业要深得多。在雅加达这种大城市,可以看到华为这些大企业的广告,但到了万隆、日惹等二三线城市,就难寻中国品牌的踪迹了。这些日韩企业在东南亚经营已久,甚至已经出现了二代、三代为这些企业工作的本地人。中企在当地的经营是很难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须靠长时间的跨文化交流来积累互相之间的信任。
当然,东南亚普遍存在“都市主义”特征,即大城市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吸纳了来自全国的年轻人口,消费很发达,它的中高端消费领域和其他国际大都市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中企在初期更容易进入这些市场。但是,二三线城市的本地化色彩更重,要进入这些市场,所耗费的时间和信息成本是巨大的,除了自己派合适的员工前往之外,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也是重要路径。
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经营时的另一个思想误区,是照搬国内的项目治理思维。许多企业不熟悉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生态,习惯了跟“一把手”打交道解决一切问题的方式,但是在选举体系里,官员是会周期性更替的。另外,在权力分散、社会组织发达的东南亚,衡量谁有影响力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在不同事情上,不同机构的影响力也不一样。如果没有深入地在地调研,很难在复杂的关系中找到解决具体问题的方式。
(摘自《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