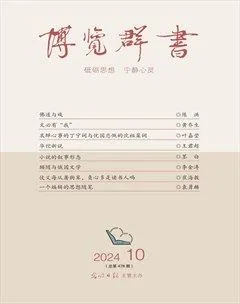诗是诗人的另一种“人生”

梁平是一个极具辨识度,令我尊敬的诗人。他注重诗歌艺术的叙事性,善于从寻常的生活中捕捉灵感,发现诗意。在多年的写作生涯中,梁平始终保持着罕见的艺术掌控能力,不浮躁,不追风。“拒绝肤浅和妖艳,把诗写进骨子里”,既是他一以贯之的诗学主张,又是其特立独行的诗歌风格。这种与众不同,独辟蹊径,向诗歌领域的纵深开拓,已然成为梁平诗歌高贵的精神气象和宏阔高远的写作格局。如此有艺术坚守,写作追求,且优秀作品不断问世的诗人,在当代诗坛确乎是并不多见的。梁平写诗,从事诗歌编辑数十年,一生始终都与诗歌相伴相随,密不可分。诗歌成了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他毕生的追求。梁平对现实、历史、时间、人生、死亡等千丝万缕的世间万象的深刻思索,无不浸透在他的诗歌中。这种对艺术的思考和生命的追问,就像地下的温泉,汩汩而出,结晶成为一首又一首精妙的诗歌,让我们欣喜地领略到了梁平在日常生活之外的另一种“人生”。
墨西哥诗人帕斯说:“诗歌作为一个民族的缔造的圣经,是每一个文明中出现的特征,从吉尔伽美什的诗篇,它可能是我们诗歌传统的源头,到熙德的诗篇。”“诗人帮助我们懂得什么是激情,从而使我们认识自己:嫉妒,好色,残忍,伪善——总而言之,人类灵魂的全部复杂性。”(帕斯《谁读诗歌》)古往今来,每一个优秀的、伟大的诗人的诗歌,从来都是生生不息,渊源有自的。梁平的诗歌写作,深受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注重内在的节奏和韵律,同时又广泛吸收了西方现代诗优秀的表现技巧,在极具艺术张力的出色书写中,庖丁解牛,佳句迭出。这种兼容并包,举重若轻,融盐于水的巧妙吸收,使梁平的诗歌呈现出清晰的,与众不同的写作风格,并成为他诗歌写作雄厚的底气。
梁平从不炫技,并对当下诗坛的弊病,毫不留情:
诗歌中“我”的出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有点不受人待见。如果自己的写作总是去考虑受不受人待见,这是很荒唐的事。古今中外无论大小的“我”,举不胜举。中国诗歌传统从《诗经》以来如数家珍的“我”比比皆是。屈原厄运之后汨罗的净身,李白入世失败之后寄情于山水,杜甫的隐退,苏东坡的官隐,陶渊明的归隐等等,“我”在其中活灵活现。米沃什当过记者、教师、外交官、流亡者,甚至被限制过母语写作。米沃什诗里大量出现的“我”“我们”,就是他的骄傲,他的“我”能够成为他所有经历、所有认知的证据。海明威的间谍生涯,记者生涯,以及他经历的两次坠机事故生还,四次婚姻,最后饮弹自尽,他伟大的作品和他不能复制的“我”,成就了他成为世界文学的仰望。我甚至认为,尤其是诗歌更需要“我”以自己的面目出现,包括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形状以及出场的仪式感。“我”是我找到的进入这个世界至关重要的切口。……而当代诗歌的轻浮,甚至轻佻已成诟病,不能视而不见,应该高度警醒了。陈超先生曾经很尖锐地指出,当代诗坛的重大缺失是历史想象力和历史承载力日渐薄弱。(梁平《自言自语或者几个备注》)
可以说,梁平以自己的写作,捍卫了诗歌的尊严和艺术品格。王国维高度评价纳兰性德“以自己之眼观物,以自己之舌言情”。梁平推崇王国维的诗学主张,并以自己的诗歌,践行王国维别具只眼的诗学观,从不跟风,独树一帜。
壹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乌台诗案下狱,贬谪湖北黄州。宋神宗元丰三年三月七日,在沙湖道中遇雨,同行者皆惊慌狼狈,而苏轼却泰然面对,并写下了《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这首千古流传的词。对于饱经人生坎坷的苏轼来说,再大的苦难和打击,都不能击垮他,使他低头。因为他早已进入了“也无风雨也无晴”崇高的人生境界。这样的人生境界,对于梁平来说,完全就是一种人生高标,面对现实生活中的任何挫折和残酷打击,苏轼始终都能从容面对。这种乐观豁达的潇洒和人生态度,不仅影响到梁平的人生,而且成了他诗歌中永不枯竭的文化血液。《一蓑烟雨》是梁平继《时间笔记》之后的又一次大胆探索和新的突破。他从不把目光局限于书写现实生活中鸡零狗碎的生活琐事,或者由此引发出来的小感触,而是把诗笔伸向历史的纵深之处。在书写那些沉重的历史题材时,梁平常常是举重若轻,游刃有余的。他能在诗中非常出色地处理好历史与当下、虚构与真实、现实与人生,以及诗歌与未来的关系。在他看来,诗歌书写现实,与人类的进步和社会发展始终相关联,从未间断,并以自己出色的诗歌,赓续了中国诗歌优秀的文化传统,成为其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诗性化的人生感悟和艺术呈现,其艺术冲击力和带给人们陌生化的审美阅读体验,真可谓妙笔生花,让人欣喜:
渠江、涪江投奔嘉陵江而来,
三江汇合处,峭壁上的钓鱼城,
没有闲情逸致执钓,城墙上猎猎的旗,
与南宋的血雨,坚硬了这里的水。
13世纪罗马教皇没见过这样的水,
惊呼“上帝的罚罪之鞭”,这一鞭,
大汗蒙哥应声倒下,横跨欧亚的蒙古铁骑,
戛然而止,世界改变了模样。
水上打鱼的船,岸边钓鱼的人,
都见过世面,敢说先人的血就是一整条江,
敢说大世界不过几块石头,
没有水咬不烂的石头。
水在合川就是图腾,理解和不理解的,
一生一世过来了,一代一代,
顶礼膜拜。水里繁殖的血性上了岸,
随便一声吆喝,两岸落木纷纷。
——《合川》
在我看来,像“水里繁殖的血性上了岸,/随便一声吆喝,两岸落木纷纷”这样激情四溢,激荡着雄性血性的诗句,是只能属于梁平的“诗歌专利”,它彰显出合川人以弱胜强,用沸腾的鲜血书写历史,视死如归的无上荣光。
在梁平的笔下,许许多多的地名,都有一段非同寻常的历史,都是一个浪漫迷人的传奇。梁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所到之处,无不触景生情,文思如泉:
最后一滴血硅化成玉,
雁江忠义镇高岩山上的石头,
有了盖世的名分。
沱江埋伏战国礼乐,苌弘的音律,
惊动齐鲁圣贤,孔子拜师拉长的镜头,
定格资阳的封面。
北宋那尊卧佛一直睁着眼睛,
从身边走过不敢喧哗,退后百米,
默读岁月沧桑。
三千五百岁的“资阳人”以为躺平了,
看流行的群裾,摩登的高跟鞋,
跃跃欲试。
年迈的先人真想翻身起来,
时尚一回。最早古人类唯一的女性,
已怀疑自己封存的颜值。
资阳车水马龙的一个缝隙,
现代刻度一天一个样子,稍有不慎,
找不到自己。
——《资阳》
合川和资阳,或许都是许多读者并不熟悉的巴蜀小城。其饱经沧桑的历史和悲壮动人的故事,向来鲜为人知。殊不知,“上帝折鞭处”就发生在合川;“苌弘碧血”的苌弘,就出生在资阳。苌弘不仅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学者和贤臣,政治家和音乐家,而且还受到孔子的极为尊崇,拜为老师。苌弘忠而见谤,放逐归蜀,慨叹虎狼当道,奸佞横行,从而决绝地与污浊的世道一刀两断,剖腹自尽,以身殉节。蜀人感其精诚,将其鲜血盛入匣中,三年之后,苌弘的鲜血竟化成了碧玉。“苌弘碧血”,表现出资阳人令人怀想,可贵的英雄气节。梁平书写历史和历史环境中的个人,就像中国古代诗人对历史的再现和想象,鲜明地彰显出诗人对历史的判断和解读,乃至对具体历史环境下的人物所进行的臧否。就像司马迁在《史记》中,对虽死犹生,失败的英雄项羽所进行的同情和悲悯,李清照在《夏日绝句》中对项羽的赞美一样,鲜明地表现出梁平对于历史的深刻感悟和对于诗歌艺术的独到理解。在《一蓑烟雨》中,合川和资阳,以及众多古老的历史地名,都纷纷以诗的形式,鲜活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这种历史的、诗意的书写,塑造出了一个崭新的、不一样的“诗歌合川”和“诗歌资阳”。
贰
作为一个诗艺精湛的诗人,梁平拥有多副笔墨。在题材上纵深开拓,在技巧上,古今中外,无所不精。中国古代诗歌讲究炼字炼句,注重音节的抑扬顿挫,乃至平仄。而西方诗歌则更强调形式和内容,乃至题材和风格上的开拓,以及对写作边界的突破。梁平在诗歌写作时,左右逢源,眼光深远,并能充分融化成自己多样化的写作风格。在处理历史题材时,他的笔总是深沉、浓重的,而在描写日常生活,或某一事件,乃至具体场景时,往往又是轻松、飘逸,甚至颇具调侃性的:
隔夜的茶很委屈,
茶叶横七竖八不能自证清明。
茶针分不清白天黑夜,
不知与水的交欢还有时辰的嫌弃。
隔夜隔得了众目睽睽,
隔不了质疑与纠结。
蒙受不白之冤的夜,
找不到一尺缝隙的申诉。
玻璃杯在夜的末端保持缄默,
我的时间自己拿捏,
日茶夜茶只要汤色正好,
皆与我亲密无间。
——《隔夜茶》
好的诗歌,一定是意蕴丰厚,具有发散性思维,甚至常常是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往往都可做多种解读。梁平表面是在写隔夜茶,但又并非真正是在写茶,而是在剖析,我们一贯囿于固定思维的陈规陋习。这就如同人们普遍认为,隔夜茶不能喝,而隔了夜,并且隔了无数个夜的冰红茶和菊花茶完全可以喝一样吊诡。从来就没有人怀疑,我们判定的标准和思维方式,是否从源头就出了问题。梁平表面写的是“隔夜茶”,其实却是在以诗歌的方式警醒人们,一定要走出被长期遮蔽的信息茧房,打破固有的思维和“从来如此”的判定事物的方法。这种想落天外,无理而妙,寓寻常于深刻的艺术书写,无疑是梁平对寻常生活的独特发现。这样富有哲学意味的诗歌书写,就像润物无声的春雨,悄然提升着读者的审美鉴赏和艺术感受能力。
秘鲁诗人塞萨尔·巴列霍在谈到诗的生命时说:
一首诗就是一个单位,它比自然界中富有生气的生灵生动得多。一头动物截取一个肢体,它仍然可以活。一棵树砍掉一个枝子,它也仍然可以活。但是一首诗删去一个诗句、一个单词、一个字母、一个书写符号,它就活不成了。
(塞萨尔·巴列霍《诗和诗人》)
梁平的诗歌,无论短诗,还是长诗,都有精心的构思和完美的结构,尤其是像《水经新注·嘉陵江》这样气势磅礴,规模宏大的长诗,让读者处处都能感受到其精心的艺术结构,领略到其精妙的写作技巧,在当代诗歌史上,堪称是一次诗歌艺术的探险和写作壮举。而《蜀道辞》的写作,同样彰显出梁平对诗歌艺术的孜孜以求和写作抱负。梁平说:
诗歌如何保持它揭示历史生存的分量,如何置身世俗的“生活流”,又不至于琐碎、低伏地“流”下去,如何在对个人经验的关注和表现中,实现诗歌话语与历史文脉的融汇,让诗歌不再飘忽如云,这是当代诗歌必须重视和要解决的问题。《蜀道辞》几百行几乎用了我整整一年时间。古蜀道,一条比意大利古罗马大道更久远的世界交通遗址,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无所不及,从实地考察到案头资料消化,节点的取舍,构架的设计,人物的勾勒,语言的调试,应该是完成了自己的又一次重要的实验。其中最为耗费精力的是,如何深入,如何浅出,为了浅出,头上又添了几丛白发。(梁平《自言自语或者几个备注》)
可以说,《蜀道辞》既是梁平对诗歌艺术的大胆实验,又是他多年写作艺术的成功结晶。许多天马行空,无所依傍的奇诗妙想,就像山间的白云,变幻多姿,飘然而出:
尔来四万八千岁,
峡谷与峻岭悬挂的日月星辰,
以川陕方言解读险象,三千年典籍。
线装书的蜀道巨著,章节回旋、跌宕,
在秦岭、巴山、岷山褶皱里,
雨雪滋润山清水秀,
雷电席卷金戈铁马。
(《古蜀道》)
旺苍纪家河桥头石碑年事已高,
“上通秦陇,下达蜀川”的碑刻,
抬举了旺苍的身份。
一路过米仓山围猎南江温婉,
又巴中沿巴河、渠江南下重庆,
另一路经蓬安、合川,终结嘉陵江。
(《米仓道》)
嘉陵江水位爬不上明月峡,
东岸峭壁上一条天路,
与古长城、古运河齐名的古建筑,
现存的活化石。
(《明月峡栈道》)
这样大气磅礴,具有雄性血性和气魄的诗歌,堪称当代诗坛久已不闻的黄钟大吕,读来令人血脉偾张,从而获得一种难得的阅读审美体验。
叁
在谈到《一蓑烟雨》的创作时,梁平说:
年龄越大越是感觉到该写的欠账还是该一笔笔算清,给自己一个交代。“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春秋”,做不到。但是可以深居简出,去过的地方不去了,人多的地方不去了,谢绝了很多场合。尤其害怕人堆里随时冒出来几个自诩的大神,海阔天空,还总是在诗歌分行的时候,头颅昂扬,目光向远。仔细一看,满身披挂的珠光宝气,用以唬人的竟是低级、廉价、仿冒的文字吊牌。
在多年的写作中,梁平远离平庸、抵抗喧嚣、特立独行,始终拒绝拉帮结派,坚持以优秀的诗歌作品和雄厚的写作实力来说话。
主动与那些非诗的、世俗的、喧嚣的、打着诗歌旗号的“诗歌活动”和“诗人”进行毅然的切割,这是梁平对于自己的写作所进行的深刻反思和必要的“断舍离”。只有决绝地回到自己的内心,专注于写诗,才能写出真正属于自己,同时也属于时代的好诗。就像葡萄牙诗人佩索阿,一生都生活在一个狭小的地方,籍籍无名,苦难艰辛,每天都在为生活辛勤奔波。但正是因为有了诗歌,佩索阿的心灵世界才显得如此辽阔,内心才如此宁静平和。对于佩索阿来说,诗歌就是他整个的生命和精神财富。除此之外,什么都是浮云,什么都是身外之物。有学者发现:“从他的手稿判断,佩索阿写作不辍,几乎一天都没有停歇过的样子,这也许是因为他对自己建构的庞大的写作世界有着紧迫感?”(杨铁军《想象一朵未来的玫瑰——佩索阿诗选》“译者序”)就此而言,作为异常珍惜写作时光的诗人,梁平与佩索阿可说是灵犀相通,追求相同的。
什么样的诗人才能写出真正的好诗?西班牙诗人阿莱克桑德雷说:“诗与人性之间有着强烈的血缘。”在他看来,一个真正的诗人就应该耐得住寂寞:
寂寞与沉思的时刻也便是创作的最佳时刻,寂寞与沉思使我感到了自己与世界并未脱离,并且这种联系永不会终断;从这时候起我就坚持认为,写诗的真正意义就是和人们沟通。正是诗歌把诗人多年来蕴藏在心中的思考向这个世界展示。每一首诗、每一部书都是一份恳求、一次呼唤、一种质询,答案则由读者在沉默、含蓄和不断的阅读中所呈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诗就是诗人的询问和读者的答复之间的一种精妙绝伦的对话。
(阿莱克桑德雷《诗与人性之间有着强烈的血缘》)
诗歌要写“我”,写“人性”,这是古今中外一切优秀诗人共同的写作“基因”。梁平写过无数的好诗,涉及过众多的题材,但最让我感动,并且始终难忘的,是他描写与父亲生离死别之际的两首亲情诗:
凌晨7点10分,
突然想拨电话了。通了没接,
再拨,又通了,那边声音有些异样,
变得浑浊而遥远。
——“我要走了”
一句没有任何铺垫的应答,
比子弹更迅即,击中了我,
窗外惊飞一只白鹭。
成都与重庆距离拉长,
四个轮胎长不出翅膀。
窗玻璃外,整片天空面无表情,
路牌在倒,树木在倒。
12点零8分,高速戛然而止。
前面是世纪的界碑,
只差五步,
抵达我们之前的约定。
——《至痛时刻》
父亲上山以后,
清明节就没有雨,欲哭无泪。
老爷子走了,阴阳之间,
上下划分了一条线。
线下的哀思、烛火和鲜花,
线上虚拟抵达。
父亲加过我朋友圈还在,
没有动静,没有信息,
应该睡了吧,让他好好睡吧。
我们上线了,母亲很好,
儿女很好,孙们曾孙们很好,
那是九十五个年轮,
平常百姓相依为命,
粗茶淡饭留下的好。此时此刻,
天色清明,草木念念有词,
有风吹送父亲熟悉的鼾声。
——《线上清明》
在当代诗坛,这是我读到过的最感动,最令人潸然泪下的描写父子亲情的诗。梁平诗中那一幕幕生与死的诀别,以及锥心刺骨的悲痛和血脉相连的依依不舍,早已深深地镌刻在我们的脑海中,让读者异常真切地感受了那种欲哭无泪,挥之不去的难言之痛。
肆
每位诗人都有自己心仪的诗歌前辈和致敬的伟大诗人。他们的诗和诗学理论,乃至分析问题,看待世界的方式,无不深刻地影响着一个个继往开来的诗歌写作者。波兰诗人米沃什是一位享誉全球,备受敬仰和尊崇的诗人。米沃什从来就不喜欢“热闹”,甘于寂寞。有记者问米沃什说:“你称自己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诗人。你不想拥有受众吗?”米沃什回答说:
我为一个理想的人而写作,我想象那是一个变异的自我。对于是否容易理解,我不关心。我会判断,我的诗有什么是必要的、有什么是适当的。我跟随我的节奏与秩序的需要,而且,我反对混乱和虚无,为了将多方面的现实尽可能转化为一种形式。……很久以前有一个时期,我因为写作一些取悦于人的东西,尝到过“知名”的滋味,但是这个时期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当你写作政治诗时,就像在我战争期间所做的那样,你总会得到一些追随者。今天,对于“知名”,我感到吃惊和不安,因为我想知道,那些反响是真实的,而不仅仅因为我是诺贝尔奖得主。另一方面,我不认为诺贝尔奖已经影响到我,或者已经影响到了我的创作。
(《巴黎评论·诗人访谈》)
就内心的强大和对人生的态度而言,米沃什简直就像“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波兰苏东坡”。米沃什出生于波兰,他“真实地经历了20世纪的一切人间地狱,也体验过某种天堂。他内心装着我们整个世界的理想和幻想。如果没有米沃什,波兰人通过个人经验所获得的关于20世纪的认知将是十分贫乏的,甚至我都不晓得,波兰是否还会停留在跌跌撞撞的步伐上”。(马丽亚·雅尼昂《克朗斯基—米沃什:思想与诗歌节选》)“他躲过了血腥的20世纪初在他头顶上呼啸不止的立陶宛和波兰的子弹,躲过了集中营(尽管他曾被德国人抓走),躲过了精神迷失,未曾被迫出卖笔杆子。他创作的作品是过去的那个世纪所发表的波兰文学作品中的杰作。他受到很多人的诋毁,但都慷慨大度地原谅了他们。”(安杰伊·弗劳瑙塞克《米沃什传》)
苏轼的不幸遭际,广为中国人所知。在“乌台诗案”中,他同样躲过了杀头。如果没有苏东坡,中国文化的星空,一定会黯然失色,绝不会如此星光璀璨。有了苏东坡,在中国人的内心里,就再没有过不去的坎。梁平喜欢米沃什,更是对苏东坡心慕手追,高山仰止:
一直喜欢、推崇苏东坡,喜欢他的大格局、大胸怀,历尽千般苦难,“也无风雨也无晴”的从容与乐观,最后依然对坎坷的人生际遇作出温暖的回应:“天下无一不好人”。
(梁平《自言自语或者几个备注》)
一千年前的苏东坡,与一千年后远在波兰的米沃什,完全是命运相似,才华横溢的隔代灵魂和异国知己。他们共同都选择了“原谅”,并且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他们的精神气质,以及诗歌艺术成就,无形中成了梁平诗歌的文化血液。他们对人生、命运、苦难、不幸的深刻理解,更是梁平终身追求的大格局和人生大境界。这也是我们打开梁平诗歌的一把密钥,同时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梁平的诗歌创作,以及他之所以要远离诗坛的喧嚣与浮躁,读懂《一蓑烟雨》字里行间所蕴含的历史和复杂多变的人性,领会梁平诗歌中所彰显出的无穷艺术魅力,乃至在诗歌写作上的苦苦追求。
诗歌成了梁平的精神生活,写诗成了梁平日常生活的常态。默默写诗,深耕细作的梁平,以他的心血之作《一蓑烟雨》,实现了又一次新的突破和精彩蝶变。就像从未离开土地的老农,梁平总是在他心爱的诗歌这片沃土上,辛勤耕耘,默默付出,写出一首又一首优秀的诗歌,最终得到了读者热情的赞誉。诚如梁平所说:“我的整个写作都是未来完成生命塑型的根。”诗歌与梁平,早已融为一体,密不可分。
(作者简介:唐小林,生于1959年,四川省宜宾市人。出版有文学评论集《天花是如何乱坠的》《孤独的“呐喊”》《当代文坛病象批判》。在《文学自由谈》《作品与争鸣》《当代文坛》《南方文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当代作家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星星·诗歌理论》《文学报》《文艺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发表文学评论数十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