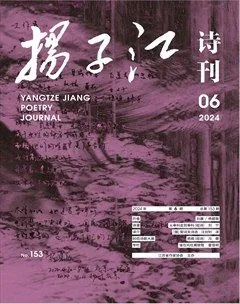一再地,终点往前流去
崖丽娟:自从我开始做诗人访谈就从不同渠道收到诗人朋友们的建议,诗人朱朱你是一定要访谈他的。可见您是一位很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诗人。我们先从一个宏观问题开始:好诗的标准有哪些?谈谈对“新诗”的认识,初学者常犯的写作错误应该如何规避?
朱朱:好诗的标准像一个看不见的球心从来没有变过,变化的是各种不同的球面。“新诗”看似允诺了更多的自由,但也带来了更多的无所适从,你需要为每一首诗找到一个特殊的、甚至专属于它的形式感。也许是面对一个黑洞时产生的心理防御,最近十多年来我陷入了某种强迫症,大多数的诗都保持各段落的行数均等,只有极少数例外。
有一些评论家朋友,譬如江弱水和李章斌,探讨了新诗的韵律和音乐性。我有一首短诗《寄北》,在江弱水的建议下,去除了一个并不必需的字之后,通篇暗合了五韵步“素体诗”的汉语形式,这件事让我很惊讶,它也许说明了:我们可以凭借自己的本能和内在听觉印证什么,但合于韵律之道未必就意味着是一首好诗。
太多的诗歌以为自己是蚌壳孕育出的珍珠,其实只是泥沙般的情绪释放或排泄。对于每个写作的人而言,犯错的过程是无法省略的,博尔赫斯说他犯过一个写作者会犯的所有错误,至于我,每天都还在犯错;写诗不靠肌肉记忆,一个普遍适用的经验是:对经典的阅读或他人的建议固然重要,但只有自己真的意识到需要改变的时候,一个人才会做出改变。
崖丽娟:您大学时期就开始诗歌创作,能否介绍上世纪80年代大学校园诗歌活动的情况,还记得在哪里发表的第一首诗吗?诗歌在哪些方面改变了您?
朱朱:记得当时上海的高校中,最活跃的是复旦和华师大的两个诗社,地理位置上一东一西,我入学的时候,华东政法学院并没有诗社,但有一些喜欢写诗的学生,我和好友谈勇一起创办了一个诗社,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出一本油印的合集。
我们的大学邻近华师大,日常的交往自然更多一些,我也曾去旁听过宋琳的诗歌课,当时还没有真的认识他,在课堂上他用迷人的催眠语调,进行着现代主义的启蒙。华师大的大门口有一家小酒馆,他们的诗社有时会请我们吃饭,吃到没了酒又没了钱的份上,有人叫一声“干爹”,于是酒馆老板就笑嘻嘻地出现了,然后,啤酒就成箱地跟来了。
大约三年级时,我和陈东东、宋琳才算真的认识,并且一直交往至今。和陈东东的相识要略早一点,关于写作他同样说过一些让我受益的话,在最近写给他的赠诗里,我这样写道:“我们之间从不是雄辩的氛围,/耳语般的溪流进到心扉,/有些已是地板下干涸的电池,/有些汇成瀑布,至今声若雷霆。”
我第一次发表诗应该是在安徽的《诗歌报》上。在大学时自己也油印过几本小册子,似乎是一年一本,这习惯在毕业后也持续了不少年;在早期的那些习作里,《扬州郊外的黄昏》的完成度似乎还不错。
我愿意将上世纪80年代称之为“最近的故乡”,也曾对此怀有浓烈的乡愁,《旧上海》《重新变得陌生的城市》都与之相关,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意识到那个年代值得反思的东西更多。至于诗歌,给予我的其实是一种内在的独立人格,无论处在哪种现实环境里,我都有恒定的一面。
崖丽娟:您写诗几十年间是否感觉疲惫和厌倦,让您坚持下来的动力和理由是什么?
朱朱:我没有坚持过什么,写诗近于本能,几乎像呼吸那么必需,一天之中,如果不和诗歌发生一点联系,我会觉得自己虚度了时光,尽管在书桌边想上一个上午,可能连一个字也写不出,甚至只是删除了昨天写下的一行。诗不是写出来的,而是你需要和它们生活在一起,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的相处,它们才肯向你显露最真实的模样。
有时候,我也会厌倦一切,甚至想起这颗星球早晚都要毁灭,意识到这一点,对写作也不是坏事。
崖丽娟:您的成绩有目共睹,评价您的诗歌,组诗《清河县》是绕不过的作品,在《清河县》里您写“人性”,也写“性”,怎么想起要以此为创作题材的?
朱朱:当时我试图以此传达人性的相对性和复杂性。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能力,就可以通过性折射出人性或世界的全部,但这是很难做到的,所以性这个主题始终被不同年代的作者书写着。
崖丽娟:很多读者对现代诗的隐喻感觉晦涩难懂,主观意象太多是否对读者构成阅读障碍?作为诗人,您为谁写作?
朱朱:写作不是炫技,不是一场关于难度的竞赛,但诗本身就是有难度的,关系到速度,穿越事物的速度,也关系到准确,蕴含多义的准确。
我不揣摩、更不低估读者的智商,有时候,我有意识地为自己设置障碍,以免写作惯性的衍生,譬如在写作《旱船》之前,我就决定不用一个明喻。更多的时候,难度意味着为具体的主题找到合适的表现形式,譬如去年的两首诗,采用通篇提问的句式更吻合《曼德斯塔姆的一首诗》的主题,而在《夏尔巴》那首诗中,我迫使自己采取短促的句式,以对应那种在雪线之上攀缘的心跳感。
我为诗这样一种既有的传统而写作,我希望自己能和同代人一起真正地延续它,在《过灵岩寺》里,我写过“一再地,终点往前流去”。
崖丽娟:在诗歌不断被边缘化的语境下,诗人何为?当代语境是否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诗歌对现实生活的呈现?
朱朱:也许我孤陋寡闻,不记得人类的历史上,有谁因为诗人的身份高踞于权力的核心,或者有哪一首诗决定了关键时刻的社会走向,边缘或许意味着更多的精神空间……不过,在今天,也许是诗人们自己萎缩了,退出了,变得没有能力回应当代的问题,蜷缩在一个抱团取暖的小圈子里。
崖丽娟:我读过批评家张桃洲教授主编的《寻找话语的森林——朱朱研究集》,有很多批评家都评论过您的诗,诗歌创作与诗歌批评是一种什么关系?您从中收获了什么?
朱朱:关于我最早的评论,应该就是张桃洲写的那篇《寻找话语的森林》,当时他还在南京大学担任教职,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不少快乐的时光。书中有一些作者我从未谋面,譬如年轻一代中的赖彧煌,他的那篇文章写得妙趣横生,可惜他早逝了。
对我来说,获得来自评论的深切理解,当然是很大的安慰,譬如我读姜涛的那篇文章时,就在想:精妙的倾听,智识与感性在他那里并存。还有一些后来写出来的好文章没有被收录进来,譬如麦芒的《无人赋予使命》、李章斌的《成为他人》等。
马小盐关于《清河县》第一部的“环型剧场”论,为我写作《清河县》第二部带来过启示,这是批评在切实地影响到我的创作。
崖丽娟:身兼诗人、艺术策展人,两个身份之间的张力构成的是相互启发、相互促进、相互提升的关系吗?有没有冲突?
朱朱:开始时,两个身份之间的龃龉不少,主要是时间和精力的分配、知识系统的调整、个人习惯的改变等,譬如过去我只能在自己的书房里写诗,后来,等到我也能在上午时分的旅馆里写诗时,情况就开始好转了。
现在看来,从事策展,尤其是写作艺术评论,让我有机会深入到他人的思维方式之中,帮助我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诗人身上的两种常见病:半是高士半是怨妇式的自我中心主义、遗老式的文化优越感。
崖丽娟:您先后出版过法文版诗集《青烟》和英文版诗集《野长城》,在中外诗歌交流活动中获得哪些启发,创作中会受到潮流的影响吗?
朱朱:没有什么潮流等着我去汇合,更多的意味着我得以置身在异域,以一个观光客的身份观察着那里的“好天气”。出版《青烟》的收获,是我被邀请去了出版社所在的海港拉罗榭尔,回来之后以那里为原型写出了《小城》这首诗。当时,出版社安排在大西洋沿岸的一些小城镇做了几场朗诵,有一座小镇为我们举办了隆重的晚宴,但是镇长迟到了,他来了之后一个劲地道歉,原来他是为一头母牛接生去了,在日常的工作中,他交替担任镇长和兽医这两个角色。
受限于语言能力,我对西方诗歌的了解绝大部分仍然来自中译本。对于国外的同行,我近年的记忆里倒是有一些零星的片断:在一次互译活动上我邂逅了安妮柯·布拉辛哈,荷兰的一位女诗人,我为她的那首诗激动过,《蒲福风级表中的贝多芬》,起势平缓,然后旋律一浪高过一浪,结尾臻于一种近乎抽象的虚无。此外,德国的杨·瓦格纳应该是一个极其用功的诗人,2019年我们一起受邀参加鹿特丹诗歌节,有一天清晨,在旅馆门前,他一边观察着草地上的鸟群一边记着什么,好像画家在写生,后来,那些鸟厮打起来了,不知道是否干扰或改变了他的思路。
崖丽娟:您关注90后、00后年轻诗人的创作吗?如何评价他们?有什么建议?
朱朱:属于他们的时代正在到来,最近两三年,我和80后、90后之中的几位渐渐有了一些日常的交流,虽然读他们的作品并不多,但他们的修养、趣味和判断力都显得可靠,只要有闲暇的时间,我很愿意彼此以朋友的方式一起谈论诗歌,分享写作的进展;在我的同代人那里,这种激情变淡了,话题开始变成无休止的怀旧之类……
时间确实过得很快,我也到了给别人提建议的年龄了,那就“修辞立其诚”吧。
崖丽娟:感谢您百忙之中回答。
朱朱:应该感谢您的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