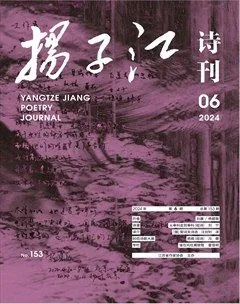霍珀(组诗)
三间屋
1
一块暗礁内部挖出的屋子,
挖出的石料堆成四周的阴影。
住在附近的人亲切地称它
“午夜的光之岛”,午夜,
当泅泳者经过时,四肢
会被黄蜂般钻出窗户的灯光螫中,
一阵温暖的麻痹,足以导致
终生羁留。不信就问问
那位白头的酒保,他来自
我们每一个人的老家:一座
被浪冲毁的码头,储藏在大脑
但远离了心跳;如今他弓身
在海的最深处,熟知用什么来
填满黎明前成排像伤口咧开的杯子。
2
固执留下了形象,但不够。
岸边的塔或荒野里的大教堂,
智慧的虹已在其中蒸发,徒留
七彩的纹饰。看,这铁道边的屋子
让我想起祖父当年端坐在家中,
要对抗随时会来的地震,
已无人信任古老的屋顶了,却也
没有谁能劝得走他。地震确实没来,
但我们都已爱上路过的新世界
——忍冬花的耳朵探出枕木
测听车轮,一种速度如炉膛的火
一闪,瞬间让它枯干。酷烈的
不再是对抗,是地平线逃往
自己的尽头,让位于面对面的遗忘。
3
连大海也可以省略,唯愿光
到最后的一刻依旧在场,它
透视人不过是一场自愿的耗散,
像一团咖啡的热气渴望被风催赶,
很快就剩一层薄薄的黑色残渣;
它透视而不责备,如常地抵达,
顺应门窗既定的方位,如果
一面墙赠予了画布,它就用
整天描绘出你生命的不同时段,
直至傍晚时你们完全叠合,那份
默契远非大海与陆地能够比拟。
看,连故事也可以省略了,只剩
类似固态的那种波动;波动,
不就是全部?我生来从未见过静物。
阳光里的女人
现在有一个机会
去问明余生的际遇,
她却止步于那条额外的路。
立着,就这么赤条条。
乳房就这么累赘,
头就这么负发而重。
窗再框紧阳光片刻——
和风已填平深渊,
正将悬崖吹至背后——
注定要来的事情,
就让它们桩桩件件地来,
逐一被应729980d160b1de3801570a240fdfe902339d1085a4ae8af159752168efc946aa对。
多菲内的房子
退役后上尉做了一个哨所般前插的梦,
并在梦中驻扎不少年。现在:
字迹已1ddccbb3305d7a21e3902ef17a3e74b7ce5eb642c8db5ade65cc8fe0b3ebfbb7湮灭的“待售中”。
烟囱甚至蒸发了视觉的暖意。
在该死的、后来才修建的铁道边,
这个被围合的空尚未瓦解,
全靠那几根壁柱在原处支撑着,
谛听着,似乎仍然等待什么。
熟悉的脚步声走远后,有一天
忽然响起,在近旁消失,
然后再次响起,走远,从此消失。
现在,就可以说:草是陆地上
最广袤的海,致力于面积而非深度,
它的目的是以漫过的方式让往世搁浅,
它的波浪做好了扎根的准备,
缓慢地扩展,却没有退潮的间歇。
加油站
长久地行驶在梦中的极地,
你终于决定短暂地回归;
将车泊在路边,关灯
但不熄灭引擎,只为凝视同类。
那人伫立在一片整理过的荒野
(全然不知你已悄然来到),
他摆弄着加油泵,像先民
在傍晚的厩栏边填放草料。
当一个人独自沉浸在劳作中,
四周就没有末日的迹象,
森林静静地汲水,昆虫和鸟
不断加入即兴的合唱。
当一个人独自沉浸在劳作中,
像钟表背后的齿轮忘我地运转,
而另一面指针一圈又一圈
重复着那种无谓的计算。
皮管偶尔会像调皮的马蹄踢他。
若有若无的美国在附近游荡,
看,筑在松槐上的那些巢,
原来每个地点都与天空接壤。
当一个人独自沉浸在劳作中,
他是在轮值我们共同的渺小;
动荡的星球,激愤的呼号,
延迟的告解,获得隐秘的担保。
你是逃亡犯凝视一个有家的人;
你是晚年的托尔斯泰,被电影
特写镜头里一位马拉松选手吸引:
恍若终点在上,永在原地奔跑。
这凝视像刻刀,将你从冰海
凿出,从虚无的浪沫里析取;
在洒落的灯光下,这凝视
将你重新还原成确凿的人。
路边,稻草钨丝般闪烁
即将点燃的暖意(当心,随后
会像腐热的沼气)。油箱已
变得充足,现在,就让旅行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