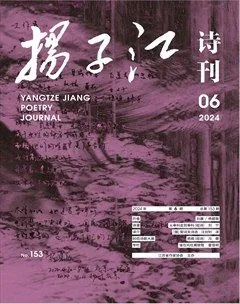乡野的轮回(组章)
柏水,本名马健,1995年生于山东临沂,现居山东济南。
小河门槛
跨过连绵的山崮,小镇上的风有了红瓦的模样,在夜幕来临前,留下唯一的记录。田间的镰锄,摩擦出透明的火花,一点点挖掘着干裂的土地,愈来愈深。
镇子外的小河,雕琢出一座小镇的岁月,在乱石与泥土中滋润着往来之物。几只鸟摆脱了圆形的引力,落于河滩,在泥沙中构造起避人的“门槛”。曾有先生来此隐居,在屋舍之间留下无声之诗,每一句诗,都是自然的馈赠。
一部分在春秋沉淀而成的絮语,从门的夹缝中脱离,它们跃出虚幻的门槛,重回乡野,试探着每一处新生的绿意。等到飞鸟归巢,远方的路人重返小镇,那夜幕下的最后一幅画,成为此刻小镇上唯一的故事。
纵使四季轮换,那条环绕小镇的长河,却终年没有干涸,它为镇子带来生活之外的惊喜,在老旧的渡船旁,敲打出诗语,告诉人们它的历史。小镇的命运,从未在门槛之外,那些顺流而下的碎石,击打着来自岁月的鼓点。
酒歌
父亲的麦田里住进无数风声,在赤黄的泥土中与麦苗交换上个月的听闻。隔岸的河洲上有路人歇脚,他们从偏重的木船上划开黏稠的日子,在父亲还未理解前,抹去了河川的声音。
村外的石磨旁,有酒香占据了几间瓦房,云朵外的白鸟,轻点羽翅,将沁人的香味带离矮房,送到父亲的肩头。他很少独自偷饮,而是深入河滩,穿织起江流与村落的故事,在喟叹中与友邻小酌几口,裹紧对话的歌调。抛开那些跟随水声远去的古歌不谈,清风、明月、麦浪,早已填满了乡民的思绪,在无人的时刻,悄悄低吟。
斑驳的水野间,太白的酒歌蔓延到北纬23度的庭院,让院中的水井拂过石槛,向父亲他们言说着历史清单。现代水票无法阻隔飘荡百年的鼓点,只能依着酒的香气,盖住酒歌里的遗风。
荒原与麦田格格不入,那里不曾有酒香的影子,穹顶之上的诗句,依旧绕不开酒歌的呼唤。父亲是山野的看门人,他早已数不清河洲与田间的声响,不过,酒歌穿透时间的巨墙,使他打开了岁月的巨门。钟点之外,我们拼接起眼前的村落,酒味再起。
牧羊的老人
山坡上的石楠花,飞越草原,带来无数闪耀的晨露,花的世界远离河滩,在羊肠小路旁望着时令。细雨已经将日子打落在花丛中,老人驱赶着羊群,涌入草野的腹地。他用一生的时间,摸索出草原的模样,却没有摸清自己的样子。
高处的石楠花,是他多年前撒下的枯种,时间将花苞滋养成熟,让花色在天空下拼凑成诗意的音符。老人日日闻鸡而起,放牧着羊群与晨风,在脚步的回响中丈量着与故乡的距离。他用一根细鞭抽打着生活的暗礁,帮助羊群躲避风雪的侵袭,那墨绿的门扉,总是离他不远不近,却无法触及。
秋末,旷野不再温顺,而是以枯败的景象面对老人和羊群,自然的法则终究无人能堪破,老人带着余生的愿景,在生活的残章中写下温柔的一笔。他曾走过雨巷、老街、河港,将过往之事一一抛掉,在草原上重拾生命的影子。远方的星海,是他悬于胸口的秘密,无人时,他总要将秘事倾诉给羊羔,仿佛完成另一种托付的仪式。
黄昏里的石头
从城市走入乡野,踏进一片浑厚之地,碎裂的星辰,无人关注,在黄昏后留下了隐约的影子。他是穿越山河的旅者,放下旅行的包袱,在这座安逸的小村里驻足。
黄昏是他最喜欢的风景,如一扇真实之门,收纳着世间独有的美。黄昏前,他择一处开阔的河滩,任由眼前的牛羊在黄昏里奔腾、迷狂。风绕着他手中的词语不停飞舞,将陌生的词语吹成日落的模样,在小镇的河滩上,他遇见了不一样的黄昏。孤霞迎着时间的旧痕,映照出不一样的故事,草露成霜、鱼游河川,自是没有皴染的风景。一阵风,勾起石楠花的香味,在温柔的夕阳下,送来“月神”的简讯。
短暂停留后,他又要踏上远方的旧路,由乡野进入城市,追寻另外的光景。词语的黄昏,在午夜前浸入大地,那些沉眠的故事,循着旅人的足迹,重新踏上了归乡的路途。
深秋经验学
很少踏入秋的旋律,九月,自有过渡的意旨,将城市的高墙推向一个成熟的季节。及至深秋,眼前的风景不再炽热,而是以沉稳的色调装点着周围的世界。被诗情画意包裹的秋日,发散着不竭的经验,人们穿过落叶满地的林荫道,体悟着吹在身上的柔风,走进另一个生命的良宵。云深无归处,深秋的安稳告解着逝去的故人,让南归的群雁带去无法言说的思念。
在城市与山乡的交接处,秋日完成了一幅色泽鲜明的百景图,演绎着独属于这个节令的荣枯之貌。深秋的风,从未越过幽深的山谷,而是沿着城市的高墙,阐释着秋日的影子。一些无关乎生活的景致,自会没入万物的隐喻。记录,不过是短暂的永恒,没有触及秋日的灵魂。那些在旅途上奔波的人们,喜欢深秋带来的故事,却也讨厌深秋的凋零。
当思想落入旅途的经验,被忽视的部分,开始有了不一样的转折。比如,沿途中永不消失的落叶,不断向下生长的草木,都像一场场没有预设的电影,遁入深秋,演绎出在世间丰盈的经验。
芦苇的思想之歌
水中的芦苇,跃出云的倒影,宣告着一种新的声音。雨水介入河滩,打湿万物,带去令人颤抖的凉意。关于芦苇的诗词,总有哲学的影子潜伏其中,记录着时令的挽歌。在河滩上静自生长的芦苇,镌刻着乡野的标识,复现每一处草木的故事。水域外,无数的目光反复打量着这片芦苇丛,想象的门槛,在此生发。暗香浮动的河岸,总有折返的鸟稍作停留,仿佛要抛下所有的憾事。
荒原的季节,在草木中愈发洗练,芦苇丛里的思想之歌,在无人的夜晚悄悄生成。生活的窄门,嵌入芦苇丛,在夜晚敞开,留下诸多隐秘的碎语。当晨曦的光辉又一次照亮河面,一丛丛芦苇低下了头,等待另一个挺身的节点。
多年前,先生来到河滩写生,他迎着晚霞,看到了水中芦苇的倒影,仿佛一座看不见的小城在眼前浮现。他明白,草木的历史,难以追溯,凝结出想象的风,在诗人的笔下成为了永恒之物。芦苇中的思想之歌,无人聆听,却在天地间演绎着辽阔的图景。离开水野时,人们总会看见浮动的芦苇,却听不到关于思想的声音。
再谈归途
离开乡野多年,在远路上总能触到故乡的味道,迷人的城市里,余散着荒原的记忆,夹杂着属于故乡的风景。一部分来自山野的信物,在半路上隐匿,流淌出忧伤的挽歌。漂泊数年,我们似乎懂得了无风的意义,那些早已复活的岁月,一次次上演着荒原的故事。乡野的小路,成为不再独特的符号,装点着无人观赏的石楠花、宝铎草。
异乡的笛声,在流水淙淙的夜晚一次次响起,街巷里的石画、长街上的草垛,在悠扬的旋律中荡开。雨水的介入,让归途有了朦胧之感,乡土的味道也愈发浓郁。我们离开城市的街衢,找寻属于乡野的至真感,却总在原地来回打转。
远处的山林,不再藏有挽歌,而是复现每一处和乡野有关的记号。古老的山群,守护着少有人踏足的乡野,也隔断了两个文明的交织与碰撞。乡野的归途,在轮回中充盈着生活的记忆,我们不再孤独地返乡,而是穿过岁月的窄门,和乡野有了一场新的对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