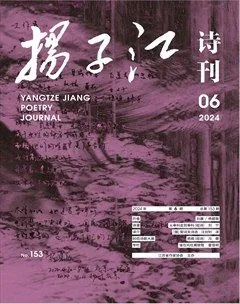桂香(组章)
王尧麟,2000年生于湖北钟祥,现居湖北武汉。
故人来
我们聊起那首诗,聊起瞬间的战栗,像偷偷分食同一道闪电。
那时我们还足够年轻,足够用一个句子照亮夜晚。如今,有回忆把我的喉咙抵着,使我不敢发声——在一把生锈的匕首面前,是埋藏多年的地雷。
我在周围环绕着,轻轻贴上“禁止入内”的封条——不敢点燃的引线,不敢打开的链接,不敢回看的,另外的一生。
“后来,那些人就不见了。”我们自然而然地谈起他们,就像谈起一个荒诞的寓言。
客厅雪原
你称呼我傻子,像用一柄柑橘味的塑料气锤轻轻叩击额头。情人间总能产生这样的力场,把锋利的匕首握持成一束栀子。
魔法还是魔术,是变幻还是转移,取决于演练是否精确和谎言是否精心。今日早餐,分食焦脆吐司壳下的流心煎蛋,凭借凝固的程度来判定二人权能。聊聊昨夜法棍般的梦,反复切断,并不厚实的梨肉纤维,像伐倒一棵积雪压枝的冷杉。
天气骤变,温度下潜得越来越快,客厅几乎快要被冻结。我们坐在桌子的两边,用紧绷的姿态捕食,眯眼对视,几乎快要成为两只歪着头颅的可爱雪鸮。
停电
人类总是习惯通过电力开掘生活的沟壑,在白天的尸体上缝补,躺在夜晚的怀抱里凿刻,然后重复涉过齐腰的明天。
而我喜欢那些在黑暗中闪光的事物,白昼里,它们并不容易被察觉——那时,生活抓到什么,就吞咽什么——它们太过微小,不足以击起浪花。
它们只是拌嘴、晕车、一袋杨梅和一首情歌。只有在黑暗中你才能看到它们,正聒噪地发出自己的光热。
夜色蛰伏在窗外,安静听着。树木口渴,星星嵌入烛火。
桂香
屋外种着三棵桂树,高高的,过二楼,手举香气,不讲道理地把花开进客厅。
我想起初中学校的花坛外种的桂树,每到九月,晨读时,花香从窗户袭进教室,把我们驮着。趴在桌子上,总感觉自己躺在一棵巨大桂树的枝条上打盹。桂花的气味好闻,大家都乐意大口呼吸,于是说话的声音也变得洪亮,轻轻把那段记忆抛光。
后来我从那所学校转走,从此不再晨读钓鱼做梦。我总以为,秋冬早上喝到的桂花糊平日里也能买到,其实不然,用旧的部首从来无法更换,回忆终究只是听起来老土的流行词。
观影记
等到三点四十五分的时候,你就该明白了——电影准时开场,没有恰好坐到你身边的女孩。
还要留下来吗?为了看这工作灯的光束,像一截刚刚蒸好的花卷。你想到今天没有晚霞,没有月牙,只有不怀好意的小雨和饿坏的肚子。
好在电影还不错,足够安慰干涩的喉咙。可一些失落悄然而至,断绝发泄的权利。
太多的欲言又止,塞进裤兜。穿过影院大门的时候,它们噼里啪啦掉落,跟在你身后,结队成群。
午夜
午夜,我路过长椅旁。
这样的晚上,应该有两人在这里聊聊月亮。
提问,用一些比喻——用云的披肩,或者露水的呼吸来形容月光。其中一个低头,想想说,月光灌满眼眶,漫出来的,就成了泪。而另一个,默默拧干浸满月光的衣裳。
可是,从来没有这样的晚上。漆上月光的长椅,有沉稳的影子,像一截坟墓,杵进地面,埋葬几个迟到的修辞和古老的愿望。
疲惫
站在寝室门前,钥匙仿佛又一次失效。它在锁孔里重复旋转,开启更多的雨声、鸣笛和铁轨摩擦。
它们从时间的各处赶来,并在搅拌中逐渐凝固,坚不可摧。我用拳头凿取这些标本,作为呼救的号角,替我催开铁门。
躺在床上,拖鞋像黑色金鱼般游离我,窗帘被风吹鼓,化为粉色的腮。我隐匿进窗帘的羽翼,得以避开那两片发散光芒的白色云朵,只剩键盘,躲在一旁叹息。
盖上被子,几乎要被柔软融化。蘑菇般的褶皱逼近,搂住我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