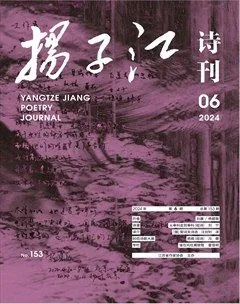船歌与莲蓬(组诗)
河阳船歌
她一边歌唱,一边做摇橹状
使小戏台有了船行水上的荡漾感。
“摇一橹来过一村,哎呦呦,
村村杨柳绿沉沉。”
我坐在小戏台下,像水中荷叶
或岸边杨柳间的鸟窝。
“闺女十八水上走,哎呦呦,
雪白牙齿红嘴唇。”
她面庞比歌声衰老,
还能把小戏台摇回初潮和春心?
“桃花朵朵落船篷,哎呦呦,
麦过清明大局定。”
我已越过寒露和霜降,
一支笔欸乃不绝,把人生划入暮境。
“饭香时分闻鸡啼,哎呦呦
春吃鱼头夏吃尾……”
在深秋,鱼背加大宽度和厚度
为冬日里的肥美筹备容积。
“摇一橹来过一村,哎呦呦
村村不见意中人。”
在长江入海口处的河阳船歌里,
感受意义的流逝与重生。
扬州慢
南宋以后用“扬州慢”词牌写作的人
周身充满一座城池的疼痛——
要么让扬州像受伤的头颅引领生命
要么躲开,去“念奴娇”“点绛唇”。
二十四桥与春风十里仍在。
幻想娶一朵芍药为妻的人,须暗藏
“感时忧国、才华横溢”这古老的病。
我平庸,喝茶、泡澡、吃炒饭。
楼船、夜雪、瓜洲渡
转型为游船、雪铁龙汽车、风景区。
我爬上马照相,手挥小钢笔
向铁马冰河中的前驱和利剑致敬。
长江对岸是镇江金山寺。
我一直喝醋养生,充满酸楚感——
谁是恨我怨我的法海、白娘子?
明月升起,像东海新生的一个婴儿。
篝火记
围绕篝火,围绕母亲的心。
春浅夜寒,我们伸出手
向篝火要求母爱——
木柴毕毕剥剥,是她的心跳。
七八个诗人,五六个村民,
在一堆篝火前成为兄弟。
读读诗,村民无表情。
谈谈稻子和雨水,村民笑了。
稻子和雨水是好诗篇。
母亲用绣着星辰的春夜
这一件宽大绸衣
把我们抱在同一个怀里。
篝火熄灭,母亲心碎?
我们散去,像孤儿各自流离。
唯有写诗能把长短句点燃,
向一张纸要求母爱。
温泉记
赤裸如婴儿,在温泉就是在子宫。
明月慈祥如母亲的脸。
丙申秋,与若干友人共浴
如同胞共生于母爱。
泉边,有岩石、松、佛龛、油灯……
川端康成怀念伊豆的温泉和雪,
写小说,用一个舞女的爱意
抵抗东京孤穷。
我也想起若干旧事,起风了,
泉边油灯显得危急。
江南温泉没有新雪和艳遇,
仍足以让一个衰朽者
恍惚回归夏天,像残荷重生尖尖角。
有蜻蜓二三,把我微秃的头顶
更新为一座停机坪。
一枝枯莲蓬
壬寅秋,陶渊明墓前
没有菊花和柳树。
草木脱俗,一概能表达清高,
隐士与君子仅仅口音不同。
有荷塘常相伴也很合适。
莲蓬以枯萎和疲倦的姿势
怀想荷花、蜻蜓和一个归人,
更显得触目惊心。
我俯身采摘一枝莲蓬,
像荷塘一样高举它
过安检通道,乘高铁回上海
一路被他者诧异地盯着。
像盯着光天化日下
一个用莲蓬淋浴头洗澡的人。
有一枝莲蓬隐喻荷塘,
我怎能藏污纳垢?
把莲蓬插进书房陶罐。
一抬头,就看见南山和田园
一低头,这写下的汉字
就与莲子没有了区别。
两匹马
两匹马艰难地亲吻——
伸长脖子,越过两道栅栏,衔接为一座桥
让彼此的血液和心跳一涌而过。
某年,我在草原马厩中拍摄的这张照片
让一座临时的桥,获得永恒。
它们亲吻三分钟,我扭过头去看远处山坡。
情侣间亲吻,需要类似的障碍才显得动人?
没有栅栏和难度的爱,平淡以至平庸。
平淡以至平庸的爱,更为罕见——
一个人如果把眼镜取下,放在床边,俯身,
就能一下子进入草原?
稻田诗会
一群诗人在稻田里
低头读纸上分行的汉字。
稻穗也低头读分行的米粒,
用溪流作为哽咽不止的喉咙。
若干农夫驾驶割稻机
演绎“诗人之死”这一命题?
必须以“来不及了”的紧迫感
说出满纸汉字亦即米粒。
远处,五峰山像笔架
恰好可以搁置四支笔、四季。
万物并作,生生不息——
稻田与书桌有类似的轮廓和潜力。
一行白鹭越过诗会
比越过糖烟酒交易会欢快优美,
把稻田和诗人之心
运输到更高远的境界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