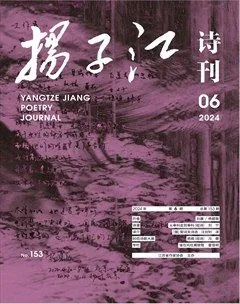青蛇(组诗)
方水池
希尼在诗中写到了亚麻池
童年的自然主义者
如何被扼杀在布满蛙鸣的池水中。
我的童年与亚麻无关
用来沤肥的长方形水池,十平方米
大小,深约一米,散落在
田野和地堂之间的高地上,盛满
荒芜记忆和野生时间。
像一只被凿穿的木舟,搁浅于荒野
池底野草蔓长,几乎淹没了
同样被弃置的石碌。
雨后夏夜,水池里的牛蛙
叫声比一头牛还要大:“空气中回荡着
密集的低音合唱。”(希尼语)
我们在池边奔跑,在池中跳跃,在不远处的
荆棘丛里捕捉金龟子——
这野蛮的生长,封闭、自由、快乐
我们当然无法想象,多年以后
那秃顶的中年,郁闷而焦虑,彻底丧失了
对星辰和大海的兴致。
而我通常是一个人穿过黄昏
带着自制的天文望远镜来到这里
观测星星——水池和石碌
构成一个凹陷于大地的天文台。
那时晚风清凉,星光嘈杂
周遭的田野和远山围着池子在“咔咔”地
旋动,处身于旷野中心
我突然感到一阵幸福的战栗
十亿光年之外的星星蜂拥而至
仿佛疯狂繁殖的果蝇
而随之升起的,除了无垠的孤独
还有一种难以驾驭的神秘
穿过水池的底部
越过云团、雷电和遥远的星系,最终
抵达秩序中的永恒——
他们捣毁了那些水池,而我固执地重建
这座私人遗址,在一首诗中。
野泳池
台风过后,是三日大雨。
仿佛屈从于一种暴力
小时候我们看待台风的态度
总是又兴奋又害怕——
风暴使大地沉沦为一所牢房
囚禁在黑色旋涡中
我们一次次裹紧并吮吸
那些由飘摇风雨所赋予的安全感
待风暴退去,连日的
大雨,再次将我们摁在家中
形同发霉的土豆。
当孩子们获得解放,迫不及待地
奔向野外,仿佛那里别有洞天
我们惊喜地发现,暴风雨为大地
准备了一份闪光的礼物:
一方水塘,横空出现于荒野
在那片沙地的最低处
几乎是一夜之间的造化——
深一米,阔数亩,波光潋滟
如同一块白果冻,凝住蚀骨的清澈
而阳光直捣水底,却搅不起
一池的空明与虚无——
这天然的、恩赐的野泳池!
我们迅速脱光衣服
像水鸟一样扑腾进水中,水位
刚好,露出大半个脑袋
撇开小伙伴们的嬉闹,我一个人游向
池水中央,丝绸一般黏滑的水体
抚慰着我,带着夏日的清凉
将数日来积聚于心中的块垒彻底融化
换个姿势,现在是仰泳——
我凝视天空,发现天空此刻也在
凝视我,像一个倒置的深渊
把一汪碧蓝倾注进池水中
我继续游啊游,一直游到池水变蓝
……恍惚遨游于白云间。
在水底,睁开眼睛潜游
目力几乎可以抵达池水的边缘
几座荒坟在那里摇曳——
整个水塘,原来被满荒野的坟头包围着
一个个隆起的孤独,纠集取暖的灵魂
池边的新坟,是邻居同龄小友的长眠之地
两个月前他溺毙于大海,因为
看不见的暗流——
那是我第一次目睹死亡。
而现在,畅游在布满死亡的坟墓中间
我们没有半点的恐惧和不安
死亡成为公开禁忌:一种随身携带的意志
或反抗,而海水才是内心隐秘的火焰
因此,继续游啊游——
一直游到海天交接之处,稍息
一直游到池水干涸之时,安息。
野蓖麻
那天黄昏,我躲到了
野蓖麻下。
那里曾经是孩子们的天堂
广播天线通过连接树的枝丫而增强了
信号:歌声里,有一棵橄榄树
和一个电波中的远方。
那时候,我的远方在哪里?
我当然无从知道。
我还是个孩子
刚偷了同桌的文具——
一支烫金钢笔,通体透蓝,形成
致命而闪光的诱惑
我把它埋在野蓖麻下。
作为一个秘密,它发育成一棵
羞答答的野蓖麻——
掌形叶片,遮挡着直射的阳光
铜锤状果实,浑身布满了刺
如同坚固的防御工事
我能抵御时间的拷问吗?
我只想逃到远方去,但远方
就是那个橄榄树的远方?
当我打开成熟的果实,我被那个
画面惊呆了:蓖麻种子
那光滑的大理石般的纹理中
竟藏着一幅微缩的航海图——
啊,蓝色的远方!
多年以后,当我涉水返回故乡
我早已不再小偷小摸
但岁月却无声偷走了远方的诱惑
还有当初的那棵野蓖麻。
落地生根
一种药草植物:易见,盎然
从《赤脚医生手册》里抽出它的
根、茎、叶和花果,仿佛
四季的轮回一并保存在书页间。
我们在墙头、屋角甚至瓦楞上
看到它的身影——
太常见了,以致我们忽略了
它的美和存在,而它
像钻出地底的精灵,倾心于繁殖:
从叶片边缘分裂出更多的
小叶崽,并长出乳白根须,一落地
便植入泥土,独自生长——
这,就是名字的由来。
“滥生的不死鸟!”爷爷竟会比喻
超强生命力里,肯定蕴含了
某些神奇的密码——
采摘它的叶子,剁碎,敷于
脓疮或发炎的伤口上
翌日便拔毒生肌,屡试不爽。
除了落地生根,爷爷的园子里还种有
路边青、艾叶草、野薄荷、金银花……
在民间,中草药就是一门
生存哲学,充满了粗野、廉价和
简单实效的智慧——
小时候爷爷将我们撒播于田埂、野地
与牛羊、鹅鸭放养在一起
“穷孩子粗生粗养,在任何地方
都可以扎下根来……”
作为异姓外来户,爷爷倔犟、低调
执着于田地认同和命运流转
像极了那棵毫不起眼的落地生根
临终时,他嘱咐我们——
埋我在田地,但你们的家不在这里
而在城市,在天涯,去吧
到那儿去落地生根,开枝散叶……
将爷爷的心愿带往都市
种在异乡阳台,我第一次看见它
开出灯笼般的花朵。
青蛇
青蛇是最后出现的。
我们前两天已将墓地修葺一新
今天过来祭拜的时候
发现坟头的石块塌落,蚁穴
钻空了山坟。
由于没带工具
只能徒手将坟墓整理好
我们像一个个虔诚的信徒
这些被祭拜的祖先
从未谋面,但他们躺在这里
让我们找到了来路——
黄土枯竭的血脉
如今,流淌在我们身上。
待我们收拾停当
潜伏在墓地旁的一条竹叶青
现身了:碧绿躯体
有一种纯粹的、剔透的晶莹
与身边的青草融为一体
但又提纯了人间的绿,超越
尘世的寻常——
哦,这修炼已久的精灵!
它似乎并不惧怕我们
从草丛中爬出
缓慢越过那条黄土路,身体
紧贴着土地的凹凸,优雅地起伏
仿佛在从容里游弋
它的吐信,一团微弱火苗
点燃了我们的恐惧
爬过黄土路,进入另一处草丛
它那小小的三角头
朝向我们装祭品的箩筐而来
我们击打石头
发出警告,防范它的入侵,但似乎
我们才是入侵者。
它停了下来
伏在草丛里朝我们张望,形成
紧张的对峙——
在我们的想象里
有猝不及防的一击,而毒液
是致命的蓝。
于是,我们开始撤离
在它的注视之下(转动绿眼珠)
待我们离开,它又爬回
墓地——
隐没在一个土洞之中。
美的捕获
他是一个善于捕捉风景的人
确切地说,他善于摄取
风景中美的神韵
不过更多时候,他是一个
耐心的狩猎者,贮聚着
出击的闪电——
静静潜伏于洼地里、草丛间
将自己伪装成一个背景,或者
把意志融进时间,成为等待的
沙漏:每一分每一秒
都飞出一只蚊子,伸长吸管,抽取他
快要耗尽的耐心和专注力。
他知道在水塘上空
将要上演一场关于生命的舞台剧
而作为导演,他甚至不计成本
在水塘里投下大量的小鱼和小虾:
哦,这赤裸裸的诱惑!
终于,鹭鸟现身了——
哨音盘旋着、滑翔着,掠过水塘
在他内心的湖面溅起一阵涟漪
暮晚的光,柔和、舒展
给白色的羽翼镀上了金边
高高的脚丫,意示它们就是
天生的舞蹈家?
在晚风、光、影交织的旋律里
白羽翩跹起舞;而在他圆形的注视中
那些恣意挥洒的自由与激情
仿佛就要溢出镜头之外
为他带来某种涌动的丰盈
他甚至有些疑虑
光圈禁锢了美,要拍下吗?
当他按下快门,他意识到必须将
它们放还于天地间——
美是艰难的捕获,也是自洽的
维持:对于秩序,还有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