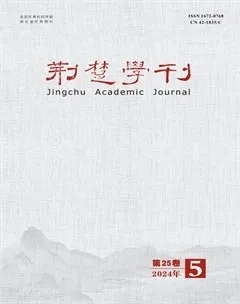助推:教育治理优化的第三条道路
摘要:助推是介于自由主义治理与家长主义治理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是通过改变选择背景中的某个因素来影响个体决策和行为的柔性方法。它避免了单纯的自由主义和家长主义治理的弊端,既尊重个体的选择自由,又能使个体的行为朝着预期的方向发展,将其应用于教育治理有其适切性和合理性,并有大量的循证实验验证了其有效性。在教育治理中应用助推需要结合决策环境和学生实际,活用“动机、理解权衡、默认选项、反馈、预计错误、重构复杂选择”等设计工具,遵循透明性、自由性、教育性、公益性等原则,充分发挥其治理效能,以提高学生决策的能力,帮助学生做出更好的选择。
关键词:助推;教育助推;教育治理;教育治理优化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768(2024)05-0052-08
收稿日期:2023-12-21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教育部重点项目“供给侧改革视域下高校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研究”(DIA230430);湖北省教科规划重点项目“湖北高校本科专业调整机制和路径研究”(2023GA067)
作者简介:肖未(1996-),男,重庆人,荆楚理工学院师范学院助教,硕士,主要从事教育管理研究;
戴伟(1980-),男,湖北红安人,荆楚理工学院数理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研究。
通讯作者:刘建银(1976-),男,四川邻水人,重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教师教育研究。
自古以来,人们在推进教育治理的过程中,存在着两种极端的价值取向——自由主义(Liberalism)和家长主义(Paternalism)。自由主义者认为人的选择自由不容侵犯,治理就应该给予人们充分的选择空间;家长主义则相反,认为人难以做出最优的判断和选择,主张个人让渡权力给政府,让政府行使公权力进而代替个人做出选择( 1 )。可是,实践中我们也经常看到权力“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恶性循环,说明自由主义式和家长主义式的治理都存在困境。那么,有没有介乎二者之间的第三种治理模式呢?近年来,依托于行为经济学理论出现了公共治理的第三条道路——自由主义家长制(Libertarian Paternalism)以及相应的政策工具——助推(Nudge)。这一模式不禁止任何选项、不限制选择自由、不利用经济杠杆,也不诉诸命令和指导,而是通过适当改变人所面对的选择架构(Choice Architecture)促使人们的行为选择发生预期变化[ 1 ],既保留了自由主义者捍卫的选择自由,又体现了家长主义者强调的政府引导,从而避免了单纯的家长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缺陷,值得教育公共治理认真借鉴。目前,助推已经成为将行为科学应用在公共治理中的成熟理论,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同时引发了新公共管理之后的行为公共管理又一研究热潮。本文讨论了助推理论的发展脉络及其理论基础,梳理了助推在国际教育治理优化中的应用实验,讨论了将助推工具应用在教育治理过程中的设计方式和原则,为优化我国的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提供新的思路。
一、助推的内涵与理论基础
助推,原意是指用胳膊肘或身体其他部位轻推别人以提醒或引起别人注意。塞勒和桑斯坦(Thaler & Sunstein)将之引入行为经济学原理之后赋予了它新的涵义,使之成为行为科学的一个关键概念。2008年,塞勒和桑斯坦在其合著的《助推:如何做出有关健康、财富与幸福的最佳决策》中首次提出了助推理论:助推是在不禁止任何选项、也不显著改变对人们经济激励的前提下,仅通过对决策者、决策程序、决策信息、决策环境和决策选项进行适当的调整变换,以小拨大地改变人们的行为。要算得上是一种助推,它的干预措施必须是容易避免的[ 2 ]。助推理论一经提出便得到广泛的应用,在医药健康、节能环保、减少财政支出、促进慈善捐助和优化教育治理等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得到了各国政府的青睐。英国政府邀请塞勒组建了行为洞察力小组(Behavioral Insight Team),美国政府则邀请桑斯坦担任信息与监管事务办公室(the Office of Information and Regulatory Affairs)主任,将助推理论广泛应用于政府的管理和决策,从而大大减少了政策执行的阻力,提升政府的执政效率。在我国,以中科院心理所、浙江大学、中山大学等为核心的研究团队,正零星地将助推理论应用于公共管理和教育治理的实践之中。
助推脱胎于行为经济学理论(Behavioral Economics)。行为经济学是主张将心理学应用于分析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流派。行为经济学认为经济生活中的人是“社会人”(Humans),而不完全是“经济人”(Econs)。社会人具有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有限意志力(Bounded Willpower)和有限自利(Bounded Selfishness)的三重有限性[ 3 ],因而在做决策时会受制于有限的信息与认知偏差,难免做出不利于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助推就是通过利用人的这种认知偏差,改变影响决策的选择架构帮助“社会人”作出更好的选择。与传统的禁令和经济激励不同,助推不会对“经济人”的决策产生影响[ 4 ]。助推的心理学基础是卡尼曼(Kahneman)所提出的认知加工双系统理论(Dual Process Theory)。该理论认为人类大脑有两个认知系统:基于直觉的自动式思维系统(Automatic System)和基于理性的反思性思维系统(Reflective System),也称为系统1和系统2[ 5 ]。系统1具有不受控、不费力、联想、速度快、无意识、熟练等特点,不占用或占用很少的心理资源,模块化封闭运行,反应自动化,容易受到背景的影响,通常我们只能意识到其加工结果而意识不到加工过程;系统2具有受控、费力、演绎、速度慢、有意识、依照规则等特点,占用较多的心理资源,不易受环境的干扰,其加工过程和结果都可以被意识到。系统1和系统2是紧密联系的,同时对决策或推理过程产生作用。系统1和系统2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是“助推”工具得以应用的潜在心理机制。
二、助推在教育治理优化中的循证实践
助推是通过改变决策环境来影响决策者行为的柔性方法,既尊重了个体的选择自由,又能促使个体做出设计者期望的行为,应用于教育治理过程中有其适切性和合理性,部分研究者实施了循证实验,并取得了部分成效,为教育治理优化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助推应用于教育治理过程中的适切性
将助推应用在教育治理过程中有其适切性与可行性。一方面,教育治理过程中教育者扮演了“选择架构师”(Choice Architect)的角色,承担着为学生建构选择背景的责任。他们对学校环境、教室环境等选择背景的设置,影响着学生的选择和行为。同时,教育者也身处一定的选择背景之中,很多时候教育的情景通常不允许他们停顿下来进行反思性思考,仔细考虑各种可能的选择、决定最佳的行动方案,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认知偏差的影响[ 6 ]。另一方面,受教育者是发展中的“社会人”,具有有限理性、有限注意力和有限自制力,容易受到认知偏差的影响,做出违背理性、损害自己利益的决策。教育决策是跨期决策,是在年轻时做出的、涉及直接成本和潜在利益的决策,不会马上产生效果,受教育者常常受制于认知偏差,容易夸张贴现当下的快乐而忽视长久的利益,因而最需要被引导、被助推。最后,作为一种治理工具,助推在塞勒和桑斯坦正式提出其概念之前就已经存在于教育治理中。例如,学校走廊上贴的“禁止喧哗”、垃圾桶前贴的“绿色脚印”等标志,这些司空见惯的环境设置都算是一种助推手段,只是鲜有人意识到这是一种科学的、系统的治理工具。
(二)助推在教育治理中的循证研究
关于助推的循证研究较为零散,散见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SNo+Snp6JjAakrZptyYoGOqSVWU+CYQKoewAJ7LTo4w=等各个领域,对其进行系统梳理首先要探索分类框架,将其统整起来。根据助推是否透明、是否引起反思性思考两个维度,可以将助推划分为四种类型,即透明的类型1助推(Transparent Type 1 Nudge)、不透明的类型1助推(Non-transparent Type 1 Nudge)、透明的类型2助推(Transparent Type 2 Nudge)和不透明的类型2助推(Non-transparent Type 2 Nudge)[ 7 ]。类型1助推通过维护或利用个体的自动思维影响其行为,并不促发人们的反思性思考。类型2助推则通过影响个体的注意力而引起反思性思考,然后由个体自主决定做还是不做那个行为。透明的助推,即被助推者明确知道其背后的意图以及追求行为改变的手段,可以合理地预测预期的结果。不透明的助推是在被助推者不能猜出其意图、也不能看穿其手段的情况下影响个体的行为和选择的助推方式。
1.透明的类型1助推
透明的类型1助推公开了其背后的意图和采取的措施,以及所要达到的预期结果。这类助推不涉及反思性思维,而是通过影响人的自动化行为产生作用。具体而言是通过激活个体的本能反应、习得性反应和改变容易忽视的默认选项等方式产生作用。
教育治理中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把小学食堂的背景音乐设置成古典钢琴曲,通过音乐让学生们安静吃饭不再大声喧哗,从而来维持就餐秩序。这一助推通过激活学生的本能反应产生作用,学生们不用反复思考“现在要不要好好吃饭安静听音乐”就会自动安静下来。查尔莫斯(Chalmers)等人发现,有了古典音乐之后,孩子们产生的噪音会比没有音乐声低12%,食堂工作人员纠正孩子们不良习惯的次数也减少了65%[ 8 ]。这种方式给孩子们建构了一个舒适的用餐环境,间接地提升了他们的幸福感,取得的约束效果也比传统的贴告示、呵斥和禁令要好得多。这种助推没有压制学生的聊天的自由,也没有操纵的意味,其背后的意图和采用的措施很容易就被学生们知晓,也能取得较好的干预效果。利用可见的默认选项也是一种透明的类型1助推。例如,将打印机设置为默认双面打印,这一助推利用人的惰性或安于现状产生作用。大部分人在打印资料的时候不会在意是单面打印还是双面打印,不会去调整打印机的默认设置,除非要打印的资料有特别的要求。人们可以猜到默认双面打印的目的是节约纸张,也可以随时选择单面打印。张希川在2008年时估算,如果将所有的学位论文进行双面打印,我国学位论文用纸量将减少2100吨或更多[ 9 ]。美国联邦科学评估处(Office of Evaluation Studies)估计,将默认打印模式由单面改为双面打印,联邦政府每年能节省4.4亿美元的印刷开支[ 10 ]。简单的设置能产生以小拨大的效果。
这类助推针对的是个体的自动性思维,通过人的本能或习得性反应产生作用,不涉及反思性思考,不能算是个体的主动选择,有违背个体意愿、损害个体利益的风险。因此,教育者在设计和应用这种助推时,还需要提供方便的投诉渠道和退出机制,保障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还要为可能出现的直接的、预期的结果以及间接的、附加的结果承担责任。
2.不透明的类型1助推
不透明的类型1助推通常在“雷达下面操作”[ 11 ],不激发反思性思考也不告知个体助推的目的和手段,通过影响个体的直觉思维改变个体的行为。它影响的不是个体的选择,而是个体的自动行为。这一类型的助推是最不显著的,既不会引发反思性思考也不会引起个体的注意,在实践中常常被忽视,甚至在被人告知我们正在被这个因素所影响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不太可能,即使结果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也会怀疑其真实性与可信度[ 7 ]。这种助推的一个经典实验就是“大小盘子”实验,通过改变盘子大小来控制学生的卡路里摄入量[ 12 ],减少学校食物的浪费[ 13 ]。盘子的大小没有影响学生的饭量,也没有改变食物的味道,更没有激发人们的反思性思考,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助推利用了人们的自动习惯产生作用——装满这个盘子并吃完它。
另一个实验是“默认加入”短信服务实验。短信服务是指学校通过短信的形式向家长提供关于他们孩子的表现、出勤率和作业的信息。博格曼和罗杰斯(Bergman & Rogers)选取美国初高中学生的家长作为被试,将之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的家长“默认加入”短信服务,对照组的家长则需要“选择加入”,二者获得的短信服务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实验组的家长任何时候都可以选择退出,对照组的家长任何时候都可以选择加入。研究发现,美国初高中孩子的父母在默认加入短信服务和选择加入短信服务方面,参与比例存在很大差异。选择加入组的家长参与短信服务的比例为7.8%,默认加入组的参与率却达到了96.5%。在默认加入组中选择退出的比例不到4%,尽管他们在这一学年的任何时候都可以选择退出[ 14 ]。这一实验同样没有涉及家长的反思性思考,而是利用家长的惰性产生作用,具体而言是利用了其“默认偏差”(Default Bias)产生作用——个体面对选择时通常选择默认选项。
这一种类型的助推是最不易察觉的,它们不引起个体的反思性思考和有意识的选择,而是通过技术手段和对公民的心理操纵导致其行为改变。因此,教育者在设计这类助推时,首先要保证助推对受教育者的成长是有益的,其次要为其直接的、潜在的后果负责,保障他们选择的权利和退出的权利。特殊情况下,需要保障实施助推的民主程序,允许公开征求意见,尊重受教育者的意见。
3.透明的类型2助推
这一类型的助推公开了目的和手段,并且激活了反思性思维系统,个体可以轻易地推测其意图和手段,自行决定是否做出行为改变。这种助推的手段和目的都是透明的,个体可以轻易地选择拒绝。一般是通过突出特征、行动、偏好和结果,或者提供反馈和决策机制,促使人们作出与自己偏好相一致的选择。这类助推的经典例子就是“截止日期”实验。艾瑞里和韦滕布罗赫(Ariely & Wertenbroch)选取了麻省理工学院的99名学生作为被试,这些学生必须要为一门课程写三篇课程论文。实验设置了三个实验组,第一组设置了平均的截止日期,而第二组则是由学生自己设置截止日期,第三组只有最后期限。三组成员的论文要求和评分标准都一样,每超过截止日期一天,就有1美元的惩罚。研究发现平均设置截止日期的学生比没有截止日期的学生取得了更好的成绩;外部设置截止日期的学生比自我设定截止日期的成绩要好;当有选择的时候,超过三分之二的学生设定了中间期限[ 15 ]。学生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设置截止日期就是为了提高作业的完成率和作业的质量,也可以自由地选择要不要在截止日期前完成作业。这一助推手段利用了学生的有限意志力产生作用,学生们当然知道早点完成作业的效果更好,但是总是忍受不住诱惑被其他有意思的事情所吸引。更具体一点,这是利用了行为经济学中的现状偏差(Status Quo Bias)( 2 )产生作用,和完成作业相比学生们更倾向于维持现状。
还有一种实验是“目标设定”实验。克拉克和吉尔(Clark & Gill)发现,让大学生自己设定关于任务和成绩的目标会提高大学生对任务的投入程度,提高测试的成绩[ 16 ]。我国学者王晓庄选取了天津中学180名初中生作为被试,测量他们的平板支撑和跳绳成绩。实验设立了三个小组,第一组提供精确的目标,如跳绳196个;第二组提供粗略的目标,如跳绳190~200个;第三组则是无目标组。研究发现,三组的平板支撑和跳绳成绩均存在显著差异,都是精确目标组高于粗略目标组,粗略目标组高于无目标组[ 17 ]。这些助推实验利用了学生的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产生作用,锚定效应是指个体在不确定情境的判断与决策过程中,呈现的一些无关数值信息会影响其随后的数值估计判断,使得其最后的估计结果偏向该数值的一种判断偏差现象[ 18 ]。学生清楚地知道那些目标是什么,可以选择要不要达到那些目标,可以决定自己要付出多少努力,这一助推不改变学生的体能,也能提升学生的体育成绩,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透明的类型2助推是最温和的、最不具侵略性的助推,它引导学生以一种可以预测的方式改变自己的行为,同时捍卫他们选择的自由。这种类型的助推公开了目的和手段,学生可以自由地质疑助推的效果并行使自己的选择,较之于传统的政策手段,它是非干扰性的,教育者只需要对学生选择造成的轻微干扰承担责任。
4.不透明的类型2助推
不透明的类型2助推卷入了反思性思维,但没有公开其目的和手段,具有欺骗性,可以称之为对个体选择的“操纵”。这类助推通过对个体心理不透明的操纵产生作用,比传统的政策措施更具有侵略性。这一类助推的典型实验就是“框架效应”实验。菲尔德(Field)将即将入学的纽约大学法律系学生随机分配到两个资助计划之中,这两个资助计划提供相同的资助金额。第一个资助计划被命名为助学贷款,如果学生毕业后选择了一份低收入的公益性工作,这笔贷款将由学校承担。另一个资助计划被命名为学费减免,如果学生毕业后选择了高收入的非公益性工作,就必须偿还这一部分学费减免。对资助的不同命名导致了学生显著的行为差异,获得学费减免的学生在毕业后选择低薪公益性事业的可能性比获得助学贷款的学生要高36%~45%[ 19 ]。学费减免与助学贷款的资助金额完全相同,选择公益性工作获得减免和选择非公益性工作收回减免的资助策略在经济学上也没有任何区别,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是学生对“获得减免”与“失去减免”的主观感受不同。
另一个典型的实验是弗赖尔(Fryer)设计的“教师激励框架”实验。研究设计了两种激励方案,两种方案的奖金数额都相同。一种方案是在学年初给教师发放奖励,如果期末学生考试成绩没有得到提高,则要求教师返还奖金;另一方案则是根据学生的期末成绩发放奖金。该研究发现在先发奖励后收回的激励模式下,学生的数学成绩才有所提高[ 20 ]。这两个助推实验利用了“社会人”的“损失规避效应”(Loss Aversion)产生作用,损失规避是指人们憎恶失去属于自己的东西,具体而言,失去某件东西使你难过的程度比得到这件东西使你快乐的程度大一倍[ 21 ] 39。这一助推变更了奖励发放的时间和机制,不提升奖励金额就能激励教师付出更多的努力,提升教育质量和学生的成绩,切实提升了教育治理的效果。在教育财政经费紧张时,也可以试着在不提高奖励金额的情况下,优化教育评价机制和奖励发放的时间和机制来提升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三、助推在教育治理优化中的应用策略与原则
助推通过利用人的认知偏差产生作用,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治理工具,适用于社会、健康、环保、减少财政支出、慈善、教育等不同领域,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不可否认,在应用过程中,助推也引发了部分争议[ 22 ],因此,在教育治理中应用助推需要遵循相应的策略与原则,提升助推工具有效性的同时回避争议。
(一)助推的应用策略
如何设计出一个好的助推,优化人们所面对的选择架构?塞勒提出,好的选择架构应当包括六个基本原则:动机(Incentives)、理解权衡(Understand Mappings)、默认选项(Default)、反馈(Give Feedback)、预计错误(Expect Error)、重构复杂选择(Structure Complex Choices),从上述6个词语中各取一个字母,正好构成了“助推”(Nudges)[21] 119。在教育治理中应用助推也应遵循助推设计原则,提升助推工具的有效性。
1.动机(Incentives)
人们做出选择要受到动机的驱动,对动机的觉察与遵从影响着人们的选择。但“社会人”不能一直觉察自己的动机,很容易被新的刺激带偏,忘记自己做出这个行为的原因以及这个行为将会导致的后果。因此,选择架构师必须设计出一种选择体系,提升动机的显著性,引发个体的反思性思考,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自己的动机上面来,做出最优选择。例如,在纸巾盒上设计小树苗形状的进度条。一方面,可以让人直观地了解盒内的纸巾数量,以便及时补充;另一方面,可以让人们在使用纸巾时从进度条联想到树木被砍伐的情境,从而唤起使用者保护树木、节约用纸的动机,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构成浪费[ 23 ]。
2.理解权衡(Understand Mappings)
决策者在决策时会将选项的信息转化为自己容易理解的、易于比较的、更加切身相关的经验并加以权衡,最终选择最满意的结果。所谓权衡是指对每一个选项所对应的行为及行为后果进行分析,最终得到满意结果的过程。然而,要决策者理解并权衡每一个选项是不现实的,有些选择远远超过了决策者的理解范畴,很难进行权衡,例如,初次接触大学专业的高考生很难从中选出真正适合自己的专业。一个好的选择架构能够使人们改善自己的权衡能力,从而做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在设计选择架构时,选择架构师可以使各种选择的相关信息更容易被理解,方便决策者进行权衡。例如,某些运动软件将卡路里消耗的数值从多少千卡变成一粒花生或者一块曲奇饼等食物图,让决策者直观地看到自己的运动量,决定是否继续锻炼。
3.默认选项(Default)
人是具有有限理性和有限自制力的“社会人”,很难对每一次决策进行理性的分析,在分析之后也很难坚持执行。在决策时,人们受到惰性、现状偏见、禀赋效应( 3 )等认知偏差的影响,更倾向于选择最直接、最简单、不需要付出任何努力的默认选项。无处不在的默认选项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好的默认选项会帮助人们以最省力的方式得到满意的结果。江程铭通过实验室试验和现场实验研究发现,应用默认选项,可以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增加捐款[ 24 ],设计捐献“被试费”的默认选项,可以提高被试的捐献概率;当有多个金额选项时,将较高金额作为默认选项,可以提高平均捐款额。
4.反馈(Give Feedback)
教师和学生是每天被大量选择和提示淹没的“社会人”,容易忽略或是做出错误的选择。一个好的选择架构是能提供即时的反馈,提示人们的行为是否得当。其中一种重要的做法是在教师和学生决策时提供“出错预警”和邮件提示。教育中的决策很多是跨期决策,很多行为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够得到结果。学生很容易放弃需要坚持的长期学习,选择即时能够得到回馈的娱乐活动,有研究表明,一门慕课的注册者可能成千上万,但是,大多数学生在两周左右就失去兴趣,课程的总体完成率大概只有5%至10%[ 25 ]。如何给学生提供即时的反馈,帮助学生做出最优选择是教育者需要思考的命题。
5.预计错误(Expect Error)
助推产生作用的方式是通过回避或利用人的认知偏差,这也意味着设计助推,必须考虑到人所固有的认知偏差以及在具体情境中可能出现的错误,并进行相应的补救。例如,为了防止出现学生因忘带身份证无法进入考场的情况,公安在高考考场外设置“户籍窗口服务点”[ 26 ]。一个好的选择架构能允许他的使用者出错,并对此给予最大限度的宽容。学生是发展中的“社会人”,更容易受到认知偏差的影响,做出错误的决策。教育者需要理解学生的认知偏差,以及在决策时容易做出的错误行为,并设计出好的选择架构予以纠正。
6.重构复杂选择(Structure Complex Choices)
人们做出最佳选择的概率基本取决于可选择项目的复杂性。当面对少量容易理解的选项时,个体倾向于对所有选项的性质进行分析,然后在某些选项中进行权衡。当选择范围扩大时,人们很难对每一个选项进行权衡,从而陷入决策困境。因此,在面对复杂决策时,人们会采用“逐步简化策略”,设立不同的筛选标准将复杂、繁多的选项简化成少数可以权衡的选择。一个好的选择架构会提供一种结构,帮助决策者重构复杂的选择。例如,我国各高校针对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开辟了入学的“绿色通道”,采取一站式服务,以集中快速的办理方式提供给有此需求的学生[ 27 ],简化了助学贷款的办理程序,提高了助学贷款的使用效率,确保助学贷款能物尽其用,切实助力寒门学子圆梦大学。
(二)助推的应用原则
助推理论源于实践并指向实践,助推的效果也需要实践的检验。助推需要借助科学实验才能得到验证和推广,比过去的理论思辨更注重科学证据。当然,循证实验的成功并不代表助推就可以不加审视地推广到所有教育领域中,同一类型的助推也有取得异质性结果的可能[ 28 ]。因此,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需要对具体的助推手段进行伦理性审查,具体环境具体考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教育中应用助推必须满足透明性原则、自由性原则、教育性原则和公益性原则,前两条原则针对助推措施本身,后两条原则是为了满足教育领域的特殊要求。
(1)透明性原则
透明性原则是指,选择架构师明确地告知被助推者,选择架构的设计目的为何,应用了哪些助推手段以及怎样退出。告知某人正在被助推并不会影响助推的效果,但如果不告知被助推者则会有操纵的嫌疑,引发不必要的道德与法律问题。透明性原则来源于罗尔斯的公开性原则。公开性原则的简单形式就是禁止政府采用一种不愿意公开或没有能力公开的政策[ 29 ] 3。教育领域对助推的透明性有着更高的要求。学生是发展中的人,反思性思维水平不高,很难发现与监督学校的助推手段,在学校中应用助推还需要公开更多的东西,需要告知学生自己正在被助推,利用了他们的哪些认知偏差。此外,教育决策并不全是由学生自己决定,大多时候是监护人在替学生做出选择,教育领域的助推不仅要对被助推者公开透明,还要对学生的监护人公开。
(2)自由性原则
自由性原则包括选择的自由和退出的自由,前者是助推理论本身的要求,后者则满足了教育领域的特殊性。从对个体的选择干预程度来看,自由主义与家长主义之间存在一种连续性,不是两个相互割裂的范畴。助推手段不全是自由主义家长制,只有当那些坚持自我的人可以轻易地避免助推的影响时,助推才可以被称为自由主义家长制。因此,在教育中设计和应用助推时,必须控制助推的认知成本,减小助推的强制性,降低助推手段对个体选择的干预,保障学生选择的自由。在学校场域中,选择架构师与被助推者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某些选择架构中的“自愿参加、自愿退出”字样带有强制意味,有“操纵”的嫌疑。具体而言,学生的身心发展水平有限、社会经验不足,容易将教师视为权威,不敢违背教师的意志做出与教师期望相反的行为。因此,在教育领域中,选择架构师设计的助推不能禁止任何一个选项,也不能使其它选项在时间成本、麻烦程度、社会制裁等方面的成本显著增加,还要明确告知被助推者退出的方式与途径。
(3)教育性原则
在教育领域中成功地应用助推,最为关键的是助推必须符合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和宏观的教育目的,不能与学生品德的培养、知识技能的传授、学习习惯的养成等学生发展的核心要义相冲突。对学生或教育过程直接或间接的负面影响都应予以排除,不能为了满足助推者的私人目的而损害学生的利益。教育的目的是实现学生的发展,使之能独立地适应将来的生活。决策能力是学生适应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一种能力,但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担心的,部分助推利用了选择者的认知偏差,不会引起学生的反思性思考。这种助推减少了学生自主决策的机会,降低了学生决策的能力,使学生对默认选项产生依赖,在撤销助推之后不会自己做出选择。在教育领域应该将助推与助力[ 30 ]两种政策工具相结合,帮助学生做出更好选择的同时提升学生决策的能力,这样才能让学生更好地适应将来的生活,成为独立的、大写的人。
(4)公益性原则
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公共性事业。教育中的助推必须面向全体学生、指向全体学生的共同利益,不能通过牺牲某部分学生的“小我”来成就“大我”。正如罗尔斯所说,“每个人都拥有一种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整个社会的福利之名也不能逾越。”[ 29 ] 3每个人都有选择参与和不参与助推的权利,每个人都有选择与不选择的自由,不能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损害学生选择的权利或是限制学生选择的自由。长期以来,某些学校的“唯分数论”做法,将学生割裂为成绩好可以被教育、成绩差不能被教化两个群体,片面地看待学生的发展,对学生进行差别对待,明显违反教育机会人人均等的教育原则。助推通过改变环境中的某个因素产生作用,不易被察觉,极有可能被当作是加大优生与差生之间差距的筛选器,违背教育公平。为了回避这一风险,教育中的助推更应该面向全体学生,帮助全体学生克服有限理性、有限注意力、有限自制力的钳制,做出更好的选择,产生更好的行为,实现更好的发展,成为教育公平的助推器。
四、结语
每一种政策工具都有其适用的范围和固有的局限。虽然助推已经在健康、环保、社保、政治、经济、慈善等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以小拨大的效果终究有其限度,助推只能作为传统政策工具的补充手段,无法彻底取代传统的政策规定。此外,助推工具本身也存在着局限,首先是理论基础的局限,助推理论以行为经济学理论为基础,行为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依附性决定了助推理论创新的有限性[ 31 ]。其次,助推的潜在心理机制依旧是神秘的“黑匣子”。尽管心理学领域对认知偏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认知偏差作用的机理还是众说纷纭。一种助推工具往往利用了多种认知偏差产生作用,彻底解开助推理论的“黑匣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教育者、管理者们还需认识到比起设计或应用某个具体的助推手段,更重要的是改变人性假设与学生观,认识到学生不仅仅是“发展中的人”,还是“发展中的社会人”。教育者需要接受学生是具有有限理性、有限自制力、有限注意力的“发展中的社会人”事实,接受学生总是会受到认知偏差的影响从而做出不符合自己偏好、损害自己利益的决策的事实,积极看待学生的“错误”行为,不对学生求全责备。这才是在教育治理中应用助推提高学生决策能力、帮助学生做出更好选择,实现教育公共利益最大化,达到善治的关键所在。
注释:
(1)例如,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对“在家上学(Homeschooling)”就存在两种极端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尊重儿童的受教育选择权,给予其在家庭的上学自由或者应该允许家长合伙开设微型学校,给予其仅接纳自己孩子在微型学校就读的自由;但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家长不可以也没有能力让孩子在家上学,因为义务教育是国家事权。孩子应该也必须到国家开办的公立学校或国家许可开办的私立学校上学,否则便被视为妨碍办学。
(2)现状偏差是指比起改变人们更倾向于维持现状。
(3)禀赋效应是指人们往往会对自己拥有的东西赋予更高的价值,更不愿意卖出。
参考文献:
[1]何贵兵,李纾,梁竹苑.以小拨大:行为决策助推社会发展[J].心理学报,2018,50(8):803-813.
[2]Thaler R H, Sunstein C R. Nudge: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wealth,and happiness[M].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8:6.
[3]Mullainathan S,Thaler R H. Behavioral economics[J].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 2001:7948,1094-1100.
[4]Hansen,Guldborg P. The definition of nudge and libertarian paternalism:Does the hand fit the glove?[J]. European Journal of Risk Regulation,2016,7(1):155-174.
[5]丹尼尔·卡尼曼. 思考,快与慢[M]. 胡晓姣,李爱民,何梦莹,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6]马克斯·范梅南. 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M]. 李树英,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4:104.
[7]Hansen P G,Jespersen A M. Nudge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choice[J].European Journal of Risk Regulation,2013,4(1):3-28.
[8]Chalmers L,Olson M R, Zurkowski J K. Music as a classroom tool[J]. Intervention in School and Clinic,1999,35(1): 43–52.
[9]张希川,李丹.应大力推行学位论文的节约型排版规范[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8(12):60-62.
[10]刘骥,王易昕.行为经济学在教育领域的前沿实践与启示[J].教育与经济,2020,36(4):68-74.
[11]Bovens L. The ethics of nudge[J]. theory & decision library, 2009(10):207-219.
[12]Wansink Brian.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at increase the food intake and consumption volume of unknowing consumers[J]. Annual Review of Nutrition, 2004, 24(1):455-479.
[13]杨文娟.把学校食堂办好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J].人民教育,2020(22):40-42.
[14]Bergman P,Rogers T. The impact of defaults on technology adoption, and its underappreciation by policymakers[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7(6721):1-36.
[15]Dan Ariely,Klaus Wertenbroch. Procrastination,deadlines,and performance:Self-control by precommitment[J]. Psychological Science,2002,13(3):219-224.
[16]Clark Damon,Gill David,Prowse Victoria,et al.Using goals to motivate college students: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field experiments[J].Rev Econ Stat,2019,102(4):1-45.
[17]王晓庄,安晓镜,骆皓爽,等.锚定效应助推国民身心健康:两个现场实验[J].心理学报,2018,50(8):848-857.
[18]Tversky A,Kahneman D.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Heuristics and biases[J].Science,1978,185(4157):17-34.
[19]Field E. Educational debt burden and career choice:Evidence from a financial aid experiment at NYU law school[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2009,C37rNatBmAI1glIviYiTK3QggpVmrZ69jN/0HXsI/PU=1(1):1-21.
[20]Jr R, Levitt S D,List J,et al. Enhancing the efficacy of teacher incentives through loss aversion:A field experiment[J]. NBER Working Papers,2012( J24):1-36.
[21]Richard H,Thaler Cass R,Sunstein.助推:如何做出有关健康、财富与幸福的最佳决策[M]. 刘宁,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
[22]朱敏. “大瓶可乐禁售令”被法院驳回,纽约市长表示将再上诉[N/OL].中国广播网,2013-03-14[2023-6-21]. http://china.cnr.cn/yaowen/201303/t20130314_512147171.shtml.
[23]贾浩然.助推及其对技术设计的启示[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8,34(6):44-50.
[24]江程铭,马家涛,孙红月.助推爱心:利用默认选项促进捐赠行为[J].心理科学,2019,42(5):1174-1179.
[25]王宇.慕课低完成率问题的归因与解法[J].现代教育技术,2018,28(9):80-85.
[26]高翠,张永超.潍坊市:考场外 他们用爱与责任守护高考[EB/OL]. (2023-06-7)[2023-06-23].https://learning.sohu.com/a/682936031_100024676.
[27]张书维,梁歆佚,岳经纶.行为社会政策:“助推”公共福利的实践与探索[J].心理科学进展,2019,27(3):428-437.
[28]Damgaard M T,Nielsen H S. Nudging in education[J].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2018,64:313-342.
[29]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30]Gruene-Yanoff T,Hertwig R. Nudge versus boost:How coherent are policy and theory?[J]. Minds & Machines,2016, 26(1-2):149-183.
[31]贾云鹏,狄昱函,曾红权,等.教育经济学的新发展:教育行为经济学介评[J].教育与经济,2020,36(2):79-87.
[责任编辑:王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