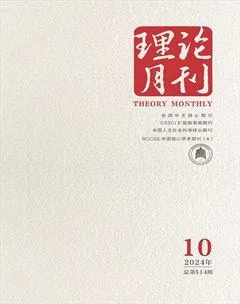中国社会科学概念建构的体系化与通则性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社会科学在一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概念建构问题不仅长期受困于古今之争、中西之争、普遍与特殊之争、本土化与世界化之争,还有规范与实证之争、定性与定量之争,等等。诸多非此即彼的争论把研究者带入无意义的陷阱,并最终交由非学术因素来裁定。那么,概念建构是否可能以及如何走出长期以来的争论?
其实,在克服诸多争论方面,概念建构需要考虑四个要素的统一。卢克指出,社会科学研究要时刻处理好几组关系,包括“树皮”(每个学者具体关注的问题)与“树木”(学术界普遍关注的议题)之间、“树木”与“森林”(知识生产领域)之间以及“森林”与整个“生态系统”(社会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因此,对“树皮”的具体研究要有意义,必须着眼并关联到整个“生态系统”1。那么,具体到中国社会科学的概念建构而言,最基础的日常研究工作是专注于中国社会具体领域、具体经验实践的概念提炼,使之对具体某一类社会政治现象有较普遍的解释力,形成有生命力的概念之树。不仅如此,概念建构还要进一步为树状的具体概念之间建立逻辑的关联性,进行体系化,形成一片茂密的概念之林,进而关联到“小系统”(中国文化与社会政治实践)以及“大系统”(世界格局与人类文明进程)。唯有从实践中建构具体概念之树,并且把概念之林与供给滋养的空气、阳光、土壤、水分等生态系统结合起来,才能让具体概念在概念体系化及其政治社会与文化环境中找到恰当位置。
对中国社会科学的概念建构而言,还需要考虑社会科学本身的属性。所有社会科学都离不开社会性与科学性两个基本支撑点。前者以价值判断为先导,后者强调价值中立,两者之间必然存在张力。这不仅使社会科学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达成“高度共识”2,而且推动着社会科学的持久争论与动态变迁。一方面,社会性要求中国社会科学的概念建构因应中国社会结构、文化土壤与历史变迁,围绕中国社会问题展开体系化建设;另一方面,科学性要求跨文化与社会体系的世界交流与传播,实现世界普遍的通则性。虽然具体概念是依据中国经验实践而提炼和建构的,但在超越其具体情境与规范条件之后,还可以对世界其他国家与社会的相类似现象具有解释力,由此才能在国际社会“传播开”与“听得懂”。这样的概念建构才有更长久的生命力,中国研究者才能参与世界大问题的讨论,并在国际学术界立足且得到承认。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的概念建构需要符合国际学术界的通则性要求,用科学规范的价值中立原则来对冲非理性的传统观念与非科学的利益诉求。
换言之,体系化与通则性是中国社会科学概念建构的一体两面,涉及概念建构与延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其中,体系化是中国社会科学概念建构的目标指向,是刻画完整中国社会并构成“何为中国”的知识基础,而通则性关系到“中国何为”的问题,是让据于中国现代化实践的社会科学概念超越中国社会本土,提防概念建构在体系化之后走向“内卷化”,从而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持续的影响力与生命力。最终,“中国式概念”可以解释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同类现象,“中国制造”的社会科学知识产品可以为人类文明进程指明更美好的未来。然而,无论是概念建构的体系化还是通则性,都必须直面概念建构本身的限制性条件。
二、概念建构的限制性条件
概念建构能否走出中国社会科学长期以来面临的诸多争论,前提在于清醒意识到社会政治概念在本质上是有争议的1。这些争议具体体现为抽象程度、情境和价值规范三个限制性条件及其之间难以化解的交织。
其一是“抽象阶梯”问题。社会科学都是据于社会生活具体经验实践归纳而建构概念,对具体范围与特定领域的社会现象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社会现象在多大地域范围出现,多长时间范围有效,对概念提炼的有效性与可信度具有重要影响。萨托利在国别比较的政治学研究中提出了概念分析的“抽象阶梯”理论,按照概念的抽象程度或者与社会真实现象的距离远近,划分出高级范畴的普适性概念、中级范畴的一般性概念以及低级范畴的轮廓性概念,分别对应跨地区、地区内与国别分析的三种抽象程度2。然而,对一般意义的社会科学而言,国家并不是一个最小范围的分析单位,甚至往往可能是最大和最终的概念范畴。因此,科利尔进一步使用“家族相似性范畴”与“辐射型范畴”3,在横向上弥补对同类社会现象的概念提炼,从而使社会科学概念得以从纵横双向展开立体化建构。对具象世界的提炼范围越大,抽象程度越高,概念的普遍化程度越高,但具体现象与事件在概念建构中的轮廓越模糊,作用越小,反之亦然。
其二是时空情境条件问题。无论是萨托利还是其修正者都没有意识到,“抽象阶梯”范畴只能适用于高度同质化的语言文化与社会情境。一旦跨文化与社会体系,“抽象阶梯”就因概念所依托的语言系统不同而失去范畴性意义。中国社会科学的概念建构需要考虑情境条件的限制。情境条件包括时间与空间两方面变化的问题。在空间维度上,中国是自成一体还是作为世界的一部分?如果是前者,概念建构只适合于中国超大规模社会独特的地理环境及由此发生的局部社会现象,而无须考虑中国之外的区域适用性问题。必然结果是,形成的所谓“地方性知识”无法参与国际学术对话与跨文化比较。在时间维度上,把中国定位为传统文明古国,还是贫穷落后的近代中国,抑或是当代中国?这就意味着,中国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变动不居的,概念建构必须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来定位中国属性。中国社会科学首先要回应当下的社会问题与现象,带入传统与西方的相应资源,进而从时空变动的情境来考虑概念建构的解释力与生命力,只有这样才能根本摆脱古今之争与中西之争的问题。
其三是价值规范条件问题。概念建构并不能坚持价值中立的实证社会科学原则,而是反过来,要充分考虑价值预设在概念建构过程中发挥的前置性作用。这是因为,一方面,任何研究主体都不得不浸淫于特定的文化结构与价值立场,无意识地持有特定的道德基础、价值观念与世界观等形而上学设定,这形成经验实在论意义上的“前提假设”1。当然,研究者有可能在主观上摆脱结构主义的观念“共享”,发挥个体的能动作用,根据自我设置的价值偏好来确立“视角主义”的研究立场2。但这种个性化的多元立场并不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范畴,所建构的概念在传播与消费过程中又可能遭到结构主义者的抛弃或转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清概念建构的三个基本限制性条件及其之间的关系。任何经验性的概念建构都要经过“抽象阶梯”的提炼过程,并都必然直接受制于时空情境性条件,进而只有经过更根本的价值规范条件才能发挥作用。
如果运用这三个基本的限制性条件来把握中国社会科学概念建构的体系化问题,可以更深刻理解徐勇教授提出的“祖赋人权”概念3。“祖赋人权”相对于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发明的“天赋人权”概念而言,是基于中国农村社会调查以及对中国血缘关系的行为合理性观察而提炼的,对中国传统与现代的社会实践活动有很强的解释力。然而,从“抽象阶梯”意义上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普世概念,与西方的“天赋人权”概念没有可通则性,甚至可以进一步佐证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以文化体系的绝对隔阂为前提预设的。因此,“祖赋人权”也可以直接代替“天赋人权”,因为天、赋、人、权四个中文语词所指代的意义都不同于西方情境。中西之间存在两个根本不同的“抽象阶梯”,各自只能在不同文明体系内的“阶梯”来提炼与抽象,其尽头就是语言文化体系的边界。显然,“祖赋人权”可以突破古今之变,但难逃中西之争。诚如王国维所言:“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4作为规范性条件的“道”经过东西文明之间不可通约性的情境化处理之后,社会科学概念建构及其体系化过程必然难以跳出价值立场的争论窠臼。
三、概念建构的体系化
即使概念建构有着三个基本的限制性条件,依然可以实现体系化建构。体系化的概念建构是任何学者以及思想家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理解、解释、预测时代发展的一种理论策略。这并不取决于单一概念本身,而是需要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让概念之间构成逻辑上的联系,类似于在满天星斗中通过联想,找到北斗七星之间的想象性关联。无论是联想还是事实,都需要发展出一个基础性、统领性或标识性的元概念,由此确立“辐射型”和“家族相似性”的概念体系。因此,从具体概念到元概念再到概念体系的系列建构,需要分学术与非学术两方面来理解。
其中,从学术方面而言,统领性或标识性的元概念建构是完全可能的。在实践中,得益于学者群体与学术共同体长期共同的努力,建构出了相对独立的学派或范式流派。这主要分为四种情况。第一种是从理念规范到经验实践。像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一样,在早年激情燃烧的岁月,完全是在书斋里建立其关于国家治理的“理想国”概念体系,围绕“正义”的元概念,从纯规范层次衍生出很多政治哲学与伦理概念。但在后来,随着雅典城邦的衰败与危机,这个概念体系在经验中不断被修正,才发展出后来实践性更强的《政治家》与《法律篇》及其相关具体概念。
第二种是从具象到总体。马克思的研究与实践工作是批判资本家并抵制资本主义私有制,但从早年到晚年有一个发展过程。早年的博士论文《赫拉克利特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比较》从对德国现存制度的批判、对无产者的同情,发展到对英国与法国工人运动的支持。后来,马克思逐渐认识到,无产者对有产者的斗争贯穿整个人类历史过程,并充分肯定了工人阶级的“历史火车头”作用。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创造了很多概念,但最后都诉诸阶级概念,以此作为元概念来统领实践范畴的所有其他概念,成就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体系与理论体系。
第三种是从总体到具体。沃勒斯坦在1960年代提出“世界体系”的元概念与分析范式,把世界视为由“中心—半边缘—边缘”构成的一个总体结构,并通过《现代世界体系》三卷本来展示其发展变迁与运行机制。在此后半个世纪,沃勒斯坦不断发展这个元概念,以此作为分析范式来讨论高度资本主义化的现代世界。资本主义世界后来半个世纪的发展实践恰恰不断验证着世界体系范式的合理性,从而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认可。2012年,笔者去耶鲁大学对他进行专题采访,问他这辈子最自豪的事情是什么,他很平静地回答:“到晚年还在坚持年轻时的观点,当今世界的发展似乎在不断印证我早年的判断。”
第四种是一辈子从事具体研究,一切都交给后世人去总结与提炼,而后世人创制一个总体性概念,或者运用某一个标志性概念,对其一生的所有思想进行系统化与理论化总结。比如卢梭的公意概念、康德的物自体概念、孔德的实证概念、尼采的超人概念、罗尔斯的正义概念,等等。
从非学术方面而言,概念建构需要依赖于外部力量。即经由权力体系与意识形态体系相结合的权威性力量推行,形成在形式上连贯的概念体系与话语体系,同时使研究者成为概念关联、逻辑扩展及其体系化的阐释者与传播者。这些概念可能是研究者根据具体社会现象和问题而提炼的,可能是应意识形态的合法化论证而创造的,还可能是二者语义转换而构建出来的,但都可能围绕合法化论证而建构出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概念集群。至于具体概念是否能参与到集群化表达的概念群,关键在于非学术力量的需要选择。这就像散落一地的珍珠要变成珍珠项链需要丝线一样。有了丝线,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五颜六色的珠子串起来,成为色彩斑斓的项链。所以,“概念孤儿”的体系化,关键在于找到串联概念的“丝线”,而不是靠某一颗“珍珠”来发挥主导作用。
这意味着,体系化的概念建构可能没有所谓的总体性概念,也可以不需要所谓的元概念,只需要一种富有穿透力的外部力量。这种力量来自既定的、强大的文化体系、权力体系与意识形态体系,可以为孤立的“概念孤儿”找到“家”1。这个“家”可以是亲生父母建构的原生家庭,还可以是抱养过来的新家,甚至可以不找共同的父母,而找有“家族相似性”的兄弟姐妹。进而言之,不同的概念具有不同的作用,但在体系化的概念建构中要各守其位、各得其所。
四、概念建构的通则性
概念建构的体系化问题关系到过去与未来两个维度。从面向未来的角度来看,概念是知识大厦的基石,而体系化建构中国社会科学概念,旨在立足中国传统文明与当下社会,奠定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坚实基础。历史地看,体系化建构是针对过去百余年来中国社会科学或对外依赖或“向敌人学习”的状况作出的反思与回应。然而,尽管概念建构的体系化可以摆脱“西方中心论”,达到“回归中国”的目标,但也可能陷入“中国文化本体论”2或“华夏中心论”3的“学术民族主义”4的窠臼。这不应该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终极目标。而避免体系化可能陷入的窠臼,需要引入概念建构的通则性。
顾名思义,概念建构的通则性意味着社会科学概念能够跨地区、跨文化与跨社会体系传播,可以穿透民族、宗教、文化与文明体系的壁垒,普遍适用于当今世界,成为世界范围内同类社会政治与文化现象的有效解释工具,或者是为人类指向更好未来的规范价值符号,成为有助于沟通并推进人类和平、稳定、发展的桥梁纽带。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的概念建构要“超越中国”,从中国场域的问题意识出发,可以“低头”耕耘,提炼中国本土的经验材料,但需要“抬头”评价,从世界范围与人类文明的整体来检验概念建构的有效性。二者的结合可以突破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时空限制,走出“中国特色论”的单一目标与结论,把中国与世界紧紧关联起来,为当下与未来的世界及人类文明贡献适用广泛的概念体系、话语体系与理论体系。概念建构指向“超越中国”的宏大目标,中国社会科学把基于本土经验而建构的概念推向世界,并影响世界格局的发展方向与人类未来的道路选择,才是最大程度地“为了中国”。
实现中国社会科学概念建构的通则性,大致有如下三条基本路径。其一是区分实质性与形式性概念。前者是明确承载伦理价值选择与文化偏好的规范概念,如民主、自由、正义等,适用于特定文化和社会的情境条件;后者是议题的普遍性与价值中立性,突出研究环节的程序性、研究过程的合理性与研究资料的可共享性,比如阶层、内卷化、社会化、统计测量、定量、定性等,是跨文化的普遍分析工具。然而,实质性概念并不是不能跨文化传播,而是需要参与到世界的普遍议题中,从中寻找特殊现象的合理性,并用彼此能沟通的材料数据和普遍适用的形式性概念工具,给出彼此都能理解的普遍性解释。费孝通在这方面最为典型。《乡土中国》参与了同时代西方学术界热议的“乡土社会”(folk society)普遍议题,在方法上发展了雷德菲尔德(William Redfield)的典型建构与类型比较分析,在内容上“以中国事实”来关注中国乡土社会与世界的共通性与差异性,由此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独特性1。这为中国社会科学概念建构的通则性提供了典范与基础。
其二是美美与共。中华文明传统以“中庸之道”“家国天下”“和为贵”为基本理念,不同于西方文明传统的张扬个性、排斥异己与敌我意识。这充分反映在费孝通的研究理念,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2之中。这一理念相对弱化了政治体、文化体与文明体之间的冲突色彩,强调从西方传统的主体性转向主体间性。因此,出于种种现实考量,中国社会科学的概念建构并不是要重走西方道路,即通过打击和贬低其他文明与社会发展的历史遗产来抬高自己。这是不厚道的,也是自卑的表现。相反,更优的选择是,在欣赏既定人类文明进程的基础上,肯定文明互鉴,推出带有自我特色的概念,在世界社会科学知识舞台上美美与共,传播中国式概念,参与知识竞争,让知识产品与商品一样,在自由贸易的国际市场上交给世界人民去选择,在未来的时间长河中去检验。
其三是参与全球的公共事务与公共话题,奉献中国智慧与经验。实现中国社会科学概念建构的通则性,要求研究者不只是关注中国社会内部的具体现象与议题,而是要着眼于全球变迁与人类文明进程,把中国的具体问题链接到人类社会面临的宏大问题与人类历史遭遇的元问题,打通中国与世界的观念壁垒,并且关注世界同时代人的共同焦虑与公共问题。在此基础上,推动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视界转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在理念、制度与实践,既把中国作为主体与对象,又作为场域与视角,以概念供给为载体形式,提供解决人类共同难题的智慧与经验。由此,中国社会科学概念不仅承载了中华文明的价值规范,还传承了中国人民高超的智慧与经验,在展示中国特色的同时,突破了中国的地方性藩篱,进而“超越中国”走向世界。
总之,中国社会科学的概念建构是一个漫长的动态进程与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学术与非学术的诸多力量共同完成。尽管所有概念建构都不同程度上受到“抽象阶梯”、时空情境性条件与价值规范性条件的制约,但中国社会科学的概念建构需要在体系化与通则性两方面同时推进,不可偏废。体系化要求把中国社会作为研究对象、行动主体、方法与视角,摆脱过去的依赖性,强化自主性,但可能陷入“中国中心论”陷阱而与世界脱钩;通则性在于克服体系化的负面后果,既强调中国与世界的同一进程及不可分割性,又要求中国社会科学具有世界眼光与为人类作贡献的态度。概念建构以“超越中国”为途径和目标,方能超越长期以来的诸多争论,也才能更好地“为了中国”。
作者简介:郭台辉,云南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化实践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22&ZD193)。
责任编辑 申 华
技术编辑 王文浩
1参见Kristn Luker, Salsa Dancing into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192.
2参见Randall Collins, “Why the Social Sciences Wont Become High-Consensus, Rapid-Discovery Science,” Sociological Forum, vol. 9, no. 2, 1994, pp.155-177.
1参见沃尔特·布赖斯·加利:《本质上争议的概念》,高奇琦、景跃进主编:《比较政治中的概念问题》,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201—206页。
2参见Giovanni Sartori, “Concept Mis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4, no. 4, 1970, pp. 1033-1053.
3参见David Collier, James E. Mahon Jr, “Conceptual ‘Stretching’ Revisited: Adapting Categories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7, no. 4, 1993, pp. 845-855.
1参见F.H. Bradley, The Presuppositions of Critical History, Canada: J.M. Dent &Sons, 1968, p.99.
2参见W.H. Walsh, 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of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4, p.107.
3参见徐勇:《祖赋人权:源于血缘理性的本体建构原则》,《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4参见王国维:《论政学疏稿》,《王国维全集》第14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12页。
1参见徐勇:《将概念带入学术体系:为“概念孤儿”寻家》,《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2年第4期。
2参见冯天瑜:《“冲击-反应论”与“中国文化本位论”:两种转型说的长短得失》,《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管窥》,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61页。
3参见张岱年:《中国文化的光明前途》,《张岱年全集》第7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42页。
4参见Chen, H. F.,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Historicizing the Indigenization Discourse in Chinese Sociology,”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vol. 34, no. 1, 2021, pp. 103-119.
1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97页。
2参见费孝通著,麻国庆编:《美好社会与美美与共:费孝通对现时代的思考》,北京: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9年,第301—3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