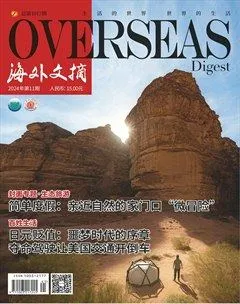厌食症:我曾坠入深渊

| 起因 |
那是一个温暖的春日。毫无预兆地,我像着魔一样,内心住进了一个陌生人。一句平常的话,一个微小的念头,世界从此天翻地覆。
时值1992年5月,我刚过完14岁生日。那天,体育课结束后,我挨着莉兹·鲍登,和班上的同学一起围坐在伦敦西区的校园里。莉兹是全校最瘦的女孩,我则经常被称为“美国小姐”。我打量着自己宽松校服裙中露出的双腿。原本我觉得它们足够修长,但在莉兹的对比下,它们显得像树干般粗壮。我以前从未意识到莉兹的身材如此纤细。我问她:“你这么瘦,好买衣服吗?”此话一出,我的内心掠过一丝忧愁:如果我也能瘦到连合身的衣服都买不到,那会是怎样的感觉呢?
“不好买,”她回答,“真希望像你一样正常。”
“正常”——我反复咀嚼这个词。“正常”,不是“苗条”,不是“骨感”,只是“正常”。我再次低头看向自己的双腿。它们怎么会如此粗壮,而且不直,难看得要命。午饭时吃的士力架顿时令我反胃。说起来,我的校服裙似乎也变紧了?妈妈说过,我可以安心吃任何东西,绝不会影响身材。现在看来,妈妈骗了我。

医生将这种时刻称为“发作诱因”,即触发厌食症的开关。对我而言,这个诱因便是别人口中的“正常”。没过多久,我就将大多数食物从食谱中淘汰,继而完全禁食。我为自己构建了一整套规则,像虔诚的信徒一样小心翼翼地遵守。短短一个月,我从一个踏着滑板、哼着小曲、性格开朗、总爱和父母分享一切的14岁姑娘,变成了对世界充满愤怒、任谁都无法接近的古怪青少年。每晚,我赤身裸体站在浴室的镜子前,瞪大眼睛观察镜中的自己。
最初,我只关心自己的小肚子,因为那是最能代表肥胖的部位。但很快我发现,身体上还有许多地方会显胖。我开始疯狂地锻炼下颌线,以防未来出现双下巴。我报名参加健身房的臀腹部训练课程,是班上最年轻的学员,比其他人小至少30岁。
身为女性,似乎注定要与自己的身体展开无休止的斗争。早早开始锻炼,提前消除可能出现的赘肉、小肚子和双下巴,便能在这场战斗中抢占先机。不仅如此,我还萌生出一连串奇奇怪怪的念头:舔嘴唇会不会增加卡路里?经过超市会吗?我多次徘徊在森宝利超市门口进行试验。我质问自己:为什么没能早一点意识到,变瘦才是人生的唯一目标?
那年8月,我凭一己之力毁掉了全家人的南法之旅。妈妈整日躲在酒店房间里流泪,我则在自己的房间里疯狂地做仰卧起坐。回看那时的照片,我虽然还算不上皮包骨头,但颧骨已经明显突出,笑起来眼窝深陷,有点像骷髅。
暑假结束重返校园时,我已经减掉了超过1/3的体重。尽管终日疲惫不堪、浑身乏力,我依然坚持在卧室做跳跃运动,家里的地基都快被我震碎了。仰卧起坐更为痛苦。因为太瘦,我的脊柱突出,每次接触地板时都容易破皮流血。然而,这些痛苦都无法动摇我继续减肥的决心。
 71OxVHJN6UQS5TZQKyOeGc5XgtVLH+NQmIk290hrvLc=
71OxVHJN6UQS5TZQKyOeGc5XgtVLH+NQmIk290hrvLc=在学校,我从朋友成群渐渐变成了孤家寡人。我的头发开始一簇簇地脱落,甚至被街上的路人误认为得了癌症。头皮裸露的同时,我的手臂、腹部和背部却长出了柔软的细毛。我会收集报纸副刊上的食谱,藏在被窝里兴奋地阅读。夜深人静时,我会从冰箱里取出冰淇淋和奶酪,用力吸入它们的气味。
妈妈时常泪流满面地感慨,“那个哼着小曲到处跑的小姑娘去哪里了?”我冷冰冰地回答:“她死了。”我讨厌看到父母心烦意乱的样子,每次吃饭都要和他们大吵一架。尽管内心充满内疚,我却无能为力。他们怎么就不明白,饥饿的感觉令我上瘾,我对此别无选择?
| 医院 |
1992年9月,14岁的我第一次住进精神病院。在那里,我唯一需要关心的是当天哪位护士值班——护士每天都会亲自检查,确保我没有使用泻药。我渐渐适应了这种生活:没有任何选择和责任,彻底丧失了对生活的控制权。一切都由不得我,因此无论发生什么都不会是我的错。虽然按时进食令我痛苦,但内心深处,我多少感到了一丝解脱。

十周后,我的体重达到了出院的标准,但我清楚,自己的病情更加严重了。之前的减肥也许只是出于无知和盲从,而在年底离开第一家医院时,我已彻底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并决心坚持下去。我重新开始锻炼,强度远超从前。我比以前更疯狂地关注卡路里。我学会了如何在测体重时作弊:将镇纸藏入内衣,或是提前猛灌一大桶水。厌食症比以往更为猛烈地操控了我。
1993年10月底,我突然在离家不远的街道上昏厥,此后几乎每周都会经历半昏迷状态。家庭医生凯伊越来越担心我会心力衰竭,他甚至请母亲作好失去我的心理准备。不久后,凯伊将我送进第二家医院——一家能够持续监测病人心脏和血压指标的私立综合医院。我在那里住了两周,于12月转入伦敦一家公立医院的进食障碍病房。等待我的是无止境的黑暗。
这家公立医院坐落在伦敦东南部一片嘈杂的街区,进入医院大门必须先穿过汹涌的车流。医院内部也毫无安宁可言,到处是病人的尖叫和医护人员的叹息。一位名叫艾玛的护士将我和其他女孩安排在同一间“宿舍”——一个塞了12张床位的长方形房间。虽然床铺上挂着帘子,但除非换衣服,否则这些帘子绝不可以放下,因为病人可能会躲在帘子后面运动、催吐或自残。宿舍中央摆着一张长桌,我们必须在这里吃完一日三餐和点心餐。
在这里,每个人都想成为全天下最瘦的女孩。第一天下午,我正吃着分配给我的零食,突然发现其他女孩都将饼干压成了碎渣,要么一粒一粒数着吃,要么将碎渣吹到地上。还有人咬几口就吐到纸巾里再偷偷丢掉。所有人都在比谁吃得更慢。卡罗琳、塔拉和诺拉是其中的领头人,其他人则紧紧追随她们的脚步。她们将食物藏在袖子里、口袋里、桌底,或者直接踢到别人的椅子下,让别人受责罚。黄油被抹到桌底,蛋黄酱被涂到墙上,饼干渣和面包碎被弹到地板上——这就是我们每天所处的环境。

对此,护士们无能为力,有些甚至会火上浇油。一位名为特莎的护士就是我们的噩梦。她从不与我们沟通,一开口便是大吼大叫。碰到不吃东西的女孩,她会用粗壮的手臂钳住对方,强迫她们咽下食物。听起来像电影里的大反派,但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
塔拉、诺拉和卡罗琳也绝非善类。塔拉当时27岁,但骨瘦嶙峋,活像个87岁的老人。她热衷于打探别人的体重,经常偷偷溜进护士办公室查看数据,发现有人体重增加就兴奋不已。26岁的诺拉长得有点像辣妹合唱团里的“高贵辣妹”,我能想象她上学时的样子:觉得自己最酷,喜欢排挤别人——反正在病房里她就是这幅模样。
31岁的卡罗琳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但没有人比她更擅长撒谎和欺骗。对她来说,隐藏食物是一门艺术。相比将苹果派藏进衣袖,她更喜欢看准时机将食物弹进别人的餐盘,然后幸灾乐祸地观赏对方在护士的逼迫下,不情愿地吃掉那些不属于她们的食物。
为了合群,我也开始花两个钟头吃一块饼干,将所有入口的食物“科学解剖”。我尽可能地将例汤、冰淇淋和其他食物残渣附在餐具边缘,将黄油从吐司中分离,最大限度地减少摄入的卡路里。我心甘情愿地沉浸在这种疯狂之中,对自己的新状态沾沾自喜。
| 转机 |
1994年1月,我被转移至第四家医院,在那里遇到了人生中第一位真正理解我的治疗师。从那时起的四年里,我每周都会见她两次。1994年8月,我的精神世界迎来了重大变革。
当时,卡罗琳也被转到了这家医院。一天早上,她歇斯底里般地大喊大叫,对护士和桌椅拳打脚踢,任谁都无法劝阻。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她认定自己吐司上的黄油比别人多。当时她已经32岁。一个无法抑制的念头突然跃入我的脑海,就像两年半以前被“正常”一词刺激了一样:我不想在32岁时还要为一片面包发脾气,这不应该是我的人生。那一瞬间,一些东西开始改变。

治疗师一直鼓励我在医院坚持学习,学校也设法从考试委员会那里得到特批,允许我在医院参加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我十分开心,因为参加考试意味着可以少吃一顿点心餐。相比必须吃下的苹果派,考得如何我并不在意。不过,打电话去学校查成绩的那一刻,我忘掉了苹果派。两年来,我再次开始关心学习了。
虽然身体欠佳,但我还是考上了大学。1996年10月入学时,我并未完全康复,依旧会躲在宿舍里靠着少量蔬菜度日。我鬼鬼祟祟、孤僻怪异,但幸运地遇到了几位心善的朋友。她们让我明白,过于担心别人的眼光是多么荒谬。尽管每天严格控制饮食,我的生活依然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向前迈进。
20多岁时,我在一家报社任职时尚记者。对于正努力克服厌食症的我来说,这种感觉颇为怪异,就像糖尿病患者在甜品厂工作一样。但厌食症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我的优势,我能够更为深刻地洞悉时尚界的精华与糟粕,明白“减肥通往幸福”的承诺不过是海市蜃楼。
| 康复 |
对我而言,厌食症和强迫症类似,都是内心焦虑的表现。我想通过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不快乐。14岁时,我的身体正迈入青春期,一切都陌生得令我手足无措。借助减肥,我试图让自己停留在瘦小的模样,那才是我的舒适区。
厌食症不仅仅是由于对食物的恐惧或回避。不过,要想摆脱厌食症,终究也得靠食物来完成:坚持健康饮食,直到不再为吃饭感到愧疚。对我来说,最终的胜利源自意想不到的收获——我生下了一对双胞胎男孩。那时我30多岁,遇到了心仪的男人。准确地说,他并未改变我,是我自己想要改变,而他出现得恰到好处。41岁时我又多了一个女儿,厌食症仿佛已经成为很遥远的事了。
我的结局听起来就像电影里的狗血剧情:“重病几十年,生个孩子就全好了!”其实,一切都是时机。我早已过了自欺欺人的阶段,不再相信厌食症会令我与众不同。我真心实意地想要摆脱厌食症,但自己的健康和生命不足以激励我,因为我并不在乎这些。关键时刻,是孩子们拯救了我。我终于找到了自己足够在乎的事。
编辑:要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