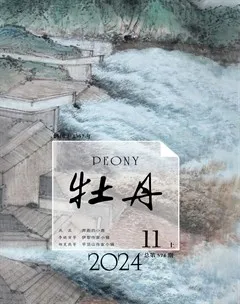小巷的伦理
我入住的酒店刚好处在苏州老城姑苏区观前街附近。每天辗转于园林庙堂、水村古建,回来得再晚、再累也要独自出来,去附近看望朴素而多情的小巷小弄,人间烟火,市井之臣。这是姑苏城的一张温柔的网,人如游鱼,在里面做幸福的寻梦。这些可爱的小巷是文化之城的另一个密码,是纵横交织的、庞大的城市根系,以诚恳、宁静的方式与时光达成了温暖的和解。
说她是文化之城是有根据的。
在一千多条长短不一的小巷里弄内,珍珠般散落着众多的寺院、博物馆、园林故园、小院人家等,长街灯火,春风门巷,柔和宽容的色彩,铺垫的是城市强健的骨骼与经络血脉,她的容颜清晰秀丽,背后是历史的积层和文化的断章。
那么对于苏州这座城市来说,谁缔造了她,初始的面貌是谁勾绘的呢?两千五百多年前,一个叫伍子胥的人站在姑苏这个地方,“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选中了太湖东岸丘陵与平原间的战略要地,将吴国新都定于此,筑起阖闾大城,为今日苏州城奠定了基础,可以说伍子胥应是古苏州城之父。人逐水而居,苏州城依水而建,内有南北向河流6条,东西向河流14条,当然也就有了与河流并行的大街小巷,前巷后河,交通便利,因此唐代诗人杜荀鹤写道:“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苏州人没有忘记这位大才之人,慷慨地“馈赠”给他一条巷弄,叫伍子胥弄。
苏州是水城,除去众多的河流外,还有小巷里亮汪汪的水井。清顾震涛编纂的《吴门表隐》里说,“平江路古名十泉里,有古井十口”,一条里弄就有十口井,整个苏州城的数量就非常可观了,清代前期就有两万口之多,即使现在也有一千多口在目在兹,日出日落,六百多口依旧反哺巷弄,像天上星星在地上的映照。仓街是明末一直到民国的贫民窟,里面有个“福寿泉”井,玉栏围挡,属于连体双口井,是一个叫朱鼎彝的外省商人为老母亲七十大寿出资开凿的,行善行义,方便附近民众吃水之需。我特意跑去看过,井台平整光洁,井口的石圈上凹槽累累,被岁月打磨得瓷器一样润泽。仓街136号门口也有一井,井圈上刻有“沈惺叔民国二十三年”字样。这个沈惺叔是当时苏州保大钱庄的老板,家住三茅观巷,老来得子,发愿行善,捐款在全城建十八口义井,皆部署在贫困巷里,仓街巷位列其中。井在温柔之乡静候,洗衣浣纱,浇桃灌李,孩子们青梅竹马,扶犁者牵牛而过,井见证了小巷深邃不浮的紧实生活。
井是深情的,又是自由的,为爱为义为恩,上善若水,苏州是个温润、甘甜之城。
一条条巷弄就是一条条时空隧道,妇孺童叟,五行八作,兴衰迭替,不同的小巷有其不一样的命运史。人们在深幽之处起居饮食、会友品茗、莳花弄草,在春兰秋菊前绘画习字、逗鸟下棋、抚琴作诗。在恬淡的背后,也有鸡毛蒜皮的烦扰,人生的彷徨与无奈。
以寺为巷名的也不在少数,最为著名是定慧寺巷,其波澜壮阔的历史可追溯到唐代,因巷内有定慧寺而得名定慧寺巷,最显著的特点是它两寺夹一院的布局。两寺指的是双塔寺与定慧寺,一院则是夹于两寺之间的清代贡院。双塔位于双塔寺院内,是苏州最具特色的两座砖塔建于宋雍熙年间,一座叫舍利塔,另一座叫功德塔,外貌长得几乎完全一样,间距仅二十米左右,相依相偎亲如孪生弟兄。巷的东面有吴王桥,至今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初闻以为与春秋时期的吴王有关,实则是吴王两族曾居住此地,真是开历史玩笑啊。巷的深处还有一个苏公弄,过去一看,果然是与苏轼有关:他与定慧寺住持守钦禅师交好,经常住在寺内参禅论佛,修心静志,慰藉旅途之苦。喜欢艺术的人不去吴作人艺术馆是说不通的,那里藏有吴作人先生、吴作人夫人萧淑芳女士以及吴氏家人的绘画、书法作品110件。其中包括吴作人三十年代创作的著名油画《缝》《青年》和《白色旋律》,50年代的油画代表作《过雪山》《孙中山和李大钊会见》以及70年代后创作的国画《牧牦图》《熊猫抱石》等精品力作,不来就意味着距离和隔阂。小小的后a6GekebqYVB9ENQoEf+1apNbW16EJwRDXvQJR1sRsg4=花园水池里倒映着隔壁的双塔,恍惚间,仿佛让人看到了时间的流转与变迁,如同连接着我们的前世与今生。
有的小巷以历史事件为名,比如王废基巷。姑苏城的小巷里有许多逸闻趣事,讲述起来的时候当然有意思了,讲者来劲,听者入迷,对于这种形式,苏州人叫“讲张”,意思就是谈话聊天。为什么呢?元末,各路反元起义军割据一方,其中一支以张士诚为首领的起义军以苏州为中心建立了政权,对老百姓还算不错,兴修水利,免除赋税,大力发展工商农桑业,颇有作为,后兵败自尽而亡,老百姓对相继而来的重赋税等严厉政策心生不满,私底下念说张士诚的好处,朱元璋听说此事后勃然大怒,下令不许再讲张士诚,谁再讲张就格杀勿论,时间一长,“讲张”就成了聊天的同义语成为历史留给苏州方言里的活化石。我们还说张士诚吧,当年最厉害的时候他的办公室设在吴王宫,兵败前一把火烧了泄愤,留给世人一片废墟,王废基就成了这个小巷的名字。在张士诚最危急的关头,他手下的十位铁心壮士应召入伍,浴血沙场,壮烈战死,他们居住的巷子被称为“十郎巷”。从地名学角度来说,这些巷弄因此成为张士诚及其历史事件的纪念碑。
中华文化中鲜有以坟为地名的,但在西大营门之西,却有条叫唐寅坟的小巷,唐寅即明代大名鼎鼎的书画大家唐伯虎。此君仙逝后埋葬于此?非也。他晚年懊悔少时诗文,遂焚而葬之,竖一碑并戏题曰“唐六如之墓”,看来只是唐寅的“瘗文冢”,民间俗称“唐寅坟”,后来人们在此搭棚建房,居民逐渐增多,形成小巷,遂以“唐寅坟”名之。哦,此坟而非彼坟也,这是对自我的一种取舍,对“旧我”隆重的祭奠。
也有正气凛然的巷。石人弄与南宋名将岳飞有关。民间相传的“马前张保,马后王横”中的王横是岳飞的部下,以力大无穷和善使一根熟铜棍而闻名,在岳飞被害后,王横也遭到奸臣迫害,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忠臣形象,后人在殉难处建庙纪念,立一身披盔甲、手执圆棍的石像,人称“石老爷”,小巷也由此得名。庆云弄里的庆云亭的匾额是岳飞的手笔,纵横飘逸,气势磅礴。值得一提的是,庆云弄北面有一条文丞相弄,文天祥曾在此居住过。这是巷弄所蕴含的精神内涵,更是这座城市永不褪色的荣耀。
江南重学,英才辈出,苏州历史上就走出过50位状元,其中清同治年间的状元洪钧是状元中唯一的“外交官”,来自悬桥巷。他一路升迁,光绪九年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后任清廷驻俄德奥荷四国大臣。有关他最为出名的是与青楼女子赛金花的风流韵事,凭着天资聪慧,洪钧带着她一同出国赴任,学得一口流利的德语,在柏林社交圈颇为有名,为她赢得了“东方第一美人”的称誉。赛金花曾在八国联军入侵时书写过“国家是人人的国家,救国是人人的本务”,有复制品悬挂于现在的悬桥巷洪钧故里,虽水平不高,但作为一个从青楼里走出来的小脚女子,彰显出的是一颗蓬勃的爱国之心,怦然一动,实属不易与难得。
走街串巷,单看看巷弄的名字就足以让人心情愉悦:百花巷、斑竹巷、桑叶巷、海红坊等等,争奇斗艳,过目不忘;有以飞禽走兽命名的麒麟巷、金狮巷、乌鹊桥弄、碧凤坊、凤凰街等,简直成了动物的天下乐园,反映出人与动物自然和谐的人文思想;还有以行业为巷名的醋库巷、枣市街、皮市街、盐仓巷等等,蚯蚓般耕耘在城市的夹缝间,显得简单而明确。那时候各行业聚拢在一起,抱团取暖也好,相互竞争拆台也罢,总会是热闹非凡之地,宽厚殷实,商业气息浓郁,如按名索需,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巷名出典,花街巷 、柳巷源于“花情柳意”“寻花问柳”二组词句,取“花、柳”因而成了地名,镜花水柳,淡抹浓妆,有欢愉也有悲凄,反映出旧苏州社会的另一面。跌落红尘的女子,流转于呜咽的角落,浮萍不定,残喘安身,无以躲避,无以逃离,在最黑暗的地方绽放为花朵,是苦难里飘渡的无尽风月,最终成为城市苦难的记忆和残红。这里面有唐代歌舞艳绝天下的真娘,卖艺不卖身,赢得了人们的尊敬,惹得诗人刘禹锡、李商隐、白居易、李绅等都曾为之题咏,从人格上给予了褒赞。有明代琴棋书画诗绣无所不能的薛素素,尤工水墨兰竹,她的传世之作《兰竹松梅图》等画作亦被故宫珍藏。到了民国时期,花街柳巷成了苏州平常人家的聚居地,入住的住户中知识分子、官员的比例相对高于其他巷子,脂粉味彻底散尽,淡淡的书卷气息贯通首尾,馥郁满巷,直至今日仍余韵不散。
还有幽兰巷,旧名勾栏巷,指围栏搭棚,是百戏杂剧演出的场所、青楼林立之地,是官绅权势人物、文人墨客、市井商贾的放荡冶游之地,原因在于,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双重的困苦,主导着这些烟花女子的命运。后来,该巷被改名为幽兰巷,寓意高雅圣洁,蜕变为高知阶层的聚雅之处,成了民国时苏州一条有品位的巷子,至今保留着一些历史建筑和名人故居,如余志华旧居、万嵩源、郁烈旧居以及唐慎坊旧居等,白墙青瓦,高高的马头墙高过屋顶,飞翎于小巷上空。这些建筑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还为苏州的文化底蕴增彩添香,体现出从世俗到雅致的伦理变迁。
巷柳街花,纵有满腔的话,也不再赘述了。
苏州众多的、网状的小巷一定是有过滤功能的,是有伦理的,它见证社会风气的转变及纠偏,承载着人们观念的更新与进步,印证人类始终如一的趋光性。小巷的伦理通过时间的沉积与提取,留存下的文化是清新、端庄的,它所呈现的是对美好事物不懈的追寻与靠近。
这是苏州的小巷,进来与出去,皆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