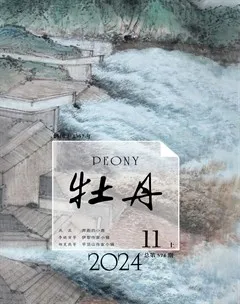诗意·苦难·温情
关注最普通的生命个体、彰显生命关怀是阿慧散文世界的重要主题。她对个体生命悲欢离合的关注、对生命不屈精神的书写,都表现出突出的生命关怀意识。她善于站在小人物的立场上,以独特的眼光去关注现实世界的诸多苦难,用温情的笔触去记录一个个在磨难中努力生活的劳动人民,去追寻在贫苦乡村里留下的童年回忆,以平和态度诗意描绘人的死亡。不论是纪实性文学作品《大地的云朵》,还是散文集《羊来羊去》《月光淋湿回家的路》,都展示着阿慧独有的诗意与忧伤、温情与苍凉。作品在揭示苦难的同时,还写出了温情脉脉的诗意生存,显示出真实可感的生命活力。
一、追忆贫苦生活中的童趣
阿慧刚出生时,父母都在不同学校教书。受到特殊纪律的影响,小孩无法进入校园,因此父母只好将她送到一户农家喂养。然而,当奶奶找到仅有八个月大的阿慧时,发现她独自在小屋里无助地啼哭,头上生满脓疮,“那疮红压压的流着脓水”。可想而知,她在农家并没有受到悉心的照顾。于是,心疼孙女的奶奶便决定带着她回到自己生活的乡村——沈丘县大于庄。在那个偏僻的村庄里,只有奶奶一人的工钱贴补家用,祖孙二人的生活并不富裕,甚至有时还会面临缺少饭食的威胁。尽管如此,作者并没有因为生活贫苦而产生消极情绪,反而从“飘荡着庄稼和庄稼汉”味道的田野中找到无限乐趣,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纯真美好的童年时光。童年的记忆对她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作者在写作时常认为自己“身上有股与生俱来的泥土味”,这味道来自豫东平原那片醇香和淳厚的土地,是她在创作时铭记于心的精神家园。这片腥热的土地,以及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民,连同自己儿时的回忆,都成为阿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作者用饱含温情的文字,“凝成一条温热的脐带,把那温热的乡情、亲情、人情、爱情,一圈圈深情地缠绕”。
在阿慧对童年记忆的回望中,常常掺杂着生活的苦难,但她始终选择将目光聚焦到对童真之情的书写上。这样,作品中的苦难便蒙上一层诗意的外衣。《羊来羊去》中提到了“我”和小伙伴四巧一起捡拾树叶的经历。在当时的乡村中,具有多种用途的树叶是每家每户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在村内的树叶已经归生产队所有的情况下,为了保障全家人一天的饭食供应,“我”与四巧不得不挎着大柳筐到别村地界捡拾树叶。作者对这一童年趣事的叙述实际上是伴随着苦难展开的。四巧因柳筐内树叶数量少而不肯回家,在她“惊恐无助的目光”中,“我”意识到她是害怕被继母打骂。从这一细节中可以猜测到,四巧难以得到继母的关爱,她的童年将充满着眼泪与疤痕。不过,作者没有详细讲述四巧的苦难经历,她写作的目的也不是要同情四巧的遭遇。所以,在故事的结尾,“我”决定把自己柳筐里大部分的树叶送给四巧。回家后,奶奶在了解完事情原委的情况下并未责怪“我”,而是用草帽作为代替树叶的焚烧原料煮熟了面条。阿慧没有让故事染上悲伤的底色,她在文章中传达的情绪往往是欢乐的、带有童真的。
而且,在阿慧幼年时,由于奶奶需要在生产队干活,为了方便看护阿慧,便将她带到了田地里。村里的人们日常生活都与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孩子们基本m+rJDWlwGrfMjhdh2puDYg==没有其他的娱乐活动,田野里的一切都可以成为他们的亲密伙伴。可是,看似枯燥无味的广阔田地,在阿慧笔下却被赋予了诸多趣味。她称自己是“乡村田埂上的一棵小草”,是“土生土长的泥娃子”。童年时期,田地是她最熟悉的娱乐场所。她写道:“土地上的孩子,喜欢在土地上劳动是与生俱来的。”不论是小时候玩蚱蜢、看蚂蚁搬家,还是长大后用镰刀割草、找寻野果,这些记忆在作者笔下都自然而然地带有一种泥土的气息。
与此同时,一些对阿慧来说十分新奇的事情也在她童年回忆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比如《羊来羊去》中写到,父母为奶奶和“我”在野外建造了新草房。尽管“我”与奶奶必须住到远离村子的西洼里,尽管新房周围土壤贫瘠、难以耕作,尽管夜里时常有黄鼠狼前来偷鸡,令“我”和奶奶难以安眠,但对那时的“我”来说,这座新房宛如宫殿一般富丽堂皇,“我”与奶奶就是“宫殿”中的两位“女国王”。阿慧描写童年生活的文字如同一股暖流从内心自然流淌出来,因此毫不生硬,尽显天然之感。通过对童年记忆的追寻,作者流露出对故乡深切的怀念,在豫东平原地域文化滋养下,这些带有泥土气息的记忆在朴实中显得熠熠生辉。
故乡的风土人情给予阿慧始终饱含深情进行创作的天分,而丰富的体验又赋予她感知、触摸世间之温暖的能力。她带着真挚的情感书写了许许多多发生于童年时期的温情故事,并以诗意的手法处理了故事中的种种苦难,这些都为作者自己及读者带来了无尽的暖意。阿慧的心灵世界是炽热的,因此,不管是她的创作态度、创作风格,还是她眼里的故乡、自然万物,都是有温度的。透过书中文字,我们能够看到作家阿慧在面对一切人和事时含着无限善意的眼光,和那柔软又充满力量的内心。中原大地养育了阿慧,也扩大了她的文学视野和写作视角。所以,她在创作中始终能够冷静地审视普通群众的生活百态,传达出她对这片土地上每一位底层人民的关怀,传递出她对苦难背后定有希望的期许与坚持。
二、歌颂逆境中的抗争
在阿慧作品中占据大量篇幅的,是以歌颂在逆境中顽强拼搏的普通人为主要内容的文章。不管是她身边的亲人、朋友,还是远赴新疆采摘棉花的河南人民,都是书中描写的主角之一。作者以生命视角去审视凡俗人生,以女性特有的温情对那些在逆境中依旧乐观坚强的人们进行了审美关照。作家坚持紧贴着社会现实、紧贴着劳动人民进行文学创作的理念,既真实地展现了普通人的平凡生活,又深度探索了他们富有力量的精神世界,挖掘了至善至真至纯的人性之美,表现了她的生命关怀和写作伦理。
在父亲的弟弟、哥哥接连意外离世之后,“我”的父母主动承担起照顾其七名幼子的责任,将他们视如己出。即使物资匮乏、日子清贫,甚至每天要早起做十四口人的饭菜,父母也从未放弃希望,未放弃责任,拼尽全力把全家十一个孩子抚养成人。这其中的辛苦难以言喻,而他们却毫无怨言。在经历女儿女婿生意破产的变故之后,年迈的父母放下特级教师的身份,心甘情愿捡拾废品挣钱,在逆境中依然以积极的心态面对人生。年仅十七岁便退学务农的莫多多,在父亲去世之后,主动承担起照顾母亲的重任。在新疆,她每天要进行十四个小时的超强度劳动。可莫多多都没有怨天尤人,反而颇有干劲,一心想要挣钱为母亲买金耳环、为姐姐们买新手机。还有“双孤女”闻免,出生后不久便父母双亡,但她无惧村民们排挤、歧视的目光,在批判和指责面前毫不畏惧,勇敢地反抗命运的安排。此外,在奶奶身上所体现的精神同样让作者肃然起敬。她年轻时丈夫意外病逝,自己含辛茹苦抚养五个孩子长大,晚年却又接连丧失两子,这让她备受打击。但是,奶奶依旧如往常一般坚强、坚韧,她用瘦弱的身躯“为寡媳和弱孙顽强地支撑起一片精神天地,她无形中也成了读者心中的精神之王”。
这些人在作品中并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他们的人生道路充满酸甜苦辣,但他们一直保持着对未来的希望,相信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的生活。这种在苦难中保持乐观心态、坚强抗击命运的精神,不仅是他们个人的价值追求,更是一种社会共识,激励着更多人为了梦想和幸福生活而努力奋斗。
阿慧关注社会底层普通民众的生存状况,写出了苦难生活中普通人生命的韧性。从她作品可以看到,作者讲述的故事中从不缺乏苦难,然而,她的作品却自始至终都未曾出现过令人窒息的绝望感,这在某种程度上源于作家洞悉了人们生命深处坚忍的承受力和不屈的抗争力。正因为她意识到了中国人文化品格深处的刚强坚韧,所以她对苦难的呈现仍向读者传递出了一种深刻而积极的人生哲学:人在不可避免的生存困境中仍需要有对生活的无限憧憬,并发挥主观能动性拯救自己于苦难中。这是她以人为本创作态度的体现。
三、淡化死亡中的伤痛
死亡是生命无法回避的命题,对待死亡的态度也反映了阿慧的生命观。她在作品中也对死亡进行了诗意的书写。在走过几十年人生风雨之后,她学会在崩溃中成长,在失去中接受,对生命和死亡也有了深刻的认识。在创作中,作家往往会将写作的重心放在追寻与逝者的种种回忆上,能够通过对诸如爱、生命等正面力量的强调从而冲淡死亡本应该具有的恐怖与惨烈,以这种方式为死亡注入诗意与美丽,这也透露出她面对死亡、面对人生的一种豁达、从容的态度。
在阿慧对死亡的书写中,她通常想要传达的是小人物在面对死亡时展示出的轻松的态度。九十六岁高龄的奶奶即使被医生判定时日不多,也依旧冷静平和地对待一切。不仅挨个唤起村民们的小名,与他们聊天,还在意识模糊时要求擦洗身体,希望带着洁净离去。文章中,作者没有大量渲染悲伤气氛,而是不断叙述与奶奶有关的回忆。既借奶奶之口提到她与村民之间发生的种种故事,还写了她与自己儿子、儿媳等人的一系列回忆。虽然斯人已逝,但与其相关的美好记忆会永远留在人们心中,这是他们来过这个世界的证据和意义。这样,作者以平和、淡然的笔调向读者展现人的最终归宿,冲淡了死亡给人带来的悲伤情绪。
关于死亡,作者还写到“我”的叔叔在二十九岁时因别人的捉弄而遭受电击,从而意外身亡的事情。这对全家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噩耗。但是,在极度的痛苦之外,阿慧还试图从心灵的疤痕中找寻一丝温情。她开始在记忆中回望与叔叔充满温情的往事:在八个月的“我”被奶奶抱回家后,叔叔虽然还是一个大小伙子,却笨拙地学习哺育经验,成为“我”的“乳娘”。作者在文章中别出心裁地将叔叔这一人物置于第二人称,直接拉近了与他的距离。她的文字中减弱了伤痛,文章结尾写道,“你的生命就这样在我们的眼睛里生长”。这样,通过存在形式的转化,生命在人们的想象中有了延续的可能。让人感觉到,似乎亲人并未远去,而是如清风一般,永远留存在与其有关的所有回忆中。
四、结语
生命关怀是阿慧作品中自始至终流淌的温泉。作者用她的作品展露灵动的气息、温情的气质和敏锐的才思,使读者参悟她对生命的尊重。正如作家自己所言,“用真情去触摸民众的根脉,用脚去丈量人心的长短,用文字去抵达灵魂的深处,用情怀彰显人格的智慧”。作家对个体生存意志的执着探寻,对生命存在价值的深度思考,对人生苦难的诗意书写,以及对社会责任、文学使命的自觉承担,共同成就了她的作品“哀而不伤”的艺术气质。
参考文献
[1]阿慧.一棵草的自然生长[N].文艺报,2015-06-03(6).
[2]阿慧.遵从自己内心的吩咐——我的创作谈[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7,(04).
附录:阿慧创作年表
一、获奖:
1. 2009年4月,散文《十一个孩娃一个妈》荣获首届全国“漂母杯”征文大赛二等奖,入选《2009中国散文年选》
2. 2010年8月,散文《羊来羊去》荣获第四届全国冰心散文奖(单篇奖)
3. 2014年9月,散文《羊来羊去》荣获首届《回族文学》奖
4. 2014年9月,散文《赤脚踏上金山岭》荣获首届全球华人中国长城散文“金砖奖”一等奖
5. 2014年9月,散文《临夏绿风》荣获首届“魅力临夏”二等奖
6. 2014年9月,散文《泥屋西边有口井》荣获第二届孙犁文学奖散文大赛优秀奖
7. 2015年2月,散文《散文树上开红花》荣获“中国散文三十年”散文大赛一等奖
8. 2016年8月,散文集《羊来羊去》荣获河南省第二届杜甫文学奖
9. 2017年12月,散文《大地的云朵》荣获《民族文学》年度奖
10. 2020年9月,散文《一口井的映像》入选《56个民族共话好家风》一书
11. 2020年10月,散文《一滴水的镜像》荣获全球新月文学奖一等奖
12. 2024年3月,散文《星梦满船》荣获全国“周兴嗣短篇作品推优活动”散文类一等奖
二、出版:
1.散文集《羊来羊去》,2012年5月(宁夏人民出版社)
2.阿拉伯文《羊来羊去》,2014年10月(宁夏人民出版社)
3.散文集《月光淋湿回家的路》,2017年11月(作家出版社)
4.长篇散文《大地的云朵——新疆棉田里的河南故事》,2020年10月(河南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时凤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