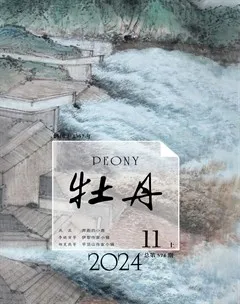悲情野杏林
离都拉塔口岸东北行,约5公里,低洼地带,有一片野杏林,宽百米许,绵延数公里,以集体的浩大的声势,逼迫白杨林在半里外暗自葳蕤,威慑庄稼田在几百米外悄然葱郁。据说这里曾是一道废弃的沟渠,不知哪年哪月哪位朋友,有意或是无意,将一枚杏核丢在这,来年受雪水和泥土的恩惠,破壳而出,长成一棵有抱负有追求的纤纤弱苗。小苗渐渐长大,结了杏子落在地上,成为第二批种子。“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野杏林借用愚公精神,使每棵树具有了不屈的风骨。
野杏林每年准时泛青,准时开花,准时结果,时令对它一点也不吝啬,一点也不因它无人认领而轻视或轻慢。相反,比起那些家杏,正因少了围墙的阻隔、房屋的遮拦、家畜的欺凌,它才更早地接受了春风的抚慰、春雨的爱怜、春阳的眷顾。它总比附近农户院中的家杏早三两日鼓苞、绽叶、吐蕊、结果,早三两日成为一棵“女人树”、一棵“母亲树”。当然,它也更早地领受了狂风的鞭笞、雷暴的击打、冰霜的侵蚀。在善与恶、爱与恨、情与仇的交加中,它自生自长,将根深深地扎在戈壁砾石的缝隙间,拼命吸吮少得可怜的营养。就像穷人家的野孩子,凉水也长肉、野菜也壮骨,半饥半饱顽强地长高长大。
与这些野杏树结识,已整整二十年了。那不是一次美丽邂逅,是慕名而来。从尼勒克县深山里的兵团连队,举家迁至伊犁河谷最西端的边境连队,一年只做两件事,种地、放牧,放牧、种地,活成一座“移动的木桩”。生活乏味得接近清水时,我的意志彻底输给生活。为了继续与生活为伍,我不得不骑上那辆不颠不响、一颠乱响的自行车,到野外给生活寻点“滋味”。
命定的相见,神仙挡不住。
桃三杏四梨五年,枣树当年能赚钱。据我多年的植树、养树、观树经验,我第一次到野杏林,驻足的第一棵野杏树,从枝干的“骨节”看,应该是首次结果的四龄树——大多数的树,每长一岁,新枝与老枝之间,能看出明显的痕迹。她的叶色微黄、叶脉细弱,叶片程度不同地卷曲,明显营养不良。“能在人下为人,不在树下为树”,她周围的杏树都比她强壮,她就成了强强之下的弱者。狂风一来,她东一头西一脚打醉拳,枝枝干干痛苦呻吟。多亏四周的杏树们手手相扶,她才勉强保持了一棵树的起码尊严。她的果瘦小稀疏、色泽黯淡,若不足月的胎儿,让人心生怜悯。我把树叶往小杏子们身上盖了盖,像一个母亲给孩子掖严被角。我向来惜弱怜贫,对这棵树格外上心,每次来看她,都把外侵的枝叶移掉,把她倾斜的身子扶正,让其堂堂正正做一棵树。
这些杏树因无人修剪而边幅不整,枝杈指天画地,随意披拂。正是这种随意,才显现出它的个性——自在、无羁、狂放、张扬、飘逸,它们是“活成自己的树”,是树王国的自由公民。那些修剪过的树,是按照人的意志生长的,是被奴役的树,纯粹的结果工具或观赏道具,彻头彻尾的“活给人看的树”;最可悲的是经过嫁接的树,已失去树的贞操,变成一棵“不洁”之树。恕我固执、愚顽,不管改良出的果子颜色多么诱人、外观多么光洁,我总认为是人工的使然,它们的躯体处处透着假。就拿杏子为例,几十年前的土著品种,名字土得掉渣,样貌俗得像同时代的村姑,随手拿起一颗尝尝,汁是山泉的甘、肉是田野的醇,杏核嚼碎了带着中草药的幽香。有谁舍得把果皮吐掉?那是肠胃钟情的物质,营养值上得了平民的排行榜。吃完几颗,香气在骨子里积了厚厚一层,留恋也积了厚厚一层。反观现在的杏子,把心思挖空,在取名和造势上抢夺人的思维阵地,中的、洋的,哪一种是中看又中吃的呢?化肥臃肿它们的身体,农药扮靓它们的脸蛋,冷库的防腐剂永葆它们青春靓丽。一颗杏子在手,左瞧瞧、右看看,造型和色彩无可挑剔,食欲完全被钓出来。咬一口,态度大变,滋味寡淡,不骂娘的,算是有修养之人。没有对比就没有高下。替果子说话的不是嘴巴,而是舌头。把良心放在日光下说,那时候,野杏子留给唇与齿的记忆,那是等同初吻的。
我眼前的野杏树,透过它的“野”,我找到了它的“真”,找到了已失踪多年的“纯情”。我热抚它的身、亲吻它的叶、吮吸它的果,缠缠绵绵到日薄西山。至此,每年总有那么几次或十几次,我骑上单车,带上“单反”,去约会我相思的“杏情人”。
我惊诧于野杏树的生存能力和生存智慧。由于无人施肥、浇水、管护,杏树只能绞尽脑汁自保。春天,为了不招惹风沙,枝杈尽力向树干靠拢,一棵树与一棵树保持距离,给风沙留一条出路,给自己留一条生路;夏天,为了抑制杂草与其争夺水肥,它们又把枝杈使劲向四周伸展,一棵树与一棵树臂相挽手相牵,使绿荫如盖,让杂草在无光的世界里绝望;秋天,为了留住树干与树枝的水分,杏叶自断生路,早早地枯萎、凋落,用生命的暗夜,换取杏树的前程;入冬,落叶与雪合谋,相互裹挟,紧紧捂在树根周围,与杏树结成生命共同体。雪融时,每片落叶都可劲吸足水,在光合作用下,一点点将自己腐烂,融进春泥,向树根输送生命的营养。
二十年来,差不多每棵树上的杏子我都尝过,至于味道,基本上大同小异,或酸或甜、微酸或微甜,让人过齿不忘的那种滋味基本没享受到。我知道,杏子的本真,就是生活的本真。循着一棵野杏树的脉络,我们是否可以回到那个纯情岁月?
野杏子的妙处不在“味”,而在“野”。至于“味”,只要有足够的钱,足不出户,想吃什么,拨一个电话,外卖小哥或小商贩不出半个时辰,准时敲响你的家门或按响门铃,甩开腮帮子风卷残云海吃海喝,或有滋有味细嚼慢咽,那就看你的个性和心情了;围着“野”展开延伸:一是田野,虽称作“野”,但“田”有名有姓有主人,“野”也就是个虚衔了。而田野里生产的物品,为了傍上环保这个大佬,追求效益最大化,无论粮食、蔬菜、果品,均标明“绿色产品”,违不违心?有没有化肥、农药的残留?只有生产者心知肚明。这个“野”有冒牌的嫌疑;二是野生物品,不姓赵钱孙李,也不姓周吴郑王,成长史远离人类视线的关注,是纯粹的“野”。这种植物的果实是原生态的,酸是本质的酸、甜是本真的甜,无所谓可不可口,吃的就是个真,品的就是个纯,回味的就是个地道。在这里,我形容一下吃第一颗野杏子时的真实感受:我伸手随便摘了一颗,在衣襟上做了简单的卫生处理,送进嘴里。当牙齿的咀嚼功能将杏子外皮刺破,舌头的味觉功能立即感到一股异样的酸的味道。它既不同于山楂柔和的酸,也不同于柠檬生猛的酸,更不同于蓝莓可人的酸。野杏子的酸,不是拒人以千里之外非一口吐掉不可的酸,也不是让人急不可待不吃不足以慰平生的酸,而是一种战略战术把握十分到位,欲进不能、欲退不可,不得不耐着性子仔细品味下去的酸。自从吃下这颗野杏子,我对平素颇不感兴趣的酸有了新的定位和定义——其实我还是挺喜欢酸的,只是从前没有找到合适的酸。
我给我的味蕾,找到了一个新的伙伴。
在对野杏林的倾慕者中,我并非独行客。团部子校有一化学老师,姓贾,板寸头,白净面皮,戴一螺纹很深的近视镜,样子很博学。贾老师酷爱写诗,洋洋洒洒一写就几百行,作品炫耀在多个“国”字号报刊。“贾诗人”的名声甩“贾老师”几条街。搞不懂,一个学化学教化学的,整日把元素周期表在脑子里碾过来轧过去,怎么就跟诗对上眼了呢?春夏时节,每逢周日,他都要来野杏林。来得多了,我们便免不了相遇。相遇得多了,便成了相识。相识得久了,便成了知己。贾老师说,他是来野杏林找灵感的,每当诗写得不畅或思路卡壳时,他就来此转转。摸一摸树干、理一理树枝、嗅一嗅树叶,回去的路上,思路就打开了,美妙的句子像开了闸门的河水,蹦跳着往外涌。他的组诗《野杏林情思》,被省级文学期刊头题刊出,好评如潮。他告诉我,他很快就要调到师文联,从事专业创作。贾老师说,是野杏林成就了他,是他事业上的“恩公”,他没有理由不倾心歌颂野杏林。要不就说人比人气死人呢,我来野杏林的次数比贾老师只多不少,别说诗,顺口溜都没吟出半句。但愿每个人的人生中,都有自己的一片“野杏林”。
较于野杏,人们对家杏的兴趣似乎要淡得多。也许家杏天天在视野中晃来晃去,已熟视无睹;也许家杏的风头被苹果、香梨、核桃抢走,变得可有可无;也许家杏始终业绩平平,压根就没引起重视。也许,家杏的悲哀就是离人类太近,就像睫毛,很容易被眼珠忽视。
我这么说,不是在故意贬低家杏抬高野杏。野杏与我非亲,家杏亦与我非敌。我之所以如此青睐野杏,实属野杏具备了碾轧家杏的一切软硬实力。我们周围几十公里范围内的家杏有黄金、金太阳、红0X6NOBsLrxcA7UMyFH5CRF8YPg/ufbEDIwi2AwFWfSQ=丰、红光等,名字透着富贵、红火,极具象征意义。还有一种“凯特”杏,名字洋气,据说是从大洋彼岸引进的,个大,小苹果似的,黄的臃肿、圆润,贵妇人皮肤般,吹弹可破,汁液随时都有破皮而出的可能,让人有种迫不及待大口吸吮的欲望。这种杏子我真的从河南老乡那里吃过,还不止一颗。就表面现象而言,它浓稠的汁,仿佛流动的水晶,诱惑得涎液夺唇欲出。撇开人情和感情,说真话,那些养眼的家杏,其味道,实在引不起我味蕾的丝毫兴趣。
我不是一个容易移情别恋的人,对于那片野4xaTW5awdpta10twCWWOOXsqSJ3kB4rkPQN/DMGqLOk=杏林,我情有独钟,我们的交情已深入骨髓和灵魂。我每有排解不开的忧虑,都到野杏林去倾诉。那些大智若愚的树叶,那些讳莫如深的杏子,摇着脑袋点着头,打着哑语的手势,深入浅出地把人生奥秘和盘托出。我大彻大悟,心满意足地骑车而返。
你千万别以为我是张开大嘴任西东。不就是一片野杏林吗?绿绿眼睛、宽宽心情还可以,还真能使人拨开云雾见青天?如果你心存这样的疑虑,说明你还没有全身心地融入过大自然,没有放下“万物灵长”的架子,与一棵树交心、与一棵草交融、与一株庄稼心心相印。你的那些所谓的春游、踏青、野餐、夏令营、农家乐,纯粹是自欺欺人的作秀,借机挥霍一点时间与金钱而已。鲁班借助一根带刺的草叶成为木匠的鼻祖,一只坠地的苹果砸出牛顿的“万有引力”。谁又敢保证,一颗野杏子的将来,不会成就一位“潜力股”的大师。大自然予人的智慧,在课堂和书本、师傅与导师间,已经弯道超车。
那年杏子熟透时节,我在野杏林遇见了一个小女孩和她的妈妈。小女孩六七岁的样子,脸庞圆润,让我想起一颗熟透的杏子;眼睛灵巧,使我联想到温润的杏核。她双手举着一个精致的塑料篮子,妈妈将树上的杏子挑选着装入篮中,全是向阳的美观的大个杏子。此时已有大半篮。对于我的突然出现,小女孩显然愣怔了一下,见我面容和善说话委婉,很快便镇定下来。三五句闲话过后,我们便攀谈起来。妈妈说,小女孩有一个比她大8岁的哥哥,三岁时得了自闭症,辗转了许多大医院也无好转。小女孩很爱哥哥,也愿意和哥哥一块玩。她发现哥哥对杏核特别感兴趣,不仅将几十枚杏核在手里把玩得个个锃明瓦亮,还能奇迹般将杏核扁放,一枚枚摞起来,摞得一筷子多高也不倒。小女孩很是惊讶,试着自己摞杏核,可不管怎样努力,运用怎样的技巧,竟摞不到半根筷子高。小女孩天方夜谭地对妈妈说,是上天派杏核来拯救哥哥的。她是多么盼望哥哥好起来,做一个正常的哥哥。她便缠着妈妈来野杏林摘杏子,回家掏出杏核,放许多枚在哥哥面前,锻炼哥哥的智力。看哥哥摞了一串又一串,像竖起的佛珠。小女孩坚信杏核里藏着“神迹”。
我同样坚信野杏林里面藏着神迹,若不,为什么这里有偌大一片杏林,而不是苹果林、核桃林,或者其他什么林。上天把野杏林安置在这,定有他的用意和暗示。贾诗人和小女孩,不就是神迹的践行者吗?自然界中,山岳有山岳的位置,江河有江河的位置,一颗石一粒沙各就其位,都充斥着造化的良苦用心。只是我们的部分大脑尚处在待开发状态,解不透其中奥秘。
我将杏子摘回来,满满的一桶,洗净、晾干。等到绵软,搁入铝盆。去核,果肉揉碎,至糊状。拌入白糖,置于玻璃瓶,旋紧瓶盖。上屉蒸熟,放进冰箱。冬日取出,火墙或暖气片上徐徐焐热。启开,一汤勺一汤勺送进口中,冰冷的季节,心里立马溢出野杏林的温馨。晒干的杏核,砸烂,取出杏仁,坩埚焙至微黄,轧碎,每日三至五羹勺,止咳、润肺、平喘、化痰。或者,将杏核一一平躺,钻细孔,细红绳穿过,小串套入手腕,大串套入脖颈,走起来窸窣作响,很庄重,很个性,很有做派,一副禅学大师的模样。
野杏林给我带来的最大收获,不是物质,而是精神层面的。它的自立自强,是我的榜样;它的甘于清贫,是我的榜样;它的随遇而安,是我的榜样;它始终如一的坚守,更是我的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每到野杏林一次,心灵的包袱就卸下一次,人生的感悟就增多一次。大自然的智慧不像人类,睫毛一闪一个、灵机一动一个,它隐匿得很深,不是交心莫逆的朋友,不会轻易赐予的。
做梦也没想到,我和野杏林的情缘就这样结束了,而且是以悲剧形式结束的。
那个和平常并无二致的早晨,阳光的明亮一点也不打折,空气的清新一点也不马虎。我再见野杏林的心情一如既往地急迫。
这是我的野杏林吗?我的野杏林怎么啦?今天,它为什么会以这种悲情的姿态与我相见?难道它不知道,眼前的它,会让我的心裂口、流血、结痂吗?
我的野杏林横七竖八躺在地上,有的断头折颈,有的皮开肉绽,有的骨断筋连。它们的根一律被拔了出来,硬生生地被拔了出来。白生生的断骨露于野,伤口惨烈、恐怖、扎心,使我的血冷凝,使我的思想苍白,使我的灵魂瞬间被掠空,使我的身体骤然深陷于无底的广寒宫。
明显有挖掘机造孽的痕迹。
无论个人行为,还是集体行为,造孽是最可恨的。
由此,我恨死了挖掘机,恨死了轰鸣的马达、沸腾的柴油,恨死了所有的铁和尖锐。恨死了握操纵杆的手。
后来听说,这片野杏林的牺牲,是为了扩大农田多打粮食。
我的恨扩充了范围。我恨死了嘴、牙齿、肠胃。恨死了由粮食支撑的皮肉、血液、骨头。恨死了欲望、贪婪、武断、专横。恨死了一只无形的大手,成为毁灭的道具。
我恨为了苟活,还要继续糟蹋粮食的我自己。我恨我可以恨、恨得有理有据的一切。
如若可能,我愿求造物主帮助,一根根将我的肋骨抽出,再插一片野杏林。
本栏目责任编辑 李知展
王东江,新疆作协会员。作品见于《文艺报》《中国艺术报》《北京文学》《星星》《散文百家》《伊犁河》等刊。鲁迅文学院第32届高研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