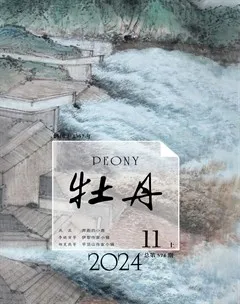目不识丁
李丽娟,山东聊城人。出版小说集《新城市人》,作品见于《安徽文学》《骏马》《中国文化报》等报刊。
1
这是母亲第一次出门远行。
落日余晖洒落大地,母亲弓着腰清扫院子,阵阵晚风袭来,树叶哗哗作响。几片梧桐叶子随风飘落到母亲脚下,母亲静静地凝望着这几片干枯的树叶,仿佛看到了自己的一生。她蹙了下眉,弯腰继续清扫。
母亲在村里生活了将近六十年,她与村庄相依为命,从未想过离开村子半步,巴掌大的村庄是她生命的半径。村庄的一草一木早已深深融入母亲的骨子深处。
她扫完地,正准备进屋,忽然裤兜里的手机急促地响了起来,打破了眼前的寂静。
电话那边,弟弟满怀欣喜地告诉母亲茜即将临产的消息。母亲接电话的手微抖着,紧皱的眉舒展开来,仿若一块小石头砸在心湖上,荡起一圈又一圈涟漪。
弟弟很希望母亲能提前过去帮忙带娃,茜的父母还没有退休。弟弟在河北一省属单位工作,在单位领导的介绍下认识了弟妹茜,半年后,俩人结婚,定居在了唐山。茜是家里的独生女,自小娇生惯养,家务活一项也不会干,生活的担子像小山一样压在弟弟的肩头。
放下电话,母亲喜忧交织,她来回在屋子里踱步,喜的是家里添丁了,忧的是:自己没文化,一字不识,没坐过火车,连汽车也很少坐,怎么过去带孩子?
母亲生于20世纪60年代一个贫苦家庭,母亲排行老大,下面还有弟弟妹妹六个。在那个肚皮都填不饱的年代,哪有钱和功夫供母亲读书啊。年幼的母亲背上经常背着小舅小姨,稍大一些就跟着外祖母外祖父下地干活。
母亲把消息告诉瘫坐在沙发上的父亲,他正戴着老花镜津津有味地读一本书,一缕听闻添丁的喜色稳坐在眉梢。
要不你陪我一起去吧。母亲小心翼翼试探地问。
父亲脸上瞬间升起丝不悦,他看了母亲一眼,而后别过脸去,没有吭声。
母亲的心顿时跌入谷底,她闷着气,踉踉跄跄走进厨房,粗糙的手一把打开水龙头,“哗哗哗”——清凉水花飞溅。怔怔站立片刻,母亲心不在焉地洗刷起来。一阵锅碗瓢盆乱响,宛若这些年叮当作响的日子,母亲的眼泪像风中的叶子扑簌簌掉落下来。
许多年前的那个深夜顿时浮现在母亲脑海里。那一年新婚夜,为这个狠心的男人,她流了一夜的眼泪。往事如生锈的刀子般伸过来,一刀一刀钝钝地割着她脆弱的心。
云淡风轻的夜,鞭炮声不断,热闹喜庆的气息弥漫着整个村庄。现在想来,竟夹杂着些许的讽刺。母亲一身红衣,端庄地坐在新婚房泥炕上,盯着窗棂外的梧桐树影发呆。屋外吃饭、喝酒的声音此起彼伏,一声声滑落在她的耳畔,燃起两片小小的红霞。一轮圆月静静地悬挂在院子上空,清凉的月亮照亮了整个村庄。
母亲心底隐隐忐忑不安,她早就耳闻,新郎心高气傲,看不上一字不识的她。传闻,他读书成绩优异,多次获得市知识竞赛奖,年纪轻轻,十九岁就去了高中学校当老师,班里一些学生比他自己年龄都大。
夜向深处沉去,人群如潮水般散去。当夜恢复原有的寂静,她顿觉自己心跳加速。她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平静下来,远处的犬吠声回荡在缥缈的夜空中。左等右等,久久不见新郎的到来,她愈加不安,开始小声地啜泣起来。
就这样干等了一夜,她连我父亲的半点影子也没见到。
第二天一早,哭肿了眼睛的母亲去见祖父、祖母。她跪在地上号啕大哭,祖父、祖母双双慌了神,这才明白,父亲这个逆子趁乱逃婚了。
委屈、气愤、绝望在母亲心中沸水般翻滚,她感到一种深深的羞辱把她拉入黑暗的深渊,她一眼瞥见屋檐下放置的一瓶农药,紧紧攥在手里,浑身颤抖,转身钻进了婚房。
父亲师范学校毕业后,听从祖父的叮嘱,工作分配到我们镇一所高中,开始了端国家饭碗的生涯。年轻气傲、心比天高的他,自是万分不同意儿时父母定下的娃娃亲。尽管他听说母亲模样长得顶俊俏,人也勤快,但他也听说了她没文化,不识字,没上过一天学。他从心底深深厌弃着母亲。
祖父认死理,他极力说服父亲。婚姻这件事上,年轻的父亲自是明白犟不过祖父的。他表面上佯装同意了,心里却悄悄拿定了主意。一个计划在父亲心中悄悄酝酿着。
那天,夜色掩护下,父亲一口气沿着马颊河跑了三十里,在一个同学家躲了起来。直到五天后,他听说性情倔强的母亲端起了一瓶农药,年轻气盛的他才回来,红着眼睛,泄了心气。
母亲试图用自己的勤劳、善良唤醒父亲沉睡的爱。昏黄的灯光下,母亲眯着双眼,细细地缝制一双双千层底布鞋。她不厌其烦地穿针走线,把家人四五年后穿的鞋子提早做完了。
她把一双蛮精致的布鞋恭恭敬敬地递到父亲手里,让父亲试穿。祖母手拙,父亲歪歪扭扭的鞋子,经常遭人笑话。母亲的鞋子,父亲很满意,他拿过去,穿在脚上,不大不小,不肥不瘦,正合适,他不由得向母亲竖起大拇指,手巧极了。
母亲微笑着,父亲也眯着眼笑了,此时,父亲暂时忘了母亲没文化的身份。鞋子的尺码要合脚穿起来才舒服。擅长做鞋的母亲,在婚姻的这双鞋里却不时磕出血来。
这个外人看来和睦的家庭,其实,一开始就内藏了“文化”这一道肉眼看不见的痕。多年来母亲试图努力修补这一道痕,然而,一到卡口,裂痕仍脆弱地暴露在阳光之下。文化这根亮闪闪的刺,深深扎在家人的心中。
2
几天后,父亲终于含糊答应下来,他同意先送母亲去唐山,然后自己再返回来。母亲听后,不安的心稍微安顿了一些。
离开熟悉的乡村去陌生的城市,对一字不识的母亲是极大的挑战。
没有文化,她极度缺乏安全感。出行前几个晚上,她在床上烙煎饼,怎么睡都睡不着。她旋开灯,一骨碌爬起身,打开行李箱,一遍遍检查行李。她翻看着亲手给小孩子缝制的碎花棉袄,粗糙的大手来回摩挲着,里面是地里刚收的新棉花,弥散着阳光的味道。她合上行李箱,重新上床,眉头紧蹙,再次淹没在不安与焦虑的海洋里。
晨曦微露,母亲紧紧抱着软布包,喘着粗气,急匆匆跟在拉着行李箱的父亲身后。离开村庄的母亲像一尾搁浅的鱼,脆弱,胆怯,说话轻声低语。
火车还没来,母亲贴在座位上焦急地等待着,中途,一直缓缓喝着茶水的父亲起身去了厕所。望着父亲渐远的身影,她心生一些羡慕来,她不敢喝一口水,她怕自己上厕所误了火车,舔了下干裂的嘴唇,感到有些口渴,一直强忍着。
火车站开始播报检票的消息,候车的人迅速站成一条长长的队伍。父亲连忙起身,拉上行李箱,母亲小孩子般紧跟其后。她被闹哄哄的人群挤簇着,深一脚浅一脚地涌进站台。耳膜鼓胀得厉害,眼皮突突地跳动,站台上,列车醒目的几个大字,她不认识,那些奇形怪状的编码,此刻龇牙咧嘴地冲她笑,笑她没文化。母亲感到一阵心慌,焦急地赶上父亲。村里的路她闭上双眼都能娴熟地走来走去,而眼前的路却如迷宫般。母亲睁着清水一般的双眼,紧跟着父亲,生怕迷失在拥挤的人流里。
火车在平原穿行,母亲战战兢兢,一刻不敢合眼,不敢乱动,保持僵直的姿态,五个小时的车程,对母亲来说,仿佛经历了漫长的大半生。父亲很快呼呼睡着了,身子瘫软着,嘴巴微张,嘴角不经意流出一滴口水,拉得好长,母亲拿纸巾帮他擦拭掉,他没有察觉,继续酣睡着。
到弟弟那里,父亲住了两天就买火车票回家了,母亲执意送父亲去火车站,被父亲一口拒绝。“你送我去车站,你到时怎么回来?你又不识字”, 父亲厉声说道。父亲走后,一番说不上来的苦楚在母亲心里翻腾着,她知道,父亲心里,还怨着她不识字,嫌她丢人。恍惚间,她不由想起多年前的一个下午。
那时,她还年轻,不到四十岁,一心急着去玉米地里灭草。她信步穿过一间一间的房子,来到储物间。阴凉的水泥地上,立着十几瓶花花绿绿高高低低的农药瓶,阳光穿过窗棂打在它们身上,投射出浓浓的阴影。望着一堆农药瓶,她一时犯了难,忘了哪一瓶是灭草的。母亲哆哆嗦嗦在储物间观望了许久,在记忆的井里拼命打捞那些农药的记忆,试探着掂起两瓶农药,绿色与红色的药液,晃动着绚丽迷幻的色彩,蛊惑着她的心。母亲定了下心神,她再一次睁大眼睛,终没有打捞到一点记忆的影子。
她泄了气,一屁股坐在地上,紧紧咬住嘴唇,心里恨着自己不识字。
她不得不鼓起勇气去问父亲。
父亲正在里屋斜躺在床上看书,突然被母亲打断,有些气恼,他鄙夷地望了母亲一眼,一言不发,坐起来,气呼呼转身走了。他恨恨地离去,让母亲一个人承受不识字的惩罚,留下她孤零零、无助地对着地上一堆花花绿绿的农药瓶发呆。父亲一走了之,加重了她内心的文化之殇。
不识字这一株庞大顽固的杂草,一直肆无忌惮地长在父母的婚姻地,偶尔,表面的丰收掩盖了它,一旦有机会,它便会冒尖疯长,婚姻的田地变得荒凉与虚无。
十几年过去了,命运的经纬线在半空画了一个圆圈,相同的剧情又一次重演,母亲无奈地叹了一口气,默默返到房间里。
3
弟弟上班去了,房间空荡荡的,像一个空空的巢穴,母亲宛若一只惊弓之鸟,一个人坐在沙发一角,她竖起耳朵,时刻听着茜另一间房间的动静。茜一边吃零食一边看韩剧,哈哈的笑声不时从门隙飘来。渐渐地,笑声缓解了母亲的紧张。
母亲望着沙发上堆的这一处那一处的脏衣服,开始收拾起来。
抱着一大捆衣服,走到洗衣机前,她又一次犯了难。
仿佛古人穿越到现代社会,智能手机、电脑、洗衣机,稍微复杂点的电器母亲统统不会使用。面对这些现代家用电器,母亲如临大敌。上面密密麻麻的字,指引着各种复杂的程序,让母亲感到一阵阵头晕目眩。弯弯曲曲的文字密码,像她看不清的人生路一样,让她心生彷徨。
她顿了顿,转身走去卫生间,拿出一个大盆子,粗糙的手搓洗起衣服来。
大腹便便的茜去厕所时,正好看到了这一幕。
妈,有洗衣机呢。她赶紧扶母亲起来,帮着把剩下的衣服一骨碌放进了洗衣机。很快,机器飞快地转动,母亲一脸神奇又无措地看着,像个无辜、纯净的孩童,茜忙拿了一张纸巾帮母亲擦脸上细密的汗珠。
茜慢慢和母亲熟识起来,母亲的和蔼与勤快拉近了茜与她的距离。
黄昏的阳台上,母亲手持喷壶给花草浇水,那些本来有些枯蔫的花草,在母亲的精心养护下开着五颜六色的花,房间愈发干净和明亮起来。茜赶紧搬来一张竹椅,示意让母亲坐下。母亲忙招呼茜,慢点,不要急,别闪着腰。茜递给母亲一杯水,俩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不时哈哈大笑着。
茜小时因父母忙于工作,她被一直寄养在乡下祖母身边,她的祖母不识字,但醇厚善良,她在母亲身上找到了久违的熟悉和亲切感。
一天夜里,茜感觉肚子痛得撑不住了,貌似孩子要出来了。弟弟慌忙喊醒睡着的母亲,母亲颤巍巍的,差点摔倒,望着两个孩子,母亲顿了下心神,她镇定下来,一边吩咐弟弟拿上备产包,一边安慰着慌张的茜。一直把茜送到医院,茜的父母和月嫂同时赶来了,母亲才舒了一口气。
住院的几天,茜的母亲专门请了假守在旁边,喂汤喂水。月嫂在一旁照看小宝宝。母亲,又一次变成了一个多余的人,木木地站在那里。她感觉自己怎么做都不是,不识字,方言也不通,叫医生、与医生交谈的事根本做不来,她再次感受到了文化对她的残忍,不由想起了岁月里的那一瓶农药。她默默地帮衬着月嫂,仿佛月嫂下面的一个小工。
因为不识字,一堵无形的墙横亘在母亲和世界之间。母亲又变得惴惴不安,话也不敢多说一句,如同一个闯入者格格不入。
从医院回家的那一天夜里,宝宝突然哭了起来,嘹亮的哭声惊醒了寂静的夜晚。半个小时过去了,宝宝的嗓音逐渐喑哑,仍在哭着。
母亲被哭声猛然惊醒,她一把坐起来,披了件外衣匆忙赶去宝宝的房间看。月嫂和茜一脸焦虑的表情,疲倦的茜脸上还挂着两行眼泪。
许是回来吓到了。母亲看了一眼,有经验地说。
月嫂半信半疑。经过正规培训,持有育儿证上岗的她,难以相信一个没有文化的乡下老太太的话。
母亲用粗糙如树根的手接过宝宝,另一只手在宝宝额头上轻轻抹了三下,嘴巴念着几句听不清的话语。
小宝宝瞬间停止了哭泣,一双圆溜溜黑珍珠般的眼睛眨也不眨地望着自己的祖母。
月嫂和茜开始敬佩起母亲来。
4
茜第二天打电话过来,对我说,姐,别看咱妈没文化,其实心里灵着呢。
我在电话这端,远远地听着茜甜美的声音,哑着嗓子,嗯了一声。茜不知道,这是这么多年来,母亲头一次被人说“心灵”。
许是没有文化,母亲在家里的地位一直不高。
祖父读书读到小学毕业,字写得尤为工整。一辈子没出过村的祖母,读书读到小学三年级,仨瓜俩枣日常的字将就够用。父亲更不用说了,上学期间,奖状贴满一屋子,数理化比赛常获市竞赛一、二等奖,高中毕业后,他考上一所师范院校,在偏僻的小村实属为数不多的个例,引起一时轰动。
唯独母亲,一字不识。
没文化的种子渐渐长成一棵卑微的树。记忆中的母亲,时常盯着墙上张贴的父亲手写的毛笔字发呆,她陷入了深深的沉默。
天还没亮,母亲窸窸窣窣穿衣起床了,她一把扛起锄头,扎去地里干活了,一直到祖母做完早饭,母亲才扛着锄头回来。中午,明晃晃的太阳像吸血鬼般垂下来,母亲拖着疲倦的身子从田地里归来,她的裤腿上沾满了泥点。幼小的我靠在门边,帮母亲打开门,望着母亲放下农具,踱到井边,拿一块肥皂一遍遍洗手。在幼小的我眼里,母亲沉默、勤快,像是家里雇佣的一个长工,没日没夜地干着农活。
父亲忙完学校的事,骑着自行车从镇上归来。他齐整的白衬衣,洁净的黑裤子,笑嘻嘻地一把举起我和弟弟。吃完饭,父亲打开书本,开始教我和弟弟读书、识字,他在院子里画下一张张围棋的格子,教我俩下围棋。
母亲,哑了口,没文化这一事实让她在家里矮了下去。她一天天扎在地里,与土地说话。也许,唯有土地才能更深刻地了解她。可是,离开父亲,她甚至连她心爱的田都种不好。
没文化的人就是睁眼瞎。年迈的祖母眼里透出一道我看不懂的光。
“睁眼瞎”这三个字如一根毒针深深刺痛了年幼的我,也刺痛了母亲。
夕阳最后一道光渐渐隐去,天色暗淡下去,黑夜悄悄来临。年轻的母亲独自一人蹲在家门口小胡同里,两只瘦弱的胳膊紧紧抱住自己的膝盖,脑袋缩在膝盖上,像一只受了委屈的鸟雀,两条俊俏的麻花辫无精打采地垂下来。
妈,奶奶喊你吃饭呐。稚气的我跑进胡同,伸着小胳膊拉着母亲,妄想把她从地上拉起来。
母亲不吭气,继续抱着脑袋。
她许是生了闷气。我不解地想。
幼小的我有些惴惴不安,天越来越黑,邻居家的一棵大榆树伸出树丫冲我做鬼脸,像动画片中的恶魔。五岁的弟弟东倒西歪地从家里摸了出来,妈妈,他稚气的声音在胡同里回响。
呜哈,母亲一把打开抱在双膝的胳膊,和我们玩起了藏猫猫。
见我和弟弟哈哈大笑,母亲抹了一把脸上亮闪闪的东西,也跟着笑了起来,三个人的笑声飘荡在胡同口上空……
许多年后,我才懂得,母亲为我和弟弟做出的种种牺牲,那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妇女本能给予孩子的爱,伤痕横生的一纸婚约下,母亲苦苦支撑。
5
一个多月后,茜出了月子,母亲开始念叨起故乡来了。
弟弟心里明白,从没离开过家的母亲想家了,她担心父亲一个人在家照顾不好自己。弟弟工作忙,一时走不开,一直担心母亲在城市不适应的我,赶忙请了年假,飞去唐山接她回家。
飞机飞行在广袤大地的上空,金色的阳光斜射过朵朵白云,天空呈现一片澄澈。我开始一点点回忆起母亲来,目不识丁的母亲。
小囡啊,你可要好好读书,好好学文化,母亲的声音一遍遍在耳畔回响着。
在母亲的叮嘱下,自小我就知道读书的重要性。教室里,我聚精会神地听老师讲课,跟着老师徜徉在知识的海洋。我认真记下密密麻麻的笔记,把所有的精力都花费在学习上,像母亲没日没夜耕种田地一样,我耕种着学习这一片土壤。我的内心深处,文化的饥渴与惶恐相互交织着,我害怕重蹈如母亲一样的命运。
文字却渐渐拉开了我和母亲的距离。我和母亲之间慢慢隔了一条深不见底的沟壑。
十六岁时,我考去了县城一所重点高中读书。一次周末,刚回到家,跨出屋门,望见母亲在院中拿着一把鸡毛掸子抽打着铁丝上晾晒的被子。飞扬的尘埃,呛得她咳嗽。发觉我站在她身后,她扭头慈祥地望向我,停下手里的活儿,和我闲言碎语。
“小囡呀,家门口每天都有几个去后街打工的小姑娘走过,妈看见一个小小瘦瘦的身影,怎看,都像你呀。”母亲温情地说,眼睛有些湿润,白发在阳光下闪着光。
“妈妈每次都忍不住望呀望。”母亲仿佛双眼望穿了我。
年少的我哪有空听母亲的啰唆,嗯了一声,一脚钻进屋子学习去了。我心里急着复习功课,自打上了高中,学习压力像充气的气球一下子膨大了起来,我奋力追赶,都回不到初中时的名列前茅。
心气高的我心里暗想,我才不打工呢,才不能成为村庄里一个没文化处处让人看不起的人呢。
又几年,我考去了三四百公里外的烟台读大学。每次去烟台,坐火车都要熬一个长长的夜,第二天才能到。母亲又开始睡不着,一夜睁着眼睛,专等我第二天到了报平安。
“小囡啊,你以后找工作可不要找坐过夜火车的地方呀。”母亲几乎哀求道。
“好好好。”我佯装应着母亲,继续攻读功课。
几年后,我又考去了更远的西安读研究生。我一天天飞远,母亲一天天老下去,变得愈加唠叨。一次放假在家,母亲盯着我望了许久,欲言又止,最后终于唯唯诺诺地说:“小囡呀,你要是不读书,早结婚生子了呀。你看看,和你同龄的谁,刚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我立马不高兴起来,我才二十五岁,大好的青春年华。头次感觉母亲竟变得如此俗气,许久以来,文化形成的壁垒开始凸显。
母亲又开始絮叨,自己二十五岁什么样子的,怎么嫁入父亲家的。她许是没料到我早已知晓那个家族隐秘。
妈,我结婚?像你一样?急匆匆赶着一个不爱你的人结婚?被人嫌弃没文化?然后一辈子围着孩子转,没了自己?
不尊重的话语在那一刻暴雨般一倾而出,句句击中母亲的心。母亲一下子愣住了,身子骨微斜了下,她终是没有料到我如一把机关枪般的反唇相讥。
她一下子瘫坐在床上,怔怔地一句话不说,一滴眼泪在母亲浑浊的双眼里打着转儿。
我有些后悔自己没脑子就蹦出来的话,如此真实,如此残忍,摘掉了长久以来我佩戴的乖乖女面具。原来一直以来,我骨子里是以母亲没文化而感到耻辱的,我深深厌恶着自己。
文化这根针被我深深地扎入母亲的心里,也再一次划伤了我。
我和母亲心口共同滴着血。
是的,母亲一天学也没有上过,只认识几个阿拉伯数字,其他一字不识,一天天印着“文盲”的标签在世间行走。母亲是无辜的,这不能怪罪于她。我怎能体会没文化的人那种深深的无助感,我也终是无法想象,不识字的世界是怎样的,那个属于母亲孤零零的世界,在弱肉强食的风雪中飘零。
我曾心里苛责过母亲,文盲的她不能像我同学身为老师的母亲那样,说出几句引领人生的话。我曾暗自埋怨过我的母亲,作为一个女人,不能给另一个女人讲一些女人隐秘的事。我怎能如此苛责一个连自己命运都无法掌控的文盲母亲呢?
我头一次感到,文化带给我的残忍。文字的功能是记录、传递,呈现心底的善良,我却忘了文字最初的意义。母亲虽不识字,她在我心中却写下了一个大大的“人”字。
多年以后,当成年的我再次面对母亲没文化这一事实时,我的眼里充斥着泪水,我多想去拥抱这个倔强没文化的女人,她只是千千万万底层农村妇女中的一个,她用自己的方式维持着几乎残破的婚姻,野草一样倔强地生长在人世间,薄薄的,水一般的命运。
6
母亲这尾搁浅的鱼终于回到了熟悉的村庄熟悉的水域,呼吸着村庄清冽的空气,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个月仿佛一个世纪之久,母亲揉了揉浑浊的双眼,仔细地瞅着这个熟悉的小村落。夕阳的光辉穿过胡同映射在母亲的身上,镀了一层淡淡的金色。
父亲早早地站在村口等候着,见到母亲,他眼里闪过一丝亮光,这么多年了,头一次。他匆忙走上前,接过她手中的软布包,温柔地嗫嚅道:回来啦,走,咱回家。母亲去唐山后,从没离开过母亲的父亲,时常在一片冷清里想念母亲在的温暖日子。
吃过晚饭,弟弟打来电话,妈,你在家好好照顾自己,有保姆在,别挂心。
奔波一天的母亲窝在自家沙发上,静静地睡着了,睡得那么安心,发出均匀地呼吸声。一滴晶莹的泪滴从母亲眼里无声地滑落下来,被一旁的我轻轻擦拭掉……
责任编辑 李知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