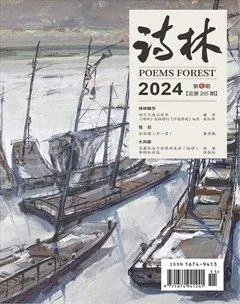光阴谣(组诗)

未诞生的
水渠边伏着一只貉子
我们发现时它已经死了
那是一只年轻母貉
刚换了浅棕的毛,腹部圆滚滚
粉色小乳房已开始鼓胀
穿过几百米田埂
对面是一片树林
在一棵桦树下我们埋葬了母貉
和它没有诞生的孩子
它们安静地睡在母亲的身体里
保留着初始的洁净和完整
而死亡本身
既不能使它们恐惧
也不能将它们分开
橘 子
那时候
我们围在一起
等父亲小心剥开
不知他从哪里带回的一个橘子
我们看着他仔细地数过一遍
再一瓣一瓣地
分到我们手里。就这样
我们兄妹四个
将小小金黄的月亮装进身体
又把橘皮放在火炉上
我们那么欢喜。橘子的香甜
装满我们的房子
父亲在的时候
我们还不懂橘子的悲伤
不知道我们的家
是一个六瓣的橘子
月 亮
很久以前
在乡下场院的麦秸堆上醒来
你突然发现
置身于一个巨大的坛子里
坛子口很小
从那儿看出去
外面的世界宁静而金黄
父亲牵着马
石磙子一圈一圈吱吜吱吜滚过
整个坛子
都跟着微微颤动
黄 昏
窗外的秋天落着叶子
榆树下
父亲和他继父用锋利的刀头
为灰骟马修蹄子
偶尔,长长的马尾向左或向右
轻轻扫一下
那是一匹被时间和鞭子驯服得
不能再温顺的马了
母亲在割葵花秆
干枯的葵叶沙啦沙啦响
最后一根葵花秆倒下后
黄昏空旷起来
晚霞已消散
灰蓝的天空垂挂在屋檐下
吹了一天的风停了
祖母用谷糠填满我的花布口袋
就着暗淡下来的窗口
她一针一线,将豁口缝补上
遗 骸
一头两百吨的蓝鲸
在西太平洋深海缓缓下沉
日落时分
刚果东部的热带丛林里
一只年老的母象蹒跚着
离开象群
我在亚洲。中国东北
三江平原腹地的电线塔下
捡起碎石土块
掩埋一只鹞鹰
我知道我终将留下什么
我知道泥土为什么
沉默而蓬勃
光阴谣
听一首歌的时间
云已不是原来那朵
打湿脚踝的露水凝成薄霜
有人为新生的白发惆怅
更多人头顶积雪
打马跃入铜镜
风一直吹啊吹
我们只身而来,我们
独自远行
人世依旧蓬勃生动
蝉蜕接满雨水
有人坐过的椅背
已爬满青藤
仿 佛
有声音漫过我
它来自语言的水泽
又或者,酒杯空置
繁花穿梭于四月的雨水
夜晚的屋脊上
酒醉之人击打掌中的燧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