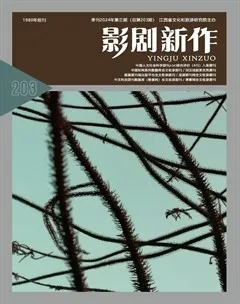《周处除三害》:一个现代反英雄的道德观
摘 要:电影《周处除三害》通过主角陈桂林的故事,展现了一个现代反英雄的形象,探讨了正义与杀戮的主题。陈桂林在面对终极生命的挑战时,选择通过除掉社会“三害”来追求个人的救赎和社会的正义。从反英雄的道德视角出发,深入剖析影片中陈桂林所面临的道德困境与内心挣扎,探讨这一反英雄形象如何映射并挑战现代社会的主流道德价值观。通过对主角形象的解构分析,旨在理解个体在复杂社会背景下如何在道德灰区中寻找正义的实现路径。
关键词:《周处除三害》 反英雄 道德冲突 社会道德观
《周处除三害》的故事源自《世说新语》。周处是东吴义兴人,他年轻时勇猛但性格蛮横,与危害乡里的蛟龙、猛虎一同被称为“三害”。后来,他听从他人建议,决定为民除害,先后杀死蛟龙和猛虎。但当他回家时,发现村民误以为他死了,正在庆祝。周处深感羞愧,决定改过自新,最终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通过现代化的重塑,导演成功地将周处的历史形象转化为陈桂林,一个深陷道德困境的现代人。电影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让观众在紧张刺激的猎杀故事中,体验到人物内心的道德挣扎与深刻反思。《周处除三害》的市场表现及其引发的广泛讨论,显现了观众对于影片所触及道德和社会问题的共鸣。导演利用复杂的叙事结构和深刻的人物塑造,让这部电影超越了传统杀戮故事的界限,成为了探讨现代社会道德观念和正义实现方式的重要文本。电影里这种反英雄的道德观提供了对传统正义概念的挑战和扩展,《周处除三害》中的陈桂林,既不是无瑕的圣人,也不是单纯的猎杀者,他的形象和行为让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正义、猎杀和道德的界限。电影中的这种“陌生化”叙事策略,不仅使故事更加引人入胜,同时也促使观众对自身的道德观念进行反思。
一、反英雄形象的塑造与特征
《周处除三害》通过陈桂林的故事展现了一个典型的反英雄形象,挑战了传统英雄叙事并引入了复杂的道德议题。
反英雄,并不是简单地反对英雄,而是在其行为和道德选择上展现出与传统英雄不同的特质。在现代文学和电影理论中,反英雄的定义通常指向那些复杂的角色,他们在道德和行为上显著偏离传统英雄的典型特质。他们可能并非完美无缺,他们的行为可能引起争议,但正是这种复杂性使得反英雄角色特别吸引人。与完美无缺、道德绝对化的传统英雄相比,反英雄的形象更为接近现实中的普通人,他们的选择和行为常常引发观众对于“什么是正义”和“什么是道德”的深入思考。普通人的觉醒和英雄的世俗化缩短了英雄与普通人之间的距离,从而为“反英雄”铺平了道路,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一批“反英雄”形象,使崇高的英雄品格不断被“降格”,即不断被“祛魅”“去神”和“世俗化”。[1] 反英雄既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也不是彻底的反派。他们往往拥有英雄的某些特质,如勇气和决心,但这些特质被他们的缺陷、恐惧、道德模糊性或反社会行为所平衡。这些角色的存在挑战了传统的道德二元对立,提供了一种探索更为复杂和真实的人性的路径。在西方早期戏剧作品《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反英雄的人物形象就已存在,并成为了一种重要的叙事元素。他们在道德、能力和意志力上都超越了普通人,但在人格上却有一定的弱点。通过主人公的垮台,观众将体验到“怜悯和恐惧带来了这种情绪的净化”。[2] 同样在电影方面,《黑暗骑士》中的角色哈维·登特(双面人)就是一个典型的反英雄人物。最初作为哥谭市的地方检察官,他以坚定不移的正义感和打击犯罪的决心受到人们的敬仰。然而,经历了一系列个人悲剧和精神崩溃后,他变成了一个猎杀心切、通过抛硬币来决定他人生死的双面人。尽管他的行动由失去所爱的痛苦和对正义的扭曲追求所驱动,但他的方法和决策常常引发道德上的争议,使他成为一个既有英雄色彩又带有明显反面特征的复杂人物。再如《周处除三害》中的陈桂林,他通过采取极端手段追求个人所认为的正义,体现了反英雄典型的道德复杂性和个人挣扎。尽管他的目标可能是正义的,但他的方法和所面临的内心冲突使他成为一个典型的反英雄形象。这种角色塑造反映了现代观众对于道德灰色地带的探讨和接受,以及对于传统英雄叙事的重新审视。
电影中陈桂林的形象和行为展现了反英雄的多个关键特征。首先,由于被张贵卿欺骗自己得了癌症,本想自首的他却在警局看到了自己的通缉令,只因为自己仅排第三而被其他画报遮挡,所以打算除掉通缉令上的另外两名以此获得声名。他的行为驱动并非出于无私的英雄主义,而是提升个人名声的欲望,这一点打破了传统英雄形象的道德光环。其次,陈桂林在猎杀的过程中经历了深刻的道德冲突和内心挣扎,如陈桂林在杀掉许伟强之后折回其住处解救程小美的情节,这种复杂的心理活动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好恶二分法所能涵盖的范围。此外,影片也未将他塑造为一个全能的角色,他的计划和行动都有可能失败,如本想除掉首害林禄和的陈桂林却被其骗去钱财,活埋于棺材之中。这种脆弱和不确定性使得反英雄形象更加丰满、真实。通过这些具体情节的描绘,《周处除三害》不仅展现了陈桂林作为反英雄的复杂形象,也促使观众深入思考个人行动与社会道德之间的复杂关系。电影通过这种深刻的人物塑造和情节发展,挑战了观众对传统正义的看法,引发了更广泛的道德和社会问题的反思。
这种反英雄的塑造与特征反映了现代社会中对于传统道德和英雄概念的重新审视。约瑟夫·坎贝尔在《千面英雄》中指出,英雄旅程模型在现代社会中经常需要适应新的文化和社会现实,反英雄的出现正是这种适应过程的一部分。同时,影片中对反英雄道德冲突的探索,也与现代伦理学中关于道德相对主义和情境伦理学的讨论相呼应,强调了在复杂多变的现实世界中,道德判断和选择往往没有绝对的标准。可以说这种对反英雄形象的深入探讨,不仅丰富了电影叙事的层次,也为理解和评价现代社会中的道德和正义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道德冲突与内心挣扎
社会道德观念与个人利益或个人正义之间的冲突是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冲突不仅涉及道德哲学的深层问题,也是许多电影作品中的核心主题。反英雄的电影人物角色通常会面临道德上的挑战和选择,这些挑战往往迫使他们在个人利益和更广泛的社会、道德原则之间做出选择。乔治·赫伯特·米德的符号互动论提出,个体的行为和道德观念是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意味着个人的道德判断和社会道德观念是相互影响、动态发展的。然而,当个人对正义的追求与社会的道德规范发生冲突时,便产生了复杂的道德困境。在《周处除三害》中,道德冲突与内心挣扎是塑造陈桂林这一反英雄形象的核心。在违反法律法规的极端行为与为民除害的扬善行为的交融下这种个人行动与社会法律、道德之间的张力,呈现出了电影对于个人与社会、正义与法律之间复杂关系的探讨。另一方面,电影通过紧张的叙事和丰富的人物心理描绘,展现了主角在追杀过程中面临的道德困境和心理斗争,深入探析了为民除害追求正义与突破法治肆意杀戮之间的模糊界限。
陈桂林内心的道德冲突根源于他对自身行为后果的深刻反思。由于在公共场合枪杀黑帮头目,陈桂林不得不隐姓埋名四年。这四年的流离失所不仅使他错过了与奶奶最后的相伴时光,奶奶故去亦令他悔恨交加。与此同时,张贵卿的欺骗使他坚信自己患有晚期肺癌,由此产生了在有生之年扬名立万垂范千古的愿望,决心惩恶扬善,铲除邪恶势力。然而,惩奸除恶虽系正义之举,但肆意杀戮违背了法治底线,因而导致了陈桂林内心的价值观冲突。一方面,他是为民除害的“正义使者”;另一方面,他本身的所作所为同样触犯法律。从道德与法律层面而言,这不仅关乎个人行为正当性,更关乎实现正义的方式是否得当、是否具有普遍性。
陈桂林作为一个猎杀者,其决定以暴力手段除掉社会上的害虫,这种决定和行为表面上看似坚定和果断,实际上却是他与内心阴影的直接对抗。电影中的多个场景,如陈桂林在准备执行猎杀计划前的犹豫、误以为林禄和已死后的失望和迷茫,以及在暴力行动中显露出的痛苦和纠结,都生动描绘了他内心深处的道德冲突和心理挣扎。这些挣扎不仅源于他对猎杀行为后果的担忧,更深层地反映了他对自我身份和存在价值的质疑。对此,心理学家卡尔·荣格的阴影理论提供了一个理解陈桂林内心挣扎的框架。在卡尔·荣格的分析心理学中,“阴影”代表个体潜意识里被压抑或否认的那部分自我,其原型是人心灵中最黑暗、最深入的部分,也是人性中阴暗的不被表现出来的部分,它是“个体的有机部分,因此它希望以某种形式与个体合聚一体。它的存在也不会因为把它理性化就可以消减掉”。[3] 阴影不仅包括负面情绪和思想,也可能藏有未被实现的正面潜力。阴影的存在是人类心理复杂性的体现,它既是个体成长和自我实现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挑战,也是自我认知深化的重要源泉。通过阴影理论的视角来看,陈桂林的猎杀之路可以被解读为一场寻求自我完整和认同的旅程。阴影中蕴含的不仅是个体的暗面,也有被忽视或未被认可的潜能和价值。电影展现了陈桂林在面对自己阴影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猎杀并不能真正解决内心的矛盾和痛苦,真正的挑战是如何接纳和整合这些阴影部分,找到更加成熟和平衡的自我。荣格认为,面对和整合阴影是个体发展的重要步骤。陈桂林的故事提供了一个探讨这一过程的生动案例。尽管电影最终可能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但陈桂林的挣扎和反思促使观众思考如何在现实生活中认识和处理自己的阴影,如何在接纳自身复杂性的同时,寻求更广泛的社会正义和个人的道德立场。
陈桂林的道德冲突和内心挣扎是《周处除三害》探讨杀戮与正义主题的核心。通过陈桂林这一形象,电影不仅展现了个体在道德选择上的复杂性,也对现代社会中正义的本质和实现方式提出了深刻的质疑。这种探讨促使观众反思个人行为与社会道德之间的关系,以及在现代复杂社会中寻求正义的可能路径。
三、现代社会对反英雄道德观的接受度与反思
数字媒体和社交网络等新兴技术平台的兴起,为观众提供了更加直接的方式来表达自身观点、讨论道德难题,这无疑也推动了电影内容向多元化和复杂化发展。如《她》(Her)这部电影探讨了人工智能与人类情感的复杂关系。通过讲述主人公与一个先进的操作系统发展出深厚感情的故事,激发了观众对于人工智能发展所带来的道德和哲学问题的讨论。在网络上,人们讨论的焦点包括人工智能能否拥有情感、人类与AI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界定,以及这种关系对人类社会和个人关系的潜在影响。此外,全球化浪潮下的文化融合和艺术品跨境流通,使得电影创作需要面向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价值观的全球受众群体,因而不得不摒弃一味强加价值观的做法,而是尝试包容更广阔的道德视野。如《寄生虫》这部来自韩国的电影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巨大成功,并赢得了多个国际奖项,包括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寄生虫》通过讲述两个家庭之间的复杂关系,探讨了阶级差异、贫富不均等社会问题。电影的普遍吸引力在于其对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的深刻揭示,同时避免了对特定文化价值观的强加,让全球观众都能从中看到自己社会的反映。
现代社会的道德接受度经历了显著的发展和演变,从电影层面便可窥知一二。在电影角色和电影主题的展现上这种变化尤为明显。过去,电影中的角色和主题往往呈现为较为单一和二元对立的道德观,而今天,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观众视野的拓宽,对于复杂道德议题和多元化角色的接受度明显提高。传统电影作品常常采取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视角,将角色刻画为理想化英雄或彻底反面人物,主题内容亦侧重于善恶简单对垒。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全球化进程加快、信息技术飞速发展、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社会文化日趋多元,人们对复杂道德议题的认知和包容度也与日俱增。这种转变不仅反映在观众对于更加立体、真实的人物形象和富有深度的题材内容的渴求上,同时也深深影响了电影创作者本身的艺术理念和价值追求。因此,当代电影艺术在塑造角色形象和探讨主题内容上,展现出日益多元化、复杂化的趋势,这与现代社会对于道德接受度的显著提升存在内在联系。
从电影角色来看,以前的电影在人物设置上往往是非黑即白的设定,如《刘三姐》《地道战》《建国大业》《闪闪的红星》等,人物形象都带有明显的符号性。但如今越来越多的导演和编剧有意识地试图突破传统道德绝对论的框架,去探索人性的多面性和道德的相对性。因此,当代电影中出现了大量具有复杂内在动机和处于道德灰色地带的反英雄角色,如《我不是药神》中的程勇、《周处除三害》中的陈桂林等。这些角色的行为虽然常常超越一般道德底线,但通过影片中对人物形象细腻的刻画,观众能够体会他们的挣扎和内心世界,产生同理心。与此同时,电影主题也更加侧重于探讨社会正义、权力压制、个人自由等高度复杂的道德哲学命题,旨在引发观众对于固有价值观的反思。
与此相伴,当代电影主题也日益侧重于探讨复杂的社会和道德议题。传统商业片常常只是简单对垒善恶阵营的故事,这种套路的主题、情节随着高频率的复刻呈现渐渐地被观众和市场所摒弃。纵观2023年中国票房前十的影片均为国产片,像《速度与激情10 》《巨齿鲨2》等传统的好莱坞商业大片反而不受人们的欢迎。反观《周处除三害》《我不是药神》《寄生虫》等优秀影片更多反映出社会的阴暗面、权力的操控、人性的脆弱等富有思辨性的内容。从对正义、自由、权力滥用等话题的关注,可以看出电影主题的深刻反思,这也得到了现代观众对于更加内敛和有深度作品的认同。
《周处除三害》这部电影可以说是兼具了道德难题与社会普遍问题两点,在话题和种族、民族审美共性之间做出了一融合。从波斯纳的道德相对主义理论来分析电影《周处除三害》中的反英雄道德观及其在现代社会的接受度,提供了一个深刻的视角来理解这一文化现象。道德相对主义认为,道德判断和行为标准是相对的,依赖于个体所处的文化和社会环境。波斯纳曾声称:“我们不能令人信服地称一个无法喂养所有出生婴儿的社会中,堕胎是不道德的;我们批判纳粹不道德是因为事后看来纳粹的方案没有顺应其社会中任何言之成理的或广泛接受的需要或目标;而美国对印第安人实施的种族灭绝则顺应了这样的需要和目标,因此很少受批评;而我们称这些行为‘不道德的’‘邪恶的’只是表达了我们的厌恶或者是增加一种修辞的力量,所谓不道德只是一个称呼,我们更应说的是这些社会的道德法典不具适应性。”[4] 在这一理论框架下,陈桂林的行为及其背后的道德冲突提供了一种观察和理解现代社会对复杂道德议题接受度变化的途径。在《周处除三害》中,陈桂林作为一个反英雄的形象,其行为不完全符合传统英雄的道德准则。他采取极端手段来实现自认为的正义,这在传统道德观念中往往是不可接受的。然而,从波斯纳的道德相对主义角度来看,陈桂林的行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理解和同情。他的行动反映了他所处社会环境中存在的道德复杂性和冲突,以及在特定情境下追求正义的深层需求。采用道德相对主义理论来分析《周处除三害》不仅挑战了绝对道德标准的普适性,也提供了一种理解和评价现代社会中道德多样性的方式。它提示我们,在面对道德复杂性和多样性时,需要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同时,它也强调了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理解个体行为的重要性,以及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交融的当代社会,寻找共同道德基础的挑战和可能性。
通过波斯纳的道德相对主义理论来分析《周处除三害》中的反英雄形象和现代社会的道德接受度,不难看到现代观众对复杂道德议题的接受度有所提高。这种接受度反映了对个体在特定社会环境下所作道德选择的理解和同情,同时也表明在全球化背景下对文化多样性和道德多元性的认识和包容。通过电影这样的文化产品,观众被引导进行道德反思,探讨在复杂现实世界中如何寻求正义和道德的可能路径。但是,当代电影在追求道德复杂性和多元性的同时,也引起了电影评论界的一些批评和质疑。部分学者认为,过度迷恋道德相对主义和模糊化,可能会导致电影作品失去应有的价值导向和正面引领,陷入彷徨和价值取向的失衡。因此,电影创作应在探索复杂性和保持积极价值引领之间求取平衡,避免陷入相对主义的极端。
结 语
电影《周处除三害》中的反英雄形象,陈桂林,提供了一个对现代社会道德观念和正义实现方式的深刻反思。通过除掉社会“三害”追求个人救赎和社会正义的行为,陈桂林揭示了个体在道德选择和行为上的复杂性,挑战了传统的英雄叙事模式。反英雄的塑造不仅展现了其行为和道德选择上的独特性,也反映了现实中普通人在面对复杂道德困境时的挣扎和反思。这种角色的存在,促使观众深入思考正义与杀戮之间的界限,以及个人行为在社会道德背景下的定位。进一步,陈桂林的故事探索了社会道德观念与个人行动之间的张力,提出了在复杂社会背景下寻找正义的道路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过程。这种探索不仅触及了道德哲学的深层问题,也反映了现代社会对于传统道德和英雄概念的重新审视。随着数字媒体和社交网络的兴起,公众对于道德难题的讨论变得更加直接和多元,这无疑推动了对电影内容中道德和社会问题的广泛反思。
然而,需特别关注的是,在反英雄题材电影的叙事策略适应市场需求的过程中,暴力、毒品、童兵等元素虽然增强了影片的观赏性,却同时伴随着潜在的伦理挑战。这些商业化的内容在吸引观众眼球的同时,可能会引发道德和伦理上的争议,甚至可能对观者产生误导。因此,电影创作者们必须保持警觉,防止这种趋向误入创新的反面,即在追求观众注意力和市场效益时,偏离了艺术创作的伦理责任与社会价值导向。
参考文献:
[1]黄肖嘉.反英雄[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24.
[2]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2.
[3]荣格.荣格文集.[M].苏克,译.北京: 改革出版社.1997:4.
[4]理查德·A·波斯纳. 道德和法律理论的疑问[M].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24-28.
王英杰:四川传媒学院电影学院助教、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黄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