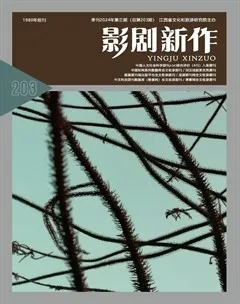折射当代戏曲创作得失的镜像
在当下,地方剧种乘借文化扶植的东风,普遍出现擢升文化品格、追求典雅化的倾向,这对地方剧种的发展应该是一件好事。擢升文化品格、追求典雅化的题材手段,无外乎朝着两个方向掘进:一是紧贴时代风向,继续发挥轻巧灵活的优势,积极创作响应时代精神的“现代戏”,直接歌颂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一是壮大文化情怀和历史担当,注目于地方历史文化的挖掘与塑造,不断创作反映地方文化品格的“历史剧”,成为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和宣传支持。尤其是后者,由于表现历史生活的戏曲艺术传统的积累、较少现实“时效性”的干扰,而更为地方剧种重视。苏剧《大树常青》,客观地说,在这一方面表现出了强烈的壮大文化情怀、塑造地方文化品格的意愿,并且能够通过现代编剧思维和舞台观念,形成完整、自足的戏剧文本。
一、戏剧内容与结构形式的成功之处
首先,要肯定苏剧《大树常青》表现历史、塑造历史人物潘世恩所取得的成绩。全剧共分为五幕,前有序幕,后有尾声,共计七个部分。作者集中笔墨,截取了晚清时期苏州籍重臣潘世恩一生中的五个片段,以此为结构,展开戏剧内容,塑造了潘世恩善权谋、知进退,既心怀天下苍生、家国前途,又深谙权力规则、久参密勿而不倒的复杂性格。这出戏为潘世恩准备了许多标签,适时逐一贴在人物的戏剧形象之上。剧中的潘世恩,是忠臣,是孝子,是慈父,是举案齐眉的丈夫;是乡贤,是鸿儒,是身处晚清权力中枢的风云人物。他是缄口免祸的政治“油条”,是救民于水火而不留姓名的慈悲义士,更是在关键时刻为国举贤的能臣。剧作通过五个场次的848V/jrl3qKhm+nO9RMq55qAMnRb3d//MVFBjI/iaO0=编排,将这些或平行、或交叉、或矛盾的性格统一于潘世恩一个人物的身上,应该说还是具备较高编剧能力的。承认人物个性的复杂,站在“人民性”立场对人物进行道德价值的定位,这本身体现出编剧思想的现代性,也是新编历史题材区别于传统历史题材最核心的价值差异。
从戏剧表现形式的角度考察,《大树常青》具有强烈的形式意识。剧本通过序幕和尾声,搭建出多重的时空维度,以仙子的引领和小女孩的对话,构成跨越时空的审视视角,使“对历史人物的评判”产生出时间的间离,对潘世恩的历史评价因而具有了沉淀之后的厚重感。这是今人与历史人物发生联结的戏剧形式纽带,也是全剧最外层的结构。进入戏剧正文之后,《大树常青》又以前后两次“心理的驳难”形成第二层的结构关系,以政敌、百姓、家人、皇帝、友人在内的众多人物对潘世恩的诘难,构成突出的心理压力和深度,并被设定为贯穿人物性格诸多方面、统摄五个场次、推进戏剧发展、带入观众情感的核心线索。如何理解潘世恩的“为官缄默”是解读全剧内容的钥匙,而对这一悬念的设计和渲染则是解读全剧结构的关键。全剧的五个场次被安排于注解“为官缄默”的结构逻辑之中,既构成了人物命运发展的线性历程,又是人物行状的分主题呈现,更是人物精神价值的递进式深入。戏剧形式结构的匠心,表现出编剧戏剧形式观念的现代化水准,以及驾驭戏剧形式的技术能力。
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来看,《大树常青》都表现出了强烈的现代化意识,不断拓展传统艺术形态与新的时代精神需求、艺术形式语言的兼容空间。这些探索都是有益的尝试,也必将与其他当下新编历史剧的实践与创新一起,不断丰厚当代戏曲的艺术矿脉。
二、“写人物”还是“演故事”?
单就剧作本身而言,《大树常青》总体上是一部不错的新编历史剧作,能够体现出当下戏曲编剧的水准。但是,如果绝大多数的当下戏曲,尤其是新编历史题材的编剧,都向着《大树常青》所秉持的编剧意识看齐,或者接近该剧的编剧水准,那么其中便蕴含了一种值得深思的倾向。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当下新编历史剧,确实如此。
从戏曲艺术的角度看,《大树常青》存在着两个具有代表性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写人物”还是“演故事”?
塑造人物,是叙事性作品的重要任务之一,表现人、塑造人,也是戏剧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之一,这是没有疑问的。塑造人物,依靠的则是人物所生活的环境,在人物的行动、人与他人的关系中具体进行,这也是没问题的。而对人物行动、人与他人关系等的表现,主要依靠故事,这还是没问题的。也就是说,“写人物”与“演故事”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不存在冲突。
但是,《大树常青》以五个场次的篇幅,截取潘世恩生命历程中的五个片段,着墨于开掘人物个性精神的众多方面,致力于向今天的观众全方位展示历史人物的精神风采。五个场次的用力较为平均,每场一个具体的事件矛盾,每场一个核心唱段。然而,各个场次矛盾之间的关联性并不强,虽然第四场“殿前议事”与第五场“迟荐真才”貌似具有因果关系的单元性,但是这两个场次在剧中的时间跨度也将近十年,而且是作为一种对比关系存在的,其间并没有任何场次的铺垫和过渡。事实上,全剧所有场次之间都存在非常明显的时间跨度,甚至有些场次之间还安排了时间的回溯。五个场次是紧密围绕着潘世恩漫长的生命历程展开的,从他中年隐居故乡开始,直到八十余岁迟荐真才,再加上序幕和尾声的穿越,全剧的时间跨度极长。然而,贯穿其间的主线,并不是连贯的故事线,而是如何形成潘世恩“为官缄默”的性格线。换言之,全剧的着眼点,不是在有限的舞台时空中编制一个连贯完整的故事,而是浓缩展示一个人物的生命过程,而对人物生命过程的展示又是散点式的。
剧作的重心并不在于如何讲述一个连贯完整的故事,而是全方位展现一个人。写“小故事”,而不写“大故事”;以“小故事”写人物性格中的某一方面,而不以“大故事”连贯整个戏剧,这就造成了“写人物”与“演故事”的背离。而且,“小故事”的编排不以人物的行动为抓手,主要依赖对话和演唱,即语言,也就是用人物的“语言”将故事的前因后果讲给观众听。观众不需要根据舞台表演理解故事叙事、感知故事的紧张感、感受戏剧表演氛围,只需要“听”和“想”就能够接收到足够的剧本所要传递的“信息量”。那么,观众观赏戏曲的“趣味性”到哪里去了呢?仅在于“听”那些“华丽”的唱段吗?
戏曲创作,需不需要在“故事”中煎熬“人物”呢?如果将传统剧目中并不存在完整的主体结构并且创作于1949年之后的历史题材戏曲称为新编历史剧的话,我们不难发现,其中能够长久“立住”、至今仍被传唱的,都是以“演故事”作为剧作重心的。《赤桑镇》《海瑞上疏》《孙安动本》《百岁挂帅》等等优秀的作品,都有着一条贯穿全剧的清晰完整的故事线。也有剧本具有时间跨度的,如《赵氏孤儿》,十五年的时间跨度是故事因果发展的间隔,而不是简单的类比和对照。戏剧的起承转合,也就是故事的起承转合,人物的性格在故事的发生发展中自然呈现。而故事也不是通过“话白”和“唱段”简单交代就算完成的,也不单单是借助舞美手段的烘托就能够完美呈现故事情绪、紧张程度的变化。它必须依赖人物的行动,也就是戏曲表演的技术手段来实现的。唯有通过行动,才能使“故事”真正被观众“看到”,唯有通过能够被观众“看到”的故事,才能够使人物的性格在故事的“煎熬”中落到实处。
正是看到了“故事”的重要性,尽管观点不同,但是戏曲理论家们仍都将“演故事”作为定义戏曲本质的中心语。
三、“写戏剧”还是“写戏曲”?
第二个问题是,“写戏剧”还是“写戏曲”?
在理论上,中国戏曲是中国民族的戏剧形态,所以“写戏剧”与“写戏曲”似乎并无矛盾。但是,因为中西方戏剧观念的巨大差异,在实际的语境中,“戏曲”在大多数时候被排除在“戏剧”的概念之外,这就造成了“写戏剧”还是“写戏曲”的区别。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同,直接的结果就是所创作的剧本有没有浓厚的“戏味”。
“写戏曲”要求按照戏曲的体制特色进行创作;“写戏剧”则是以西方戏剧(或者简化为以话剧)为剧作体制参照。“戏曲”剧作体制最主要的是“脚色制”,地方剧种在“大剧化”的过程中,逐渐完善出具备各自特色的脚色制度,而且剧本交由剧团搬演时也必须经过“脚色化”的处理,所以“脚色化”的问题暂时在当下戏曲创作中并不突出。
剩下的就是戏曲剧作的形式体式的问题,换言之,就是有没有按照戏曲剧本的样子去创作的问题。戏曲剧本的形式,有一套特殊的体式要求,如引子、定场诗、上下场诗(或对儿)、自报家门,或者锣鼓经、舞蹈动作等等。这些形式体式的存在,使戏曲剧本形成一种“程式化”构成倾向。人物通过这些形式“程式”,正式进入戏曲的舞台情境中,被观众“看到”并且“接受”,否则,除非一些特殊的功能性需要,或者非常不重要的辅助性角色,其余的舞台地位并不为观众所承认。比如“捡场”“撒火彩”作为舞台工种,不需要通过剧作的形式“程式”出场,因而观众永远不会将他们与剧中的人物角色相混淆。
但是,在《大树常青》中,类似的剧本形式体式统统被取消了,人物不需要通过引子、定场诗、自报家门、上场对儿等“程式”出场,对观众作出先声夺人的提示,而是如同话剧一样,自然地上场,自然地下场。这么做不是不可以,也不是不可以改革传统戏曲剧本体式,但是完全弃置戏曲剧本形式体式,会削弱戏曲作品的“韵味”。
对这些剧本构件的适度保留与形式创新,一方面可以保留或彰显戏曲的形态特征,另一方面,也可以契合观众对戏曲形态的认知。观众眼中的戏曲不仅仅是“唱”,不应该将戏曲的形式特征压缩到只需体现出若干段“唱”的程度,这是戏曲观念的误区,也是“话剧+唱”的积习。令人担忧的是,这种理论观念在戏曲编剧,乃至戏曲表演者中仍然具有很大的市场,甚至形成对传统戏与新编戏的“双标”,即整理传统戏执行传统戏的标准,编创新戏执行“话剧+唱”的新戏标准,所谓“老戏老办法,新戏新办法”。这种认知下编创的新戏,大多沦为形式特征不鲜明的奇怪事物,形态的缺失势必损失掉戏曲独特的美学韵味。《大树常青》在阅读过程中时常出现形态跳脱的印象,基本上源自戏曲韵味的不足。
如果继续深究造成“写戏剧”还是“写戏曲”问题的原因,最根本的是戏曲艺术形态的美学站位发生了偏移。中国戏曲的传统,尤其是进入到晚近以来,花部勃兴,主要坚持民间化的通俗立场。何为“民间化”呢?因为即或有文士参与晚近以来的戏曲创作,也要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民间立场编撰剧本,包括民间的价值原则、审美偏好、期待视野等。晚近以来,戏曲之所以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民间化的通俗立场”是其根本。而改良派的戏曲革命、“五四”时期的批判旧戏、1949年后的戏曲改革等,之所以表现出对戏曲的重视,主要也是针对戏曲民间性和通俗性的正向或负向的理论发挥。而中国话剧的传统,则开始于“洋派”的知识阶层,效法西方戏剧而实践中国话剧形态的目的,最根本在于启迪民众,促进民众的现代化觉醒,是一种高台说教式的、启蒙的立场,民间与通俗正好处于对立面的位置。历次戏曲革新运动的核心,都在于以新的价值观念革新戏曲的精神面貌,以放大戏曲艺术的教化功能。民众由戏曲艺术的消费者,变身为戏曲宣传的教育对象。问题在于,这一过程中,戏曲的内容标准与形式要求是分开的,新的价值内容必须借助于戏曲的传统形式,传统的形式程式中所凝结的民众的审美习惯,是价值革新格外看重的。这是1950、1960年代新编历史剧仍然保有积极的戏曲美学韵味的重要原因。
而进入1980年代以后,文艺观念和方法的解放,使艺术的形式问题成为一个“问题”。艺术的革新,首要是形式的革新。加之,娱乐途径的多样化、戏曲的式微,促使人们不断触摸变革戏曲形式的底线,戏曲艺术形式的决定权不再保持在民众的欣赏习惯中,而是被知识化、专业化的“创作主体”收回,成为探索戏曲“高雅化”的实验权利。戏曲艺术形式,不再需要市场的检验和接受,而变成纯粹的艺术创作和舞台实验,新创戏曲剧作尤甚,只需对创作者和投资人负责。是否借鉴传统、在多大程度上向戏曲传统学习,成为新戏曲创作者的艺术“自由”。戏曲民间性、通俗性的美学站位,完全被专业化、高雅化的站位所替代。
《大树常青》的问题正在于此,为了塑造人物而使用各种“大词”直白地宣谕,致力于对人物个性评价的舞台图解而不编织故事的整体性,以话剧的剧本形制补充进大段的唱词而成为戏曲,在根本上都是对戏曲编剧个体创作自由的过度放大,而忽视了戏曲剧本写作的规定性,颠倒了戏曲的美学站位。
《大树常青》在这些方面表现出的问题,不是自己的问题,而是当下戏曲创作的普遍性问题。对于《大树常青》而言,这些问题或许不是“问题”,而正是其孜孜不倦所要追求的戏曲创作的当下方向。所以,《大树常青》所呈现的剧本状貌,既有呼应时代、结构文本、编剧技术等方面的成熟老练,也有戏曲艺术本体性认知的不足。其创作的得失,是当下戏曲编剧集体性的观念优长与不足的折射,需要全行业重回戏曲传统、开展多方向尝试、接受民众和市场淘洗,才能够逐渐加以修正。
王一冰:三江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戏剧与影视学博士
责任编辑:周伟华